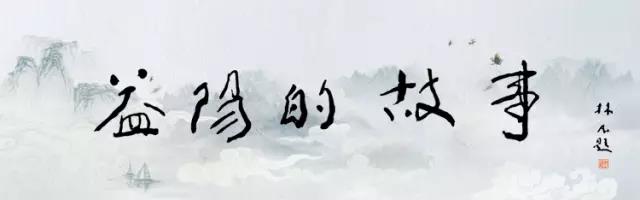
作者:老汉
如果说益阳人爱划龙舟,估计在国内都是说得过去的,一是除了这里是楚国、屈原的家乡外,最主要的是这里是资水的下游,江宽水平,适合龙舟竞赛。二是屈原流放在桃谷山作《天问》,现建有天问台,屈子伺。用划龙舟纪念屈原,是最生动的行为纪念。
当然,上述都只是益阳人爱划龙舟的理由,而历史生活的事实就是;益阳人自唐朝以来就一直爱划龙舟,并且,玩得很疯狂、很怪异、很出格。年年端阳节,资江自桃花江以下,总有数百只长短大小不一,花样百出的龙舟下水展技竞赛……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益阳龙舟竞赛,千百年来,尽管不下千次,家喻户晓,全县人几乎空户赶往江边看热闹,正所谓;摊卖小商道上摆,岸迎长炮水边鸣。老叟顽童,姑娘妇女,无不欢呼雀跃……。
就这么一个影响、热闹益阳人上千年的“划龙舟”,竟然没有一套完整的龙舟比赛程序和游戏规则,就是参加和观赏赛龙舟几十年的观察家,也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出益阳赛龙舟的过程与轮廓外貌。县史乡土志,几乎见不到比较准确生动的说明文字,再就是文人墨客的刻意赞颂,似乎也是文不对题或偏颇太甚,何以故?
原来,益阳自有赛龙舟的历史以来,就从无一次将比赛进行完毕、闭幕取得名次的,是一个有始无终的比赛。并且,没有一次不是以斗殴打伤人由官府处罚判断赔偿而告终,几乎年年都是官司收场。
这里,可先介绍传说中咸丰九年益阳知县在资江上至青龙洲,下至孟家洲两块同样的《府县两宪准示禁令碑》,这两块同样的碑就是严禁在此河流段划龙舟的禁令,传说上游青龙洲的禁碑在光绪年间被船夫与排鼓佬作为捆船套排的石柱,磨得铮亮,许多人都能背诵禁碑上的文字;“龙舟不得经过,除收缴龙舟外,鼓夫杖责三十,桡夫各二十…..”也就是说,老益阳县在咸丰九年(1859)就禁止在城区内划龙舟,并规定此区域外上下挑衅的龙舟不得在此区域内经过。
当然,这种不得已的禁令虽然严厉,到底还是有些不近人情乡俗,直到光绪二年(1876),知县吴兆熊出任县令时,又再颁布一道禁令;《为再禁龙舟杜滋事细照》,这道禁令,用宝贝纸书写,沿河墙、柱张挂,表面上看,似乎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重申咸丰九年府县的禁令,实则是网开一面尊重民风乡情,细照规定;上游自青龙洲以上的新桥河、邹家河、花果山以上的龙舟,定赛场在桃谷山的水口(即今天的划船港,地名由此而来),下游清水滩、陈婆洲以下的龙舟定赛场在兰溪的荷花潭。这样一来,虽还是益阳城区内的河面禁止划龙舟,实则是把一个赛场变成了两个赛场,益阳划龙舟的场地与文化氛围也更加开阔浓厚。
事实上,在益阳禁止划龙舟的这十多年中,禁区外的划龙舟活动从未停止过,并有扩大普及的态势,象城区上游就普及到了花果山,修山、粑粑铺、长春,远离河面的乡镇。只是碍于官府禁令的缘故,使得这种乡风民俗的娱乐体育活动从表面上失去了“正统”的支撑,官员和体面的绅士不便于公开的支持和喝彩,龙舟赛也就失去了隆重和正规气氛。
但龙舟赛原本就是起源于民间的习俗,无有官府的捧场,便更加演绎得粗俗,甚至还增加了不少恶习陋俗,这里,还是把这种纯民间孕育形成的划龙舟习俗做一个全过程的简述,并以上游桃谷山与花果山为例;
才过阴历4月8,各乡村就开始热议打造龙舟的事宜了,第一步便是“盗龙头木”,因龙头龙尾每年都要新打造,这才有新年新气象的寓意。
但龙头龙尾木硬不得软不得,硬了沉重影响浮力,轻软又不经碰撞,故此,多选择上百年的白檀木与樟木,可这类木材都是私人房前屋后留下的打家俬与棺材的名贵木材,往往视为家庭贵重财产,但这种木材不管你主人认为再珍贵,甚至就是命根子,一旦被“龙舟筹委会”看中,你就是皇亲国戚也无法保住这株树,铁定是要被“盗”走的,所谓“盗”,实则是抢,只是事前保密没通知罢了。
一声“喔嗬”,数十人拢场,尽管树主人呼天抢地,所看中树木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砍伐“盗”走,“盗”走后自然也无半点报偿与补助,至于树木打造龙头龙尾则不必细述。
再就是新造或修补船身,所谓新造,是指今年新参赛或去年赛败了的乡村,修补则是去年参赛的旧船,无非是补缝和油油罢了,但船的尺寸大小,尽管可以大小、站坐不一,有两条江湖规矩是须遵守的;一是比赛的龙舟须是同类同等,多是参照竞赛对手的类型打造。二是龙舟无论规格大小,都必须遵照一个潜规则;即船长与船宽的尺寸尾数必须是“五”,如;长两丈八尺五,宽三尺五等,这两个“五”,暗合五月初五端阳的日期。
再次,就是桡板的制作了。“桡板”,也就是桨叶,这一点,除了江湖规则的要求外,最重要的就是公输般庙(即鲁班庙)对木匠的职业要求与法律对桡板尺寸重量的要求,桡板开始是划龙舟的工具,但后来则是打仗的武器,如果打伤人堂审时发现桡板超规格或不按标准,首先追究的就是木匠的责任,不但“吊销执照”逐出庙会,还要吃板子被枷禁。
因此,桡板从不敢出格,都是用杉木做成,重量不得超过五十四两(传说中的一个人头的重量,十六两秤,约3.4市斤),按规按矩的龙舟打造好以后,四月下旬龙舟下水,第一日是龙舟测试,一是看是否进水有漏洞,二是看人坐满后龙舟吃水的深度,也就是说,以船舷高出水面一寸半为最佳,太高则说明船的空间过大,影响速度,太浅则怕船易进水同样影响速度。
测试好船以后,第二天就依照传统的祭祀方法请礼宾哼读告文,用三牲酒肉祭祀龙头,请本乡德高望重者在龙尾画太极图,在龙头点睛以长神气镇邪。龙舟便进入训练阶段,此不详述。
但龙舟正式比赛这一天,也就是端阳五月初五这一日则有必要详述;前面说过,益阳划龙舟有史以来都是有始无终,这个“始”,也就是开幕式还是很正规的;首先是请各参赛乡村的尊者与赞助者入位归坐,也就是今天的主席台,再就是在入座者当中相推选出一位声音洪亮者宣读祭文,祭祷江神龙王(似乎与纪念屈原无关),再就是司仪请入位者检验龙船与桡板、鼓、梢,验收后,便宣布比赛的分组,主要是按船的大小规格分类。
分类后,再宣布分组后的两种比赛;一种是“抢过江”,相当于今天的“短跑”,另一种则是“抢长河”,即逆水而上,约三千米,也就是今天的“长跑”。
在清朝末至民国年间,在桃谷山划船港的江面上,往往要设置五处以上的彩头台,所谓“彩头”,主要是宰杀完毕的猪,一颗猪头扎着红绸格外耀眼,谓之曰“彩头”。
“抢过江”的设在对岸的奖架上,“抢长河”的则设在江面小船的奖架上,这种彩头,一般年间都是各设两处以上,而彩头的来源多是各村能入位的尊者与体面乡绅所捐献。

(1920年挪威国家教会的神职人员在益阳大渡口参观拍摄益阳划龙舟的情景)
分组设奖落妥后,便是鸣铳开赛,三眼铳响,霎时;锣鼓震天响,鞭炮盖地飞,龙舟上;号子喔嗬节奏铿锵有板有眼,两岸边;人山人海呐喊喧天杂乱无序,再加上两岸的烟花、火焰、冲天炮,迅即便把这划龙舟的气氛推到极限,不几分钟,第一个高潮出现,即“抢过江”的龙舟便出现了混战,这种混战很有意思,往往抢过江的龙舟有上十条,但首先打起来的是一、二名,一、二名因打斗三四名便赶了上来,于是,新的一二名又成了打斗的主角,表现的是一个枪打出头鸟的场面,总之,谁也别想先抢上岸,谁抢先谁就是众矢之的,这种打斗虽然是一种混斗场面,但如果仔细观察,还是有一个大界线的,即河南与河北是主要打斗对象,当然,如果抢在前面的都是同一边的,那自然是抢在前面的互斗,也就没有界线之分了,这种打斗在离岸还有两丈远的地方最为激烈,桡板横飞,吼咆嘶哑,龙舟挤撞,人仰舟翻,一片混战……,
就在这种混战一时还没出结果的时段,另一组“抢长河”的高潮也就到来了,这是比抢过江更激烈精彩的竞赛,由于距离长,拉大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像抢过江,抢到上岸的差距也就是超越一个船身,容易发生绞缠扭打。
按理说,这种“抢长河”的长距离竞赛是完全可以摆脱纠缠的,长距离疾驰直接抢到彩头就可以赛出名次了,但益阳的“划龙舟”怪就怪在这里,目的并不是名次,也不是速度与“吉尼斯”记录,而是一种直接战胜对手相互打斗的宣泄,每次划在前面的不是直奔彩头,多是要对后面的龙船实行“包头”,所谓包头,即超越后面的龙舟一船身后,急转弯从后面的龙头前面包抄过去,然后再从后面追上来往前赶,如果包头成功,寓意把对方乡村一年的“好运”全部“包”了过来,自然,被包头的乡村一年也就倒霉透顶了。这便是包头与被包头的全部内涵与结果。
当然,激赛中的包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是绞缠在一起的打斗,只有极少的机率才能完成,千年以来,可能还没一次完整的“包头”,但即使完不成,“包头”还是每年必玩的过程,这既是很危险的过程,也是划龙舟赛中最激烈的高潮,每到这个时刻,两岸欢声雷动,喊叫震天,其阵线立场十分鲜明,都是给本村乡的龙船加油。
这里,暂借2005年端阳节资水下游兰溪荷花潭的一次龙舟赛形象说明;严格的讲,益阳龙舟赛长期以来因都是打斗收场,故官府都是禁止或半禁止的态度,尤其是在城区内的河面上,从咸丰九年(1859)以来就一直没开过禁,但老百姓自发的组织龙舟赛,可说也一直没间断过,对此,官府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没弄出大事缠着官府就装着没看见,但2005年这次却不同,起源于益阳兰溪文化站站长莫晓阳的两篇文章,《龙舟赋》与《兰溪龙舟甲天下》,这两篇文章分别在益阳日报和益阳电视台发表播讲之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巡视员龙爱冬看过之后,居然写下了一篇《字里行间见真功——读“龙舟赋”的几点感概》,认为益阳龙洲是;“两岸和谐舟上结;一方雅俗浪中凝”和“提升荆楚之闪光文化;锤炼炎黄之拼搏精神”。
当时,正值益阳“招商引资”的倡导高峰,市委区委乃至兰溪镇一致认为,打好益阳龙舟牌可以提升益阳的知名度。于是,益阳千百年以来出现了首次由官府亲自策划并组织的龙舟赛。自然,电视台与报社记者采访报道,市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员保驾护航,其规模也是益阳有史以来的一次最高规格,不下40条龙舟云集兰溪河面,最大的居然长36米,共36舱,108个桡手,8个甩桡手(即舵手),4个招桡手(用桨叶打节拍,紧要关头助划的桡手),1个鼓手,1个打扮成小丑模样举旗的指挥,共计122人。

按理说,这种市、区、镇三级组织,并明显的规定游戏规则,划定航道,设有奖金名次,并有电视台现场拍摄报道的龙舟赛应该是“两岸和谐舟上结;一方雅俗浪中凝”的圆满结局了。
但前面说过,益阳龙舟赛是有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一场打斗赛,今外表再包装规范,并没有改变它的底蕴内涵,在“抢长河”的竞赛中,一条不到三十人划的小龙舟,率先对那122人的巨无霸实行包头,这种包头是很有技巧的,要全体成员心有灵犀,准确而又齐心合力的配合,最好是在超出后船一丈时急转弯实行包抄,若被包头的龙头撞到包头的龙尾,便是借力打力的包头成功,其时间可以精确到0.1秒。
然而,被包头的龙舟“破锁”也是一宗很高超的技巧,我们知道,当桡手齐心合力划水时,船底是可以高离水面的,即“飞了起来”,会“破锁”的指挥便是利用这一刹拉可从包头的船身上横冲过去,当然,时间没利用好便是碰撞后的缠打。
兰溪122人的巨无霸正是利用好了这一刹拉时间,从小龙舟的身上横压过去,如果是相等的龙舟,这种横压,也就是压过去的那五六个人落水,但此次是122人的巨无霸,连船带人十余吨,一下便把小龙舟压沉了,满船人尽落水,而冲过去的巨无霸自然率先到达了终点,在船离岸还有几丈远的地方,岸边本村的乡亲欢声雷动,姑娘大嫂老头子像发疯似的扑到比腰还深的寒水里,个个头顶可乐,雪碧、面包、粽子、洗尽的水果犒劳他们的勇士和英雄,人人争着用手抚摸这只得胜的英雄龙舟……,但也就在这时,那打伤沉船的龙舟经重整后便箭一样的冲向了这只已停靠的巨无霸,于是,一场桡叶互砍的混战展开,随之,双方助威喝彩的村民亦加入混战之中,其中还有一对翁婿,其岳父对女婿大喊;“斌伢子,我是你岳老子”,但这种划龙舟的混战立场十分鲜明,可达到六亲不认,叫斌伢子的年轻人大声回复;“就是亲爷老子来了我都不认,先砍你几桡叶再说”。赛龙舟的乡土荣誉感居然可以做到大义灭亲!

但此时保驾护航的市公安局干警显然不知道这千年风俗底蕴的深浅,一群干警冲进去把两个打斗得最凶的桡手铐了起来,这一下,如同是火上浇油,激愤的人群一下把打斗的目标转向了干警,当场打翻十余个干警,掏出钥匙自开了拷锁。随后又追赶抱头鼠窜的干警,好在警察们逃跑有术,但跑脱了人却跑不脱车,于是,停在那里的几辆警车被一一掀翻,车上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被拖下来打断腰椎骨致残……,直到十日大端阳过后,市区两级公安局才通过调查分散抓获17名肇事者,分别给予刑拘和罚款,其文化站长莫晓阳因煽动挑事被刑拘3个月……。
益阳史上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龙舟赛就以最大的闹剧收场,所有的报道、图片音响视频全部撤销删除。
而上游桃江划船港赛区的龙舟赛虽没有下游兰溪的规模,但赛龙舟的乡俗情结却是一脉,每年都以打斗结束赛事,不过,还要特别说明的是;赛赢的龙舟被全村的村民抬顶着游乡,披红挂彩,铳炮齐鸣,凯旋回村,一路上,无论是襁褓中的稚童,还是耳聋眼瞎的老翁,都要争着摸一下这英雄的船身,以示沾上好运。
但如果是赛输了的龙舟,是绝不能抬回家的,否则就是把霉运带了回来,因此,赛输的船只都是弃之不用,久而久之,在划船港的下面便出现了一处“烂船州”,也寓意着把霉运从江河里冲走。
以上就是益阳千年划龙舟习俗的客观总结与概括,从表面上看,肯定不能算一种优良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找不到半点先进性和积极意义,再从官方的政治立场来看,似乎可以归纳为地方的陋习恶俗,但就是这么一个有始无终、每年都要以闹剧收场的划龙舟,为何老百姓如此热捧并传承上千年呢?
这就要从益阳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中去寻找其传承的原因了;益阳地处资水下游、洞庭湖区,而上游的梅山湘西文化又有几千年的刀耕火种习俗,加之资水穿越雪峰山脉时落差极大,因此,这里每年开春以后,资水都会有桃花汛,夏汛与秋汛,这种无法预测规模的自然水汛,破坏性极大,稍不留意,就有溃堤倒圩的危险,而这种灾难,往往是一个乡或几个村。
因此,凡出现一处或一段险情,抢险就绝不是一户一组和就近村民的小事,而是整个乡或几个村共同安危的大事,在这个时刻,乡村的凝聚力,统一号令,服从指挥,是湖区圩子必备的常态文化氛围,尤其是出现决口需快速堵上的时刻,就更需要速度与合力,一声“嗬喂,划董!”,就能快速的把全乡的力量瞬间集中到抢险堵口上来。只有一鼓作气的殊死抗争,才可保证不至于功亏一篑。
而划龙舟,就正是这种集体凝聚力与统一指挥合力文化的训练与养护,因此,益阳的划龙舟,尽管外人难以理解,但常年经受水患的圩子内居民是能够心领神会不言而喻的,划龙舟的拼搏打斗,实则是长期以来水患大于水利所逼出来的一种潜在的与自然抗争心态,几代人下来便形成习惯成为基因。在堤溃家破的威胁下,没有礼仪规则,文明失态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随着科技生产力的提高和水患的有效控制,益阳人这种划龙舟的心态与打斗闹剧所依据的防汛抢险环境已得到很好地改善,相信经过两代人之后会慢慢消失,但眼下甚至十年之内,只怕还无法保证能进行一次完整有终的龙舟赛。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