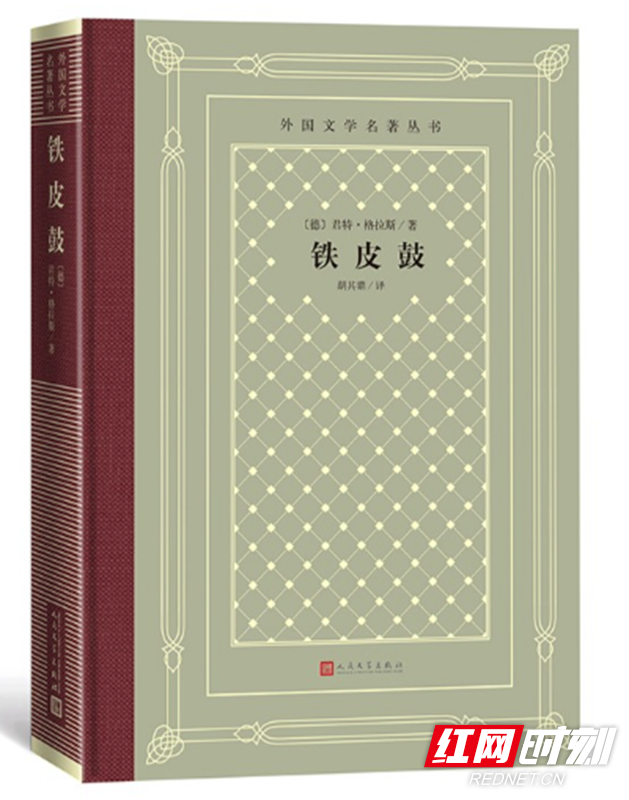
荐书词:
德国文学始终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凝视。在《铁皮鼓》中,奥斯卡的鼓声既是民族身份撕裂的哀鸣,也是个体在极权之下精神畸变的证词。当消费主义和流量算法解构个体存在的意义之时,这本书恰恰能够在时代的喧嚣中帮助我们叩问存在的本质,校准自我的坐标。
《铁皮鼓》是君特·格拉斯于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凭借这部作品,他于199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侏儒奥斯卡的视角,回溯并再现了从威廉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希特勒上台,到“二战”及战后德国小市民生活时期,发生在德国、波兰边境与但泽地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环球时报》评论其为“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
在“二战”后德国思想废墟亟待重建的年代,《铁皮鼓》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引领时代反思与自我省察的文学灯塔。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更深层次地探讨了个体“自我”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如何定位与自处的命题,其对于当下喧嚣不已的时代和精神虚无的个体,仍具有深远的警醒意义。
一、控制之鼓:吞噬与迷失
书中充满了怪诞离奇、光怪陆离的描绘:能震碎玻璃的铁皮鼓、自出生便智力超常的婴孩、因疯狂吃鱼而中毒身亡的母亲……
然而,这些看似超乎自然的叙述,并非旨在编织一个虚幻的故事世界,而是巧妙借助这些元素,揭示出隐藏其后的那段迷茫无助的悲剧历史。奥斯卡用鼓声震碎玻璃,不仅是奇幻设定,更隐喻着纳粹宣传的脆弱性与极权话语的虚妄本质。母亲吃鱼中毒而死的场景令人感到黏腻与窒息,暗示了民众在纳粹狂热中自我吞噬的集体癔症。
玻璃的破碎,不仅是纳粹话语系统的瓦解,更是奥斯卡对集体癔症的反抗宣言。格拉斯创作此书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1945年,随着希特勒政权的崩溃,德国人民从残酷的专制统治中得以解脱,但长期的精神枷锁与思想禁锢,仍深深束缚着他们的灵魂。书中描绘的但泽市民作为边疆地带的历史见证者,直观地感受着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扭曲、压抑、极端的情绪由此滋生。战争的伤痛真切地降临于个体之上,奥斯卡拒绝出生,正是因为无可避免的死亡:“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代表个体诉求的“鼓”,在混战中遭到损坏;而战争本身进行的,皆是无意义的行为。
除了最直观的伤亡与个体诉求的埋没,在动荡年代,个体的身体成为民族创伤的载体,民族身份认同亦产生巨大动摇。“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人们又在寻找波兰。”但泽作为德波边界的“飞地”,其归属的流动性被具象化为奥斯卡家族血缘的混乱:舅舅扬与母亲的不伦关系,使奥斯卡的生父身份悬而未决。血缘的暧昧性,对应着民族认同的撕裂,个体的身体由此成为领土争议的象征性载体。
二、反抗之鼓:清醒与觉醒
格拉斯极尽笔触,描写特殊时代下个体的迷失与异化。首先,他呈现了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书中有一段描写:“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擂鼓集合,擂鼓进入坟墓。”这里的“擂鼓”实为集体行动的节奏。鼓声的强烈迫使人们陷入狂热,个体声音在同化性文化的灌输下变得微弱,甚至彻底消失。
当成人世界用统一的鼓点指挥游行,奥斯卡则以更高频、更刺耳的鼓声打乱节奏。他拒绝接受成人世界的道德规范,对现实社会的倒行逆施表达强烈不满,并不断挖掘被压抑的记忆。正如有评论指出:“奥斯卡表面上拒绝成人世界,其实他真正拒绝的是外部现实世界对他独立、清醒认知方式的侵蚀。”这种拒绝,实则是对无序世界的反叛,是一种半理性却坚定的行为,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坚守。
其次,格拉斯通过奥斯卡结识的马戏团侏儒贝布拉这一角色,形象地揭示了战争爆发时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国民性,对文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展开理性批判。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当个体融入群体时,其个性往往被群体所淹没,思想也被群体思维取代,进而表现出情绪化、非理性与低智化特征。战争期间,贝布拉从马戏团小丑摇身变为戏剧团上尉团长,继而又成为西方演出公司老板,其身份的不断变换,映射出德国小市民阶层见风使舵的习性,也暴露出民族在动荡时期所呈现的脆弱与不安。他曾劝告奥斯卡:“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这句话看似是对向上流动的积极呼吁,实则是以表演型人格适应极权体制,将道德矮化为生存策略,令人悲哀!
奥斯卡的舅舅扬虽身体健全,却同样缺乏主见、尊严与责任感,在政治风浪中盲目而可悲。时代之中不乏反抗的呼声,但这些“反抗”究竟是真正的觉醒,还是仅作为时髦的标签或自我标榜的工具?奥斯卡在书中提出了这一疑问。鲁迅笔下的阿Q也曾“闹革命”,但那种革命意识归根结底是随波逐流与哗众取宠,或盲目顺从,或自欺欺人,最终错失了真正的自我觉醒,呈现出一种可悲可叹的国民性悲剧。
时至今日,思想的肤浅嘈杂与精神的匮乏孤独,已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困境。我们亟需的,不是口号式的反抗,而是沉静而深刻的反思。
三、救赎之鼓:升华与归真
家庭伦理的崩解,是君特·格拉斯解构传统价值的关键所在。书中呈现的人际关系混乱而悖伦:荒诞并非目的,荒诞本身就是现实——在欲望的火焰中,伦理道德之绳早已化为灰烬。
奥斯卡的性格充满矛盾,也蕴含着作者的深思。他并非传统意义上富有良知的“圣徒”,而是自私、淘气、冷漠又复杂的结合体,兼具善与恶、懵懂与通透。他诱使他人从破碎的橱窗中窃取物品;在波兰邮局保卫战中被捕后,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舅舅扬;战后面对法庭,却又选择沉默。奥斯卡是人性真善美与假丑恶的综合体。作为敲鼓人,他亦在鼓声中挣扎、矛盾。
战争年代下的家庭伦理与个人德行,“秩序”与“善良”都面临巨大挑战。格拉斯并未在书中流露出明确的褒贬态度,而是通过角色的道德模糊性,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答案,迫使读者直面人性的混沌本质。
和平年代亦存在人性坐标倾斜的可能性。当短视频算法试图驯化我们的思考力,当消费主义企图量化我们的幸福感,当成功学正在格式化我们的人生观时,那刺耳的、不和谐的、拒绝被规训的鼓声,就应当隆隆作响。而那些在流量狂欢中坚持书写严肃文学的作家,在消费陷阱里守护手工艺传统的匠人,这些现代“敲鼓人”并非圣徒,他们同样会在欲望的沼泽中挣扎。这种矛盾性恰恰证明:救赎不在于消灭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回归人性应有的边界。救赎之鼓,不是乌托邦式的完美和声,而是带着裂痕与杂音的、属于尘世的交响。
四、结语
在君特·格拉斯笔下,鼓声被赋予了多重复杂的象征意蕴:它既是那个时代政客用以麻痹民众、实施政治宣传与思想控制的“控制之鼓”;又是一股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够唤醒民众沉睡独立思维的“反抗之鼓”;更是引领人们挣脱欲望枷锁,回归人类纯真质朴原本状态的“救赎之鼓”。
正如格拉斯所言:“‘二战’之后的德语文学,只有使自己成为一种记忆。让过去永不终结,它才能毫无羞愧地面对自我与后人,继续‘未完待续’这一普遍有效的写作规律。只有这样,伤口才能显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从前曾经如何’。”
铁皮鼓声穿透历史,在算法与消费主义喧嚣的当下依然回响,敲击着现代人混沌的灵魂。当全球化浪潮与文化渗透撕裂身份认同,当算法“茧房”将人类切割成数据标签的集合体,当消费主义与金钱至上不断放大人们膨胀的欲望,我们更需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民族、自我与自我三者之间,以“敲鼓人”的姿态,不断自省,获取正向的前进力量。
文图/冯绮敏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