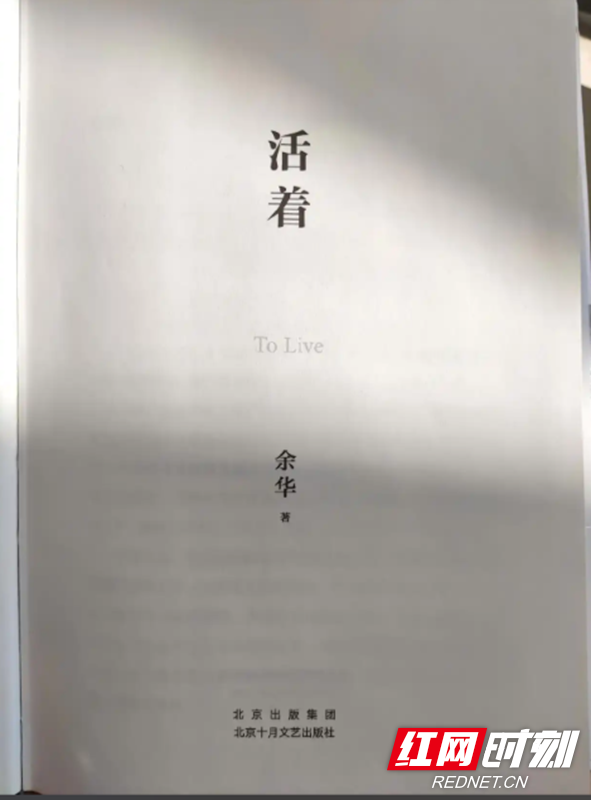
当钱财散尽不复还,当血脉传承的薪火熄灭,当温情的慰藉被碾作尘泥,所有附着在生命之上的价值外衣被撕去时,我们还剩下什么?如果你困于虚无,厌倦了用各种外在物质堆砌出生命的意义时,也许可以停下来看一看这本关于生命原力的虔诚礼赞。
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余华的作品如一枚散淡的月亮,不淆世俗的浪潮;在现实的冷酷画卷里,福贵的一生是苦难的标本,他以蝼蚁之躯对抗命运的碾压,最终在“活着”的废墟上,重建了存在的尊严。
一、以直接朴素之笔,勾勒苦难的骨骼
读余华的小说,往往是一口气憋到底,不到结尾不放松。小说中,连缀不断的血腥和死亡构成长串的生命符号、混乱到“滑稽”的社会秩序、晦暗不明、复杂多面的人性…… 一刀刀在心上磨锐后又直直地戳进脊骨,尖锐、密密麻麻、逃无可逃的痛,像是天空黑沉沉地压下来,随着叙事的推进一点一点朝人越逼越近。
在余华冰冷的语调里,我似乎目睹了福贵的一生,悲喜交集,欲哭无泪。嗜赌成性的福贵少爷荒唐地将家庭推向破败,穷困潦倒之际,老爹被活活气死;福贵又被国民党拉去做壮丁,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时,母亲早已病逝,女儿凤霞因病成了哑巴。
在层层叠叠的悲哀里,作者又让我看到了点点温情,留下一丝希望——儿子有庆长跑得了第一名,凤霞怀了孕嫁了人。当我天真地以为噩梦破晓,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跃然纸上时,作者并没有让这简陋的欢乐延续。没有丝毫委婉,冰冷的笔锋下,书中的一个个人物以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迅速死去,毫无预兆,几近残忍。凤霞难产而死,有庆的死更是冤枉。小小的孩子把能给“大人物”献血视作无上光荣,黏稠的血液流淌在胶皮管子里,一端是年幼的孩子,一端是迎接新生的妇人。最终,孩子倒在地上,像一片枯叶拥抱土壤:“去叫来医生。”医生蹲在地上拿听筒听了听说:“心跳都没了。”医生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骂了一声抽血的:“你真是胡闹。”就跑进产房去救县长的女人了。
儿女的死像是苦难的渐强符,在这之后,妻子、女婿、外孙,仿若一切都陷入诅咒一般,一个个死去,只剩下福贵孤身一人,还有他名叫福贵的老黄牛。
一气读下来,情难自抑,不知不觉竟走过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余华的笔像一条冰冷的铁轨,将福贵的一生牢牢钉在“生与死”的轨道上,没有粉饰,没有遮挡,把希望一层层剥落下来,展现出一副白惨惨的苦难的骨骼。作家并不倾心于描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悲壮冲突,只是残忍而又冷酷地剖析个人“活着”的受难方式和过程。
除了叙事结构的简单,在人物的社会身份安排上,余华也同样返璞归真。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福贵的生存愿望和生存方式都很朴实,仅仅是“活着”。他很少与社会、历史构成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很少与邻里产生伦理道德上的冲突。除了年轻时浪荡过一阵子之外,他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安分守己者,理想、光宗耀祖、抱负、地位…… 所有这些人类正常的欲望都被他从内心中剔得一干二净。人物与命运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只剩下生与死的最直接对视。因此,当福贵回忆自己的一生时,不无感慨地说:“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这番话语淡而味不薄,细细读来,蕴含了某种“无欲之境乃至高之境”的中国式生存理念。
我想,正是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使《活着》才以某种近乎透明的效果,剥离一切修饰,让苦难赤裸裸地站在读者面前。也正是这最朴素直接的表达带来了最强烈的情感冲击与共鸣,读者因此而久久不能回神。
二、大地与黑夜的合奏下,展现着人性的光辉
余华的作品不愿飞升、不想慕远,他的创作倾向是一种下潜和沉落。从土改到包产到户,政策如镰刀割过麦田,人物的命运总是和大地交织,可是在余华的小说里,我们感受不到张炜那种亲近大地的栖居之乐、那种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至性至德。我们只能通过弥漫的阴霾和鬼气,依稀看到不太真实的河流、村庄、房舍。在余华笔下,大地之上的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都是可疑的,充满了危险和阴谋。人只有活在地平线以下,像《一个地主的死》中的老人那样藏到茅坑里,才有些许安全。
在《活着》中,当“福贵”向作者“我”叙述平生无穷的苦难时,“大地”几乎从小说中消失了。直到最后,“我”告别了“福贵”和他的老牛,“大地” 才意味深长地被提起:“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的来临。” 在余华笔下,大地和黑夜并非像《九月寓言》中那样给万千生灵带来无尽的意趣,而仅仅是一种死的安宁。余华笔下的大地与黑夜只能合奏出一声怅然长叹,那不是对生命的肯定和赞扬,而是对生命的一种否定性的解脱。在《活着》中,大地更像是生命的坟场,也是福贵最后的见证者。当他牵着老牛走向田野,土地沉默地收纳了所有血泪,却也在暮色中向他敞开一丝生的慰藉。
在这种对生命的否定中,人们很容易陷入虚无,而此前字里行间泼洒出来的乐观与顽强,则是余华递给读者的一根浮木。
余华不吝于刻画那些闪耀于文本细部的人性光辉,那些弥足珍贵、苦中作乐的平凡与真实。与凤霞团聚的欣慰、有庆割草时的简单快乐、福贵的老牛、农田里的歌唱…… 历历在目,无不是人物内部的生命张力突破情节的束缚,从文字中蓬勃地洋溢出来的表现。无关乎历史的宏观叙事,这些寻常生活中冷暖自知的点滴小事,一点点袒露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博大胸怀,是血流的河中飘起的浮橹,让人望得见活着的意义。
在暴力麻木中被痛苦破碎支离,也在寻常饮水中热泪盈眶。这便是我对余华作品虽不深刻但却最切实的感悟。
三、生活以痛吻我,我将报之以歌
“活着”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存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但是“活着”的背后,又分明地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包含了某种宽广无边的生存意味,也体现了自然生命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在谈到这个题目时,余华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的意义不在于喊叫,也不在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回望那段经典的福贵与老牛对话的场景:“‘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 福贵扶着犁,对着空旷的田野念叨:‘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在此,背离传统的救赎叙事,主人公没有顿悟的灵光,没有升华的奇迹,唯有垂暮之年对着牲口细数逝去亲人的名字,将破碎的记忆缝补成日常的呓语。
在此,生存的意义不再依附于亲情、理想或历史洪流,而是扎根于“活着”这一最原始的状态。福贵对老牛的絮叨与其说是缅怀,不如说是对生命痕迹的确认:当所有社会关系被死亡剥离殆尽,当土地只能埋葬希望而非孕育未来,“存在”本身便成了最后的战旗。余华以近乎荒诞的笔法,展现了存在主义式的生存美学——活着本身,就是胜利。
有些人对待命运,疾苦地呼号,也许会淹没于命运的浪潮;有些人对待命运,悲愤地抗争,却可能在头破血流之后一蹶不振。福贵属于第三类人,他忍受命运,在静如止水的心中积蓄着生的力量。他在“窄如手掌”的一生中,活出了“宽若大地”的意义,活出了眼泪的丰富、绝望的不存在,活出了生命的色彩。
在小说结尾,黯淡的阳光下,老人与牛渐渐远去,仿佛苦难与生命一同融入了土地。亲人的尸骨在身后,曾经辉煌的梦魇张牙舞爪,背上肩负着“活着”责任的福贵,咬着牙、带着满身血痕的福贵,绝不能回头,他转过身,毅然向前——这是读者能从作品中看出的希望。余华把读者拖进悲惨世界的泥潭后,还不忘拉扯一把,镇静地告诉你人性的坚忍,只有“活着”的诘问在风中回响:若命运是巨浪,我们是该沉没,还是以蝼蚁之躯,在浪尖刻下自己的姓名?
文图/金栩妃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