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鸥
文/苏晓
红嘴鸥,俗称“水鸽子”,两翼尾部呈现出煤一般的漆黑,它们集群嬉闹,依水而生,自水边来,又在水边栖息。它们终生是旅客,一年中,它们大多时候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北亚地区一片广阔的地带,临北冰洋,因此终年寒冷。寒流来临时,它们又飞往中国腹地,落脚于云南昆明。从十一月至一月,春风渐生苗头,温暖的南方水流北上,逐渐淌过北方水系中冻结的水流,冰河变薄,这群来自异乡的鸥就预备飞回。
我有时觉得,自己应该是鸥群中的一只。我若是在天空中翱翔,人们只能看见尾羽上的黑,偶尔有视力好些的,还能看见喙上的红。他们也许并不认同我是此地的孩子,只有这块土地,以地母的敦厚接纳我。
自五岁起,我和家里人迁往外地,与鸥一样,只有到了年尾,才能飞回一次,赶上寒冷的冬。我和母亲顺着人海而来,逆着返乡的路离开,每一次春风都吹到了我们身上,急急催促我们回去。能肯定的是,我与它们又有不同,我出生在南方的暖地,哪怕每每总要飞往他地,这里也永远是我的第一故乡。这块高原之上的土地,是温柔的、暖和的、永不冻结的……
一
红砖黑墙,举头是一片蔚蓝天空,水泥地特有的冰冷气息被岁月化解,陈旧使一切变得可亲,我在这里出生,这栋房子建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小县城里,小到用脚步丈量一圈,甚至不需要一天。
我的外婆外公用双手搭建起这座三层楼的小房,到第二代,我的舅舅和姨妈开始经营,把它变成一个半住半租的旅馆。它沉默地竖在坡的半腰,支撑起了第三代人的童年——一楼的大门敞开,我和姐姐就在那里玩着收银游戏,学爸妈的样子,嘴巴里数着一毛、两毛、三毛。
一楼有收银的房间,一扇铁架框起的窗,客人背着大包小裹落脚,先付过现金,主家再替他拉开木门,视线所及,能见到一个空荡的大堂,里面还有一个隔间、一口井、一把摇椅。这种布置在现在看来似乎是怪异的,在当时,却是外婆外公为一家人所做的最精心的安排。一旁的隔间是我们一家人的厨房,有圆桌,几把椅子正好够全家人落座,这里不对外开放。外婆闲暇时在这里拨玉米,把它们磨成有粗有细的粉,给我们做包谷粑。偶尔,这间小厨房也迎来一些极累极饿的客人,外婆便二话不说,揪出两张温热的饼,让客人垫肚子,又掀开锅,煮上一碗热气腾腾、散着猪油香的汤水饵块。
隔间正对着水井,从里头打上来的水不仅可饮用,还能拿来灌水烟,那是我的外公为数不多的爱好,后来吸的时间长了,索性用烟揽客——爱好水烟的人看见,就会在此落脚。他们之间互不相识,搬张凳子来就能成朋友,夏日乘凉,冬日就缩进门里,围着炭火盆坐成一圈。我们此地的水烟有种特点,烟管如碗口一般粗,有些由直接砍下的成年的竹子制成,这也方便他们将大半张脸埋在烟管中,只露出一双向外窥探的眼睛。
无需多言,人们点点头,靠近井一端的人就心领神会,举起一瓢来,将井水自上头注进长长的烟管中,似乎这样清澈的水,可以缓解烟的侵蚀,舒缓彼此的沉闷。
自打我出生,千禧年后,外公不再抽水烟。又过几年,那把摇椅就被搬了进来,成了外公的专属座位,他如一根松针久坐于此,自清晨到晚上。最初,外公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而后一天天弯下去,那也是我对时间之迅疾感知最直观的一次,他就像一片失去水分的绿叶,变得枯黄、萎缩……最后,几乎仰靠在摇椅上。我还记得,外公常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手握两颗银球,妈妈说那是锻炼大脑的玩具。
没有搬来摇椅前,外公也常和外婆一起走路,偶尔还会轮流背我上下幼儿园,这段记忆回想起来有些模糊,我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也更令稍大一些的我好奇,外公为什么不再站起来和我说话、玩耍?总是坐在那里,他不会无聊,不会觉得沉闷吗?这些问题他始终没有给我解答,后来的他,甚至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外公虽沉默,却是当时的我的一根主心骨,无论我从多远的地方跑来,家里始终有人坐在那里等着。他很安静,那把草藤椅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后来,妈妈告诉我,外公在我出生之后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不记得大部分事情,脾气里的怒性消失了。因此,在我们小辈的眼里,他永远是温和、坚定的,每日等着我们归来。
可惜,数年之后的某个秋末,距离暖冬,仅剩下一两个月,外公走了。他还是没有如愿以偿,没能一直留在这栋饱含他半生心血的老房子里,就连葬礼也是在舅舅的新家举办。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离开了那把摇椅,住进了医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未满十岁,在外地读书,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孩子是藏不住眼泪的,伴随妈妈一阵阵鼻子吸气的声音,我一路放声大哭,赶上了回程的汽车,匆忙回到滇地。
在路上,夕阳已落,车窗之外的高架正被余晖浸染,地上车辆稀少,天空中少有鸟的踪迹,一切显得寂然、萧瑟。每逢秋末,我常想起外公,想起老房子里不再有摇椅,不再有人头戴蓝帽,安静如松。
后来,再长大一些,我了解到鸥,生物学上将它们划分为候鸟,它们一年一度迁徙,是一种按年离归的鸟类。不知为何,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一群涌动的鸥,似乎它们所追寻的远方,正遥遥指向老房子里那把摇椅的方向。
二
老房子的第二层,是我和妈妈的房间,此处有一个大阳台、一块如镜的玻璃窗,有着全屋最好的视野。从这里看,甚至能够看到对面邻居家养的鸽子,偶尔从笼中挤出一只,便引得楼上楼下所有人为之惊呼。对面的房子里还居住着我童年最要好的女孩,她长我一岁,家里总是有很多和她亲昵的动物——鸽子、大狗。更令人不平的是,我家的阳台上只有一只母猫,神出鬼没,从不亲近人,只会在外婆呼唤它时出现。
我们小房的第二层却有更多令人艳羡的地方,我的妈妈仿佛是天生的园丁,闲暇时,她浇水、修剪枝叶、搬运泥土,从第一盆开始,一盆接一盆,这里逐渐被她栽满了花。很神奇,我从不知妈妈是从哪里变出了这些植物,初来时,它们都极小,有些甚至只是一根细细的绿秆,妈妈把它们一盆盆摆在阳台上,等上一两个月,最多三个月,花苞仿若悄然降临一般,自变粗的根茎中出现,露出一张幼嫩而美丽的脸。只要有花苞,无所谓颜色、品种、大小,我和姐姐都为之欢呼,尽管我们根本无法分清月季与玫瑰,但短暂的童年里,我们常会为另一个生命的绽放而感到欢欣鼓舞。
几十年前,外婆外公在砌这间房子的时候,已经生下了家中最小的女儿——我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女,他们不再有多余的心力去装饰它,这间房子成了一处水泥色的杰作,美却有缺憾。几十年后,母亲带回的藤蔓补全了它,这些细密、成网、分不出你我的植物攀着木棍生长,叶片卷曲,叶脉柔韧,浓厚得像一片绿云。它们爬行缓慢,却终年不停,铺满大半个灰色的墙壁,这面干燥的墙变得潮湿了起来。因湿气养育生命,偶尔会爬出一些瓢虫、天牛……甚至在雨天时,会从缝隙中爬出蜗牛,小型的生态系统在绿墙上建立起来,并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
妈妈的花被照顾得极好,还有一个缘由——阳台上的玻璃窗阻碍了高原烈日,仅仅筛出部分照在里头,阳光均匀地映着每一片花叶。我猜,这也是妈妈手下的花总是开得更大、开花周期更长的原因之一,它们享有柔和的光照、孩童玩耍泼洒的水珠、不时从一楼寻来的天然鸡蛋壳,我若是在此地生长的一朵花,也应该过着富足的一生。说来惭愧,我并不懂花,但花却从未在我的成长中缺席——每一次在阳台上,无论玩耍,还是发呆,抑或是在阳光下看书,我都要经过一盆盆花,它们为我奉献自己的美丽。
还要格外感谢花的滋养,花与美,在典籍、诗词中总是息息相关。佛家有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片花丛中,我看见了美的世界,也初次体验了对美的感受。
往年,妈妈尝试种凤仙,这种花被她称为“指甲花”——它成熟后,鲜艳欲滴,妈妈采下花瓣泡水,拿来给我涂指甲,被涂过的每一片指甲在阳光之下,显得亮晶晶,又红彤彤的。为了保持鲜艳的颜色,我不再跑到河边、山前玩耍,还把邻居家的玩伴带过来,求妈妈也给她染一染指甲。红指甲新奇,我们彼此对望,两颗脑袋亲热地挨在一起,心里还涌出更多对美的渴求。她像是想起什么,从花丛中站起身,说要带我去一个美的探求地。
所谓美的探求地,其实就是她家,那栋养着一群鸽子和一只狗的小楼。绕开咕咕叫的鸽子、打着哈欠的大狗,我们跑进了某个小房间,心里充满期待。在我迫切的催促下,她神神秘秘地翻出一个大包,两根小指小心地跷起,生怕蹭掉一点颜色。包里面装满了各色小瓶小罐,如上海女人香膏,叫不出名的珠光笔、口红,还有带着香味的粉扑。她把粉扑按在我的脸上,我用珠光笔在她窄窄的眼皮上画画,谨慎又大胆,不时地笑出声来,笑得大声了又要收住,生怕被她家里的人发现。
最终,我把她画得整脸亮闪闪的,她把我画得一脸红,我们对美是有概念的,也是无概念的,我们脸上的妆容一点都不美,但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无论怎么被其他人质疑,我们都觉得那是美的,美得像被精心涂抹过的指甲,让人舍不得洗掉。
现在想来,初次拥有对美的感受,要感谢花,感谢献出花瓣的凤仙,它开启了两个女孩对美的追寻旅程。就像一生之中的春潮期,潮水退去之后,花仍旧开,然而人的心境却变得不一样。如此,才有足够的眼光观花、观叶的美。至于那个和我一起分享美的玩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但只要看见对面那栋小楼,我就能想起那个房间,充满香气的粉扑,还有昏暗的光线之中,依稀可见的两张稚嫩却涂得光艳的脸。
值得一提的是,妈妈曾为这个阳台花费极大的心力——为了让植物更好地生长,也为了让我和姐姐更放肆地玩闹,她把这面巨大的玻璃窗装饰了起来,用的是一卷半透明的窗纸,上面的图案似在万花筒中见过,由对称、有序的碎片生出万般景象。又因为窗纸是半透明的,蓝色的玻璃变得更蓝,外面看不清里面,里面的人却拥有广阔的视野。
有人说,视觉记忆往往是最容易被淡忘的,然而,我的童年却因这片偌大的阳台而分外难忘:窗纸缝隙间,一群鸟经过,我把它们认成邻居家放飞的“鸽子”。它们飞翔的姿态舒展,万花筒般的玻璃窗纸将一只变成两只,又生出哗啦啦飞起的一片鸟群。鸟被日照驯服后,黑色尾羽被镶上金边,光与影的艺术由此诞生。我眯着眼,欣赏着这幅流动的画:和大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不同,它们的飞行速度正好,让人能看清它们一路飞行的轨迹,而它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溜到从窗纸缝隙中看不见的地方。如今想来,这群鸟不正像是那段悠然时光,既快又慢吗?我的童年也朝南奔去。
冬天结束,一月底,往往是我告别的日子。扎着小辫的朋友躲在妈妈后面,在人们的注视下,她格外不好意思,我们没能说上话。车窗之外是深蓝的天,我再次望见,有一群“鸽子”飞了起来,红嘴黑羽。但他们对我说,邻居家里没有飞走一只鸽子。妈妈说,那不是鸽子,是和它们很像的鸥,自西伯利亚来,它们穿越了大半个北半球,奔赴此地。
三
五六岁之后,我去了外地上学,一年回老房子两次;到十来岁时,舅舅、姨妈都从老房子里迁居出去,我和父母也因为学业和工作上的原因,改为一年回一次;再到成年,我们回去,就提着行李住进了舅舅的新房子。从此以后,更少回到老房子,再见已隔经年,我又见到了记忆中那块水泥色、未生长过花草的碑石。
一楼窗口的铁架锈迹斑斑,收银间已经被单租出去,变成了一家烟酒小店,过去摆放阿咖酚散、绿豆糕的架子,摆上了烟盒、矿泉水。厨房长久无人使用,索性用大锁封了起来,门上贴着新旧不一的胶条。姨妈说,厨房后有一条连通邻居家的通道,总有小偷趁着深夜潜入,只得一锁再锁,一封再封。我想起在过去,即使厨房前后门大开,也无人会乘虚而入,莫非锁反倒招惹了有心之人?
二楼是我和妈妈过去的住房,墙被外公外婆用水泥砌成后,未曾上漆,水泥剥落后就露出了里头的红砖。红砖下摆着十余个花盆,花朵凋敝,藤蔓失去弹性,泥土硬化,找不出曾有的生命痕迹,被后来的租客清理掉一些,再后来,他们大抵不再有耐心,一大半绿墙被粗暴地清理,仅有最上方还留存些冰凉、发直的黄色茎叶。
玻璃窗不知何时破了个大洞,用黑色胶带一圈圈草草地贴上,这里比原来没有植物时,要显得更加破败。我和妈妈的房间被租给了一对母子,他们是少数民族,母亲用最原始的绣花背带把孩子绑在身上,警觉地望向我们,她的旁边就是那扇玻璃窗。我没有靠近,玻璃窗不知何时被敲出个大洞,用黑色胶带裹起,阳光彻底无法照进来,花叶凋败,记忆中柔和而均匀的光照也一并封存在了岁月中。
对面的邻居仍在养鸽子,时过多年,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再没有见过那个女孩。
而他们如今豢养的鸽子,是我幼时那群鸽子生出的后代。女孩家如今做起了鸽子生意,不但自己养,还存几只肉鸽售卖。笼内,鸽子们挤在一起,偶尔发出几声鸣叫,无人再为它们的逃跑发出惊呼。笼外,剥了毛的鸽子被放在铁盆里清洗,黑羽褪去,红喙无影,和寻常的鸭、鹅一样,成了赤身裸体的吃食。
我和妈妈拒绝了邻居家的好意,坐在回新房子的车上,我牵住她的手,彼此似乎在沉默中说尽了感慨。她刚从老房子里捡出一双水晶鞋,这种鞋在市面上已经难寻踪迹。
曾经,她就穿着这双漂亮、防水的鞋在花丛中穿行,给它们浇水,花朵和藤蔓皆是除了我之外她最心爱的孩子。
车窗之外,仍有飞禽在天上穿行,我抬头望,两翼是薄薄的黑色尾羽,嘴上的色彩看不分明,它们结伴而行,越过高楼、山坡,朝北方飞去,高原的日光洒在羽上,镶上金边。偶尔迷失的一两只,在鸥群下方打转,又很快迁入队伍中。已经过了正月十五,我和妈妈也将回到另一个地方,等待下一个暖冬。
我仍好奇,这群候鸟之中,会有出生在这里的孩子吗,它们会想家吗?
(原载于2023年第2期《创作》)

苏晓,22岁,湖南师范大学 2022级电影专业(创意写作方向)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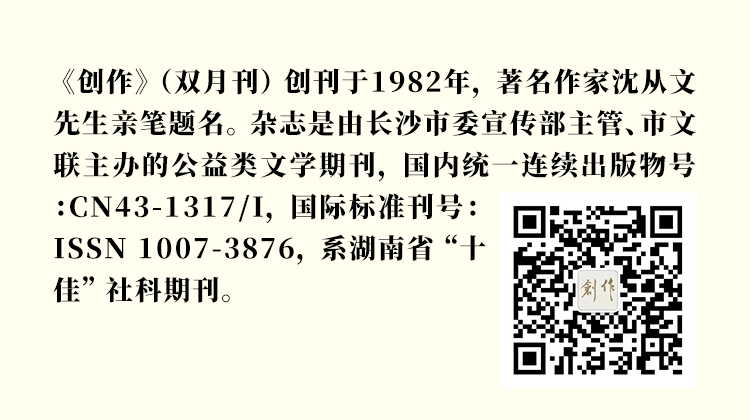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