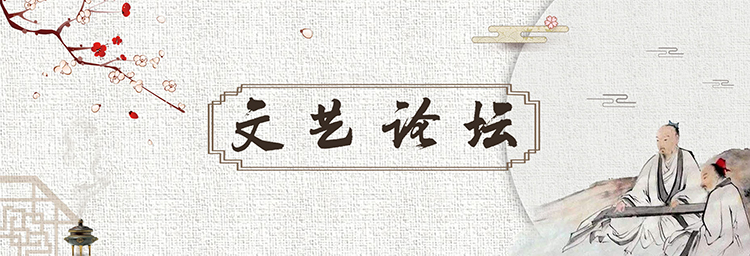

小瞌/摄
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德拉姆》的艺术生产考察
文/周海
摘 要:艺术生产与艺术创意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正以各种形式记录着人们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审美。纪录片在现代生活中呈现的不仅仅是机械生产,更多的是思想渗透与艺术加工后的品质塑造。纪录片作为影视艺术范畴下的产品,应将其置于拍摄过程中去具体实践,从社会视域下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中去互动共融,进而获得对影视艺术的最终解释。文章以田壮壮导演的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德拉姆》为例,对其创作历程、作品本身和美学意义进行艺术生产考察,让人们对纪录片的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进行重新估量与深度了解,从而推动纪录片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关键词:《茶马古道系列:德拉姆》;纪录片;艺术生产
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德拉姆》(以下简称《德拉姆》)是田壮壮导演在2004年前往云南、四川、西藏境内的横断山脉拍摄的有关马帮及其运输茶、盐、粮食古道的纪录影片。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并不受宠,人们对影视片的审美趣味明显更青睐于有人物性格发展、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故事片,由于国内观影市场多偏爱好莱坞生产的大片,纪录片的处境更加尴尬。田壮壮在《德拉姆》上映后的第一天就表达了担忧:“如果影片没有人看怎么办?这部电影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去看的电影,我明白电影跟音乐、文学一样,主流的、流行的东西在一段时间里总会卖得最好。”这个忧虑很好地说明了当前电影所处的环境——虽被视为精神产品,但其本质仍然可以说是文化消费中的商品。如果从历史或逻辑的层面考虑,市场语境中的艺术生产,就如同物质生产一般,产品需要走向市场,走向消费。然而,除了这种担忧,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有着天然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这或许与田壮壮本人所拥有的艺术素养和文化根基有关。田壮壮之后的言论又体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底气与胸襟:“但是,必须有人去做这项工作,不能让这些东西断裂,也许今天的人无法接受我的东西,可是我认为那都不重要,只要我认定了那是有价值的,我就会坚持。”事实上,《德拉姆》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获得2004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数字电影奖,而且在商业价值上收获颇丰——在国内外院线上映时,表现出超预期的票房成绩,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一
《德拉姆》是田壮壮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中国第一部使用“高清”数字技术拍摄出来的影片,被电影界评为“田壮壮一贯‘艺术影片’路线的一次延续”。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艺术生产是为资本创造价值,一切艺术品都具有商品的属性。艺术生产的目的乃是为资本创造价值,艺术品从某种层面来看,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难以摆脱其商品属性。而作为一部纪录片,或者说是艺术电影,《德拉姆》的生产并不像传统的物质生产那般,用于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自然属性上的需求。从精神生产的角度看,它遵循“美的规律”,换言之,就是基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利用现代科技,以创造性的思维去开发过去遗留的等已然存在的物质文明,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与视觉享受。同时,它也是一种记录时代的方式,用影视的艺术形式留存历史。《德拉姆》的创意拍摄在于打通云南、四川、西藏境内的横断山脉中古道的历史时空,发现大自然的生命规律与天然之美,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真谛。而以马帮运输茶、盐、粮食的古道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马帮就是交通运输的载体,以团队组织活跃在中国云南、四川各地。在这条运输的道路上,经过长期的车马往复,因各种物资的流通而形成了特定环境下的交通枢纽,也就有了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而要将这纵横几个省份的茶马古道的历史融合起来,以影视艺术的形式让人们清晰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是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的。这种艺术生产需要融入创作者思想、情感,遵循美的规律,才能使人们产生共鸣。马克思曾说过,艺术生产的本质,与物质生产有着根本区别,皆因“艺术生产本质上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是艺术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更多地包含着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观念、素质、修养、趣味以及心境等等极为复杂的心理精神因素”①。这就要求创作者尽可能地融合相关元素,使之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产出物。显然,纪录片《德拉姆》就是这样一部融入思想情感、深刻个人印记,并在美学创意上独具艺术特征的作品。在技术上,无论是对镜头、色彩、声音的选取,还是对主人公的挑选,都在田壮壮精心策划下呈现出高质清晰、思路流畅、情感饱满的独特性。不能否认的是,在投资运用上,《德拉姆》乃为资本运作下的文化商品,投入院线发行并获得一定的票房收益,是该片创制筹拍时的重要目的之一,亦即“为资本创造价值”。
从地理位置看,毋庸置疑,《德拉姆》的拍摄很有难度,对摄制组是一种挑战。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并邻,但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其中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梅里雪山三大山系形成三大峡谷,起伏绵延,地势险要,并且山巅终年积雪。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从峡谷中纵横而过,滔滔而去。由于气候使然,这里的森林和水资源非常丰富,有亚洲的动植物博物馆之称。虽有艰难险阻,却到处可遇奇美仙境,在这条神奇的“茶马古道”中穿行,为纪录片的拍摄增添了特别丰富有趣、震撼人心的素材。
当人们坐在影视厅感受《德拉姆》带来的令人震撼的奇观美景与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时,谁又能想到田壮壮为了拍摄记录云南滇西北怒江流域原住民的生活现状、率拍摄队沿怒江而上的艰难险阻?他们一路上风餐露宿,饮江水,沐天浴,屡历奇险,随马帮徒步至察瓦龙,再原途返回。虽有行走的辛苦,但途中的见闻更是触动着田壮壮的心弦,坚定了他拍摄的决心。五十多天的往返,云南滇西北怒江流域原住民的生活现状使田壮壮胸有成竹,当地各种特色与民族风情收录于镜头,让他满载而归。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的认知水平有时反而容易受到某种制约。在艺术的疆域,想象力变得能动而重要,人类思维的活跃离不开想象力与各种创造,扼杀了想象力,神话反而不可能再出现了。纪录片的特征是真实地记录天文地理、人与自然的种种。而为了更加艺术性地记录保存,使市场受众尽可能最大化,在镜头处理与技术剪辑上就需要作者把握好影片的思想主旨,既要保持纪录片的真实性,又要具有观赏性。在遵循美的规律中,纪录片要允许创意生产,以达到既定的创造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②于是,《德拉姆》既延续了纪录片的真实性特点,又在技术手段的更新中完成了它独具创意的艺术电影的生产。
二
马克思将诗人称作“生产者”,亦把艺术品视为“产品”。在此视角下,如果说纪录片《德拉姆》也是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导演田壮壮则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的角色。电影导演作为生产者,受物质生产规律支配。这就要求我们将艺术放在生产手段的结构下进行分析,尤其是放在生产关系与生产手段的结构下去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当下艺术的本质,客观且全面地研究艺术创作的目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能在院线成功上映,纪录片《德拉姆》必须达到一定的技术标准,而这牵涉到的技术问题亦是艺术生产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对于“艺术和技术结合”的探讨。在艺术创作阶段,根据艺术生产的目的,并以实现该目的而进行的技术选择,是难以避免的事情③。比如布莱希特对戏剧工艺技术的高度重视,本雅明的“艺术对技术的依赖性”等观点,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本雅明以摄影为例加以分析,把过去脱离大众的内容如春光、名人、异国风情之类的东西通过新的加工而呈现给大众,这属于“摄影艺术的经济功用”;把世界“由内向外按其本来面目”进行更新,则是“摄影术的政治功用”。在资产阶级“新客观派”中,则把这种经济功用作为粉饰生活的手段。与此同时,摄影技术也可以用来揭露生活的真实,赋予照片以革命性的使用价值。基于此,当我们把此视角放在纪录片《德拉姆》上,其经济功用和其他功用也在创作初期获得重视。比如《德拉姆》拍摄茶马古道的最后一支马帮,对于观众而言,这一题材独具“奇异性”,“最后一支马帮”会自然而然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德拉姆》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高清”数字技术拍摄的影片,技术手段的打磨让此艺术产品具有好的品相,为上座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看,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是对中国历史上特殊时期的创伤表达,纪录片《德拉姆》则是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影片。它既表现了中国人的顽强拼搏、不畏艰难、奋勇向前等一系列优秀的传统品德,同时也彰显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虽无法将其定义为对生活的“粉饰”,但在一定程度上,纪录片《德拉姆》的确展现了艺术作品的各种功用。
三
作为完全依靠科技发展才得以成形的艺术门类,纪录片《德拉姆》所处的时代,便是由本雅明所提出的“机械复制时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中,作者论述了“当艺术生产采取一种机械复制的方式,在美学上引起的后果是怎样的”④。它被分为正反两个方面:一为膜拜——韵味,二为复制——展示。本雅明把对艺术的接受态度归结为两种:一种是艺术品是为“膜拜”服务的创造物,侧重的是艺术品的“膜拜价值”,另一种则侧重于其“展示价值”。在艺术品的膜拜方式中,艺术以其原始和原生状态保留着其存在的真实性,即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这独一无二性便构成了艺术品的历史,而作为艺术品美学特质的“韵味”就寓于其中。
电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而在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导致了“传统的大崩溃”,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电影。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韵味”也就消失了⑤。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纪录片《德拉姆》的拍摄与定义,田壮壮并未被“机械复制时代”的观念所左右,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擅于突破与创新。他敏锐地感知到,在时间的淘洗中,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自然与生命,极富个性特色,不及时记录下来,很可能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他思考了机械复制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即既要保留“韵味”,又要能充分“展示”出其独特性,还能体现出社会与历史融合价值意义的作品。田壮壮大胆设想,以中国各省的茶马古道为拍摄背景,挖掘出这一历史道路上的“德拉姆”(藏语,意即平安女仙)。他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以云南丙中洛沿怒江而上到西藏察瓦龙的马帮为主线,沿途拍摄与追踪跨省的茶马古道,在天然的生态环境下,穿插各个小镇村落中发生的各种故事。这种沿途拍摄的现场感强烈,人物独特,景观奇美,真实地记录了这条茶马古道上的“今生”与“前世”,历史的氤氲气息与时代的鲜活气息在这里和谐共生、相映成趣。
同时,纪录片《德拉姆》的录制是采用亲历者的视角,让观众对古道两边人们的生活有一个真实体验。从感性上理解,拍摄人物的选择是《德拉姆》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以马帮的行走串联起沿途村寨中的人物故事,这种拍摄手段有点类似文艺电影的处理技法,虽算不上新鲜,却也和主题颇为契合。马帮生活原本就单调、平淡且艰苦,由于条件所限,摄制组大班人马显然也无法做到对马帮的长期跟拍,所以在《德拉姆》的拍摄进程中也就无法出现更多令人震撼的大场面。但正是这种平淡写实的记录更真实地反映了马帮生活的本来面目。《德拉姆》在剧情主人公的选择上,有着田壮壮导演深刻的个人印记,这样的创作方式虽在弗拉哈迪时代早已出现,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纪录片创作手法。这里的人物显然跟舞台上的演员有着本质的不同,《德拉姆》是以现实生活取材,选择的主人公不是专业演员,却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主角,他们不需要化妆师,不需要服装师,也不需要设计师,他们演出的“现时现地”就是最真实的自己。而演员表演的“现时现地性”变为导演和剪辑师的“蒙太奇性”,这也是电影作为复制时代的艺术而丧失“韵味”的表现,其现时现地性是不存在的。此时,美学的内容、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种种关系相互叠加在一起,影片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它便不再有纯粹的“美学意义”。
在当前大众狂欢、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语境下,纪录片《德拉姆》在影视领域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并不具有特别的典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技术标准和意识形态的表达还是能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参考。“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⑥,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时论述道。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影响或许具有积极的价值——人们的确要通过对影视艺术作品的欣赏来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通过观赏《德拉姆》,人们不仅沉醉于其考究的镜头表现,还会因为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而对生活充满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德拉姆》仍然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艺术作品。在记录相关地区原住民生活的同时,纪录片也对相关地域的高原地貌,以最新的技术手段,做了一次全景式的记录。上映后,其表现出的高原生态环境的自然与博大之美、原住民生存状态的坚毅之美,均引发观众诸多思考。可以说,《德拉姆》以影像的方式,记述了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些真实的存在,遵循着美的规律,完美地呈现出一部纪录片的艺术价值。
注释:
①②[德]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第5页。
③[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炳钧、陈永国、郭军、蒋洪生译:《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
④⑤[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李伟、郭东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第45页。
⑥[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作者单位:湖南卫视)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