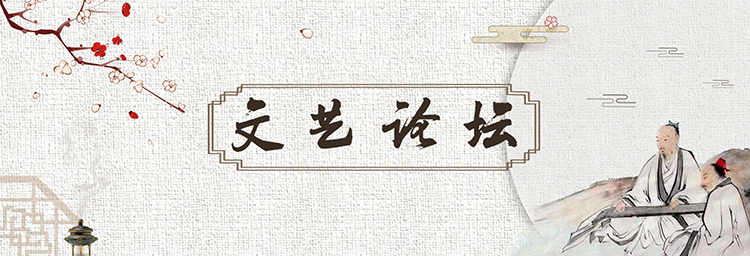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散文价值评估
文/王兆胜
摘 要:以西方个性启蒙为价值参照,思考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散文,这是长期以来的主要思路,其价值当然不可低估。然而,接续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散文传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自我生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意义,这是获得新的理解和中国智慧的关键,也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他信与自信的融通,这对于今后的散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现当代散文;价值评估;继承性;创新性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价值一向为人们所忽略。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四大文体中,散文天然地被排在后面,是作为文学的一个余数存在的,不少人认为没法归类的都可以装进散文的“筐子”。路遥将散文作为一种技巧性的文体,认为写散文只是写小说之前的文字准备与训练。{1}余光中将散文视为“雕虫小技”,认为不足以观。{2}就是散文创作者和研究者往往也对散文很不自信,觉得散文的文体独立性不强,写散文是一种休闲和无奈之举,是在小说创作高度紧张之后的一种舒缓放松。事实上,这都可以归因于缺乏文化自信,尤其是没有散文的文化自信,从而导致作为文体的散文失去了意义。只有改变这一状态,才能重审散文的价值,看到散文不可否认的独特存在意义。
一、中国文化自信与散文价值评估
在中国古代,散文是有文化自信的,所以,中国有“诗文大国”的美称,诗文传统亦如长江、黄河一样源远流长。小说的出现则是很晚的事,到明清之际才开始兴盛,且作为末流小技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西方文化在中国逐渐获得了制导性,西方小说的地位开始上升,散文的地位快速下降。可以说,散文的边缘化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走低与不自信直接相关。不过,与此相关的还有诗歌,中国古典诗歌为白话新诗所取代,从而带来声势浩大的诗界革命。其实,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值得反思,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也需要重新评估。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并存,但文化自信是不能丧失的。以往,中国是不缺乏文化自信的,汉唐雄风是何等的气魄,但到了近现代,这种自信逐渐丧失。先是认为器物不如人,后来觉得制度不如人,再后来则是思想文化不如人,{3}以至于出现吴稚晖、鲁迅、钱玄同等人更为偏激的观点:中国文字不如人,所以,要废除汉字;中国人不行,所以,要换血换种。钱玄同直言:“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此等书籍,若使知识正确、头脑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堕其玄中;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4}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并表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5}这些言论当然均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也不能简单进行理解,但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态度是明显的。这种文化的不自信,必然导致对中国古书、古代文学,也包括对散文的不自信。
二是对中国现当代散文的不自信,导致简单否定其价值。除了鲁迅、郁达夫、季羡林等人外{6} ,中国散文在不少人那里一直有落伍者之嫌。比较典型的是余光中,1963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剪掉散文的辫子》,其中对散文家与“散文”的现状极为不满,甚至用各种恶言加以贬低。他说:“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当然远胜于散文家。”“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的‘散文诗’了。”为此,余光中还用“花花公子的散文”“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的称呼来恶心散文。{7}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受到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影响,文学追新求变成为一种风潮,看着朦胧诗、先锋小说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向西方学习各种花样翻新的技巧时,许多人坐不住了,开始反思并质疑散文,还形成自我质疑,于是发出了“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之类的绝望呐喊。有作者对此表示:“散文,在江河日下之中。”“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散文’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不管散文做出怎样的努力,它最终是不会获得成功的。”“散文——一直被误作文学的散文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文化使命,它应当寿终正寝了。”“当代文学不再需要散文了,这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事实。”{8} 这是至今笔者所看到的,关于散文消亡论最悲观绝望的文章,透出散文研究者的心态和面影。
三是从中国文化自信和散文自信的角度理解,散文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当中国五四新文学全力批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时,也有一些所谓的保守顽固派一直全力以赴进行维护,希望守住中国文化的根脉,这在林琴南、辜鸿铭、林语堂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往,人们总是站在“新”的角度否定这些人的“旧”,但站在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精神角度看,那些激进派的激进言论又有些荒唐可笑。以林语堂为例,早年在五四时期也是激烈的反传统派,他甚至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提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9}不过,随着去国外生活,经年日久接触欧美文化,林语堂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并且是根本性的变化,他一改对于欧美文化的崇拜,也去掉了所谓的“哈佛气”,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敬意。据林语堂次女林太乙说,她们一家人刚到美国,穿旗袍的母亲及其“中国人”的形象招来美国人围观,在孩子的惴惴不安中,林语堂对妻女说:“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10}确实如此,对比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美国文化还只是个孩子,甚至连孩子都算不上,一句“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包蕴了多少文化自信。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写过《秋的况味》《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辉煌的北京》《年华渐老——生命的旋律》等作品,极力渲染中国古老文化的精神气质,那种成熟、镇定、从容、优雅深具诗意情怀,可以克服、穿透、消融所有的生活、人生、生命的坚冰,进入一种化境。林语堂有这样的诗心,他写道:
无论国家和个人的生命,都会达到一个早秋精神弥漫的时期,翠绿夹着黄褐,悲哀夹着欢乐,希望夹着追忆。到了生命的某一个时期,春日的纯真已成回忆,夏日的繁茂余音袅袅,我们瞻望生命,问题已不在于如何成长,而在于如何真诚度日;不在于拼命奋斗,而在于享受仅余的宝贵光阴;不在于如何花费精力,而在于如何贮藏,等待眼前的冬天。自觉已到达某一境地,安下心来,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自觉有了某一种成就,比起往日的灿烂显得微不足道,却值得珍惜,宛如一座失去夏日光彩的秋林,能保持经久的风貌。{11}
这种散文笔法是一种中国文化精神的写照,是真正懂得了人生真谛,以生命的智慧开悟后的升华体验,这是西方悲剧意识形成的心灵撕裂状态很难理解的。其实,鲁迅的《朝花夕拾》、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孙犁、季羡林、张中行等人的散文都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如季羡林写过多篇论老年的文章,其间充满中国文化的智慧,他说:“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我们应该有一种正确的生死观,正确的少年与老年观。我觉得,还是中国古代的道家最聪明,他们说:万物方生方死。一下子就把生与死,少年与老年联系在一起了。”{12}这样的认识是充满中国文化自信的,散文也就富有了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
还有,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看,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更多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13}因为诗歌、小说、戏剧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以反传统的激烈态度为前提;而“散文”这个相对传统的文体则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因为“创新”是很难的,邯郸学步很容易导致鸡飞蛋打,也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讲究“述而不作”,歌德本人也坦承,自己的原创是很少的,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上是站在前人的肩头达成的。因此,只用西方的创新性来衡量散文是一个误区,也很容易夸大创新的作用,忽略中国文化的继承性问题。因此,散文在继承性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以此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从中国现当代散文与中国传统散文特别是小品、随笔、抒情性等方面,可以找到其内在关联性。如关于亲情散文,古今有共通的母题,很难讲所谓的创新性,但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到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中》,从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到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到张清华的《桃花转世》,都可见出情感的真挚动人与感人肺腑。
总之,以西方文化评价中国现当代散文,很容易走上片面追求个性与创新的误区,甚至会简单否定对中国传统的继承性。只有在中国文化的源与流中,中国现当代散文才能找到归宿与底蕴,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根脉与力量延伸。基于此,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断流的所谓先锋诗歌与小说,其价值才是值得怀疑的。目前,许多先锋文学作家重新调整创作,向传统回归与致敬就很能说明问题。{14}
二、西方文化激活中国的散文传统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理解现当代散文,看到其价值意义,这有助于避免西方文化的简单介入、理解和误解。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现当代散文不可能成为传统的复制,更不是没有新意的沿袭,这就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是向西方文化开放、借鉴、吸收的过程,也是自我革命的一种创造。
个性化、人性化、生活化的散文在中国现当代得以弘扬壮大。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和谐为其主要基调。西方启蒙文化重在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强调自由、民主、科学理念,这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有着深刻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认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15}所以,有个性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特色鲜明,从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巴金的《随想录》再到钟鸣、刘烨园、苇岸、冯秋子、刘亮程、王开岭、蒋蓝、彭程、祝勇、周晓枫、杨献平、杜丽、黑孩、黑陶等人的“新散文”,都很有代表性。人性化与生活化的散文更多,像刘亚洲的《王仁先》、耿立的《赵登禹将军》都是从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现场感进行西方化个性启蒙。林语堂的散文更是如此,它写得放逸潇洒,追求“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在个性化、人性化、生活化上达到了美妙的调和,仿佛进入了超然境界。在《论性灵》一文中,林语堂这样写道:“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因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而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乖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人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16}在此,不论是自我个性的张扬,还是意境的营造,抑或是情绪的变幻以及遣词造句的灵活多变,都透出西方现代性特色,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郭沫若塑造的女神,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浪漫主义的青春热情、奋发有为、开拓进取成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新基调。毕竟在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禁锢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封闭保守甚至腐朽的气息存在,这是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以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进化论进行突破的关键。其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如春日新花一样绽放,这是对故步自封的老旧文化的一次涤荡洗礼。梁启超以其火热的激情、强大的逻辑和理想主义风范,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7}李大钊的《青春》更是在温润中充满阳刚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作品写道:“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8} 这种天地情怀是可以包纳宇宙的,青春气息确如朝阳般光芒四射。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魏巍的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也都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奋发向上的伟力。还有《新青年》《新潮》以及新文学、新小说、新诗、新散文等都是以“新”命名的,大大增强了新鲜的活力与气息。
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增加了亮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巨大作用,它也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以往,我们比较重视个性启蒙散文,相对忽略先进的革命性红色散文,或者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重视,改革开放后又有所调整,甚至一度出现这样的状况:对革命现实主义散文评价不高,以个人启蒙叙事进行取代或遮蔽。事实上,充分反映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不在少数,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红色文化的旗帜就已经高高飘扬,成为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和新精神的胜利。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唱赞歌更成为时代声音,这在巴金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向着祖国的心》、朱良才的《朱德的扁担》、袁鹰的《井冈翠竹》、路遥的《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作家的劳动》《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等系列伟人散文中,都有深刻的体现。但这种散文的文化自信现在还没有被发扬光大,在有的个性化、一个人的文学史、散文史中受到严峻挑战和质疑。
西方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现当代散文意义重大。其中,有的作品虽然存在表面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局限,但整体而言,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在中国散文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也有灵魂重塑之功。
三、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文化自觉意识
整体而言,中国现当代散文在文化选择上还缺乏理性自觉意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困惑,甚至出现盲点误区。不确立新的文化自信,保持清醒的文化理性自觉,今后的散文创作研究很难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与无限潜质。因此,站在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理解文化自信,散文研究就会有所突破,得到创新发展。
关于散文的文化化问题。有人说,“文化化是一项长期的、稳定的行为,是一点点渗透进消费者印记中的,愈是持续化的传递,才愈能够显出品牌的文化魅力”。{19}散文是需要文化作为强有力支撑的,散文的文化化更强调以文化的方式进行化解,从而具有文化品质、高度、境界。比如,有的散文没有文化,虽然关注了现实问题,但文化含量不够;有的学者散文沉溺于资料的堆积,没有文化含金量,只停留在表面的文化;还有的政治散文没有将政治转换成文化,也就容易显得贫乏空洞,甚至陷入政治说教。还有文化选择问题,没有通透的文化理性与智慧显现,许多散文就会处于文化的板结状态,被自己设定的心结缠绕。还有不少散文在城乡、中西文化选择上一直处于困惑状,作品不能穿越时代、历史、国家、人类前途命运中的障壁,有的简单否定现代,有的沉溺于乡土文明不能自拔,导致滞后于时代和远离社会的巨大变革。在新时代,国家、世界、人类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散文如若不能以文化成,有前瞻性眼光,必然失去引领性和文化意义。还有,散文需要克服世俗化倾向,有崇高境界与天地情怀,这是文化的更高要求。以刘亚洲的《王仁先》与耿立的《赵登禹将军》为例,它们虽然是个性启蒙的重要文本,也在人性深度描写上有所突破,但用世俗解构崇高、以个体消弥集体、以放任无视军纪,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让散文“文化化”的主要原因。{20}散文仿佛是一堆干柴,需要用文化点燃,特别是显现出文化化的光焰,这样才会富有深度和长久的艺术魅力。
关于散文的人化、物性和天地情怀问题。“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特别强调“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21}于是,人——一个大写的解放的人被凸显出来,这相对于古代忽略人来说是一种突破和超越。但是,在过于强调“人”特别是放大人的欲望之后,人的异化问题就出现了。与此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华带来的则是,万物皆在脚下,甚至目中无物,也没有天地自然和天地大道。这也是生态文学尤其是生态散文全面反思的方面。作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它必须是人与物、天地人心互为辩证地进行融通,然后再造和发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是在“人的文学”底下,“物”严重地被忽略,即使写到物也多是拟人化的,是带着人的思考及其偏见的物的存在,这样的描写大大遮蔽了物,也不可能达到物性与天地大道的层次。因此,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现当代散文是一个“物”被严重降级和忽略的空洞存在,更多的是有个性的人,甚至是一些焦虑不安、张牙舞爪、变态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在“人的文学”观念下,也仍有散文关注天地万物,并从中发掘其天地道心,早先鲁迅的《朝花夕拾》是这样,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也是这样,近些年的物性描写在散文中越来越多,也有从中探讨天地之道的作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能透入万物体性,以物为师,倾听来自天地的心声,特别是有天地情怀、宇宙意识的还是比较少的。李大钊的《青春》中多次提到“宇宙”,说明他的时空观是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在天宇中穿行。林语堂曾表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22}其中也是有天地观照和宇宙意识的,特别是用“一心”进行评说,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不失天地宇宙的规约,其中充满放逸与自律的张力效果。
关于散文的跨文体文化自觉问题。法国布丰说过:“风格即人。”“风格是应该刻划思想的。”“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都是真理,对于人类智慧来说,这些真理比起那些可以构成题材内容的真理,是同样有用,而且也许是更为宝贵。”{23}在此,将风格与人的思想、精神、真理相联系,是切中要害的。同理,散文文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容,是有文化的内容。没有文化自觉作为前提的散文文体既不可能成立,更无法进行跨越。换言之,散文文体永远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绝缘的、技术性的,而是一个多棱体被阳光照亮折射出五彩缤纷。一方面,散文有“内跨”的问题,随笔、小品文、杂文、诗的散文等相互交融,至今仍存在着混杂甚至模糊的状况。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互相联系的。不过,如何在这种联系中规范其边界,这是需要努力探讨的,否则就会导致文体失范甚至破体。最典型的是,不少人将小品文与散文画等号,也有人将随笔与小品混用,从而导致散文的概念不清、文体混乱。另一方面,散文还有“外跨”的问题,散文诗是散文与诗的跨界,散文化的小说是散文与小说的融合。还有将散文与电影、新闻、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进行会通,产生所谓的经济散文、政治散文、军旅散文、文化散文。这也是为什么汪曾祺、史铁生的散文常被当成小说发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散文化的小说,或者是小说化的散文。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散文的文体知识,也需要文化判断力,还需要审美鉴别力,更需要哲学修养。如我们提出散文是一种平淡、自然、均衡、优雅、自律的文体,其关键在于自我形象的塑造,这本身就需要人生哲学和人生智慧,不只是文体本身的问题。还有,不少人反对散文的真实性,强调散文的虚构及其虚假,这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人格问题,与对世界人生和人性生命的理解有关。当前,散文文体特别是跨文体写作有放任自流之势,其必然导致碎片化,消解散文文体的尊严和神圣,也流放散文的真情实感,使之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虚无。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说到底是要有稳定、健康、积极、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作为底座。一个没有信仰、道德律、美感、光泽的人是没有办法谈论文化的,更不要说强调文化自信了。有了文化自信,才有可能支撑起散文的绿色写作,写出光彩照人的美文,就像李大钊的《青春》那样。在新时代,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也应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开拓创新发展超越,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与境界。
注释:
①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2}{7}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选自余光中:《桥跨黄金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第359~369页。
{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见《饮冰室合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4页。
{4}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摘自《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四期。
{5}鲁迅:《关于新文字——答问》,选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6}鲁迅曾表示:“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选自《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6页)。季羡林则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散文成就远高于诗歌和小说。季羡林:《漫谈散文》,选自《季羡林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页。
{8}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9}语堂:《翦拂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10}林太乙:《突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选自《林家次女》,西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2页。
{11}{22}林语堂:《八十自叙》,宝文堂书店1991年版,第69页、第112页。
{12}季羡林:《再论老年》,选自《季羡林全集》(第8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13}参见王兆胜:《散文文体:中国传统文化基团与密码的载体》,《学术研究》2015年6期。
{14}魏韬:《高远:向传统靠拢的先锋文学写作者》,《文化艺术报》2020年1月18日。
{1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选自《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16}梦琳等编:《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1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五》,摘自《饮冰室合集》(第 1 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18}李大钊:《青春》,选自《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93页。
{19}刘伟华、林江华:《茶产业文化化视域下的新时期茶馆经营》,《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
{20}王兆胜:《国体散文与观念变革》,《文艺争鸣》2021年第7期。
{2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选自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3}布封:《论风格》,选自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3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AZW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