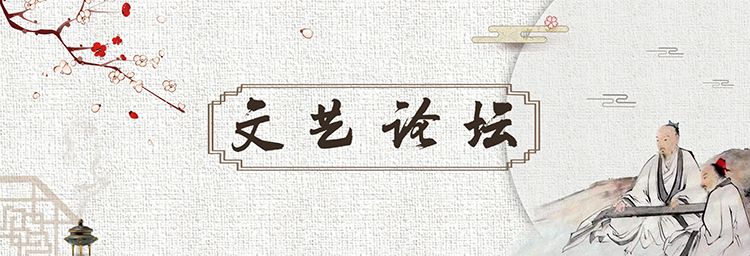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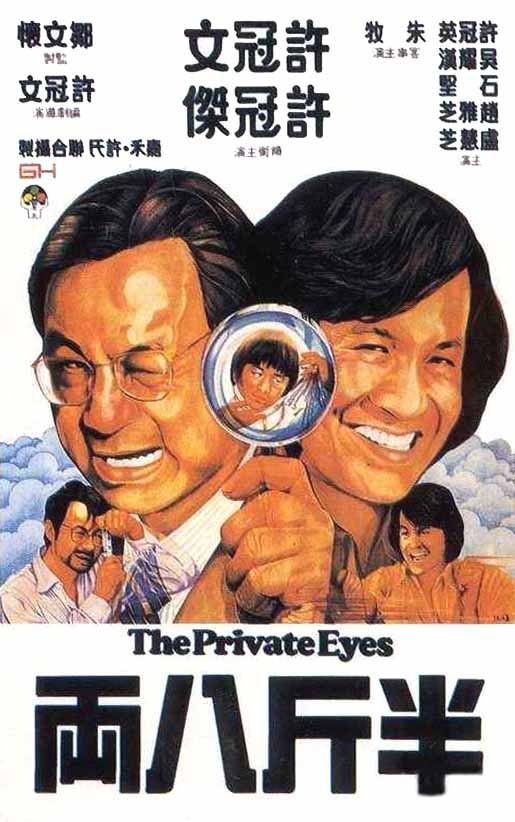
许冠文喜剧:跨文化奇观、美学关联与现代性转向
文/赖荟如
摘 要:20世纪70年代末,许冠文创作的《半斤八两》成为日本市场的现象级外语片,更将香港类型电影体系中的另一支重要流派——喜剧片引入日本观众的视线中。许氏喜剧在日本市场的票房奇迹,首先得益于动作奇观的“去谜化”作用,这赋予影片作为“吸引力电影”的跨文化优势;其次,许氏喜剧与日本本土电影形成美学关联及深层指涉,较之同时期的外语片,更贴近日本受众的审美趣味;此外,许氏喜剧标志着香港粤语喜剧的现代性转向,亦为日本观众提供了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两分法”之外的、思考现代性的方式。
关键词:许冠文喜剧;跨文化传播;形式美学;日本市场;现代性转向
在大卫·波德威尔看来,香港电影,其实是出色的区域性电影,“(香港电影)从本土跨出全球,其间理应还有一中间地带,那便是本土以外的地区,是影片及其影响力扩散时形成的第二个同心圆”。{1}香港电影从20世纪50年代高速发展至70年代迎来黄金时期,向来仰赖东亚、东南亚外埠市场的力量。在日本市场,邵氏电影公司率先于1954年与日本大映公司合作拍摄影片《杨贵妃》,以合拍片促进香港电影在日本的布局。1960年代中期,邵氏更推动港、日双方的导演、演员与技术人员赴日、来港交流,学习日方的拍摄技术与管理理念。然而,邵氏的诸多努力仅仅是内向地提高了拍片的效率与电影产量,并未对日本市场的开拓起实质作用。截至1970年代初,仅有《清宫秘史》《小白菜》《江山美人》3部香港电影在日本上映。{2}直至1974年嘉禾公司将李小龙电影输出日本市场,《唐山大兄》《精武门》以10.9亿日元的票房{3}终于打破香港电影在日本的困局,并掀起了持续的“功夫热”,使香港电影在日本市场的发展于1970至1980年代达到鼎盛。至今为止,在日本院线获得高票房(票房达10亿日元)的香港电影,大多都为1970、1980年代的影片。而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冠文编、导、演的《半斤八两》以10亿日元的票房成绩{4}在一众的动作电影中异军突起,更将香港类型电影体系中的另一支重要流派——喜剧片引入日本观众的视线中。
1979年,嘉禾将许冠文喜剧命名与包装为“Mr.Boo”输出日本市场,《半斤八两》收获热烈反响后,《卖身契》《鬼马双星》《摩登保镖》作为“Mr.Boo”系列续作在日公映,接连引发观影热潮,此外以录像带形式发行的《铁板烧》《神探朱古力》《鸡同鸭讲》《合家欢》等片均有不俗的口碑与市场表现。在笔者看来,日本市场的“Mr.Boo神话”已成文化现象,与世界范围的“李小龙神话”“成龙神话”相比,许氏喜剧在日本市场的票房奇迹有着更为独特的研究意义。总的来说,许冠文喜剧的成功与其在电影的跨文化策略、形式美学与主题意涵方面的探索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对许氏喜剧的文化竞争力进行探究,以期从“Mr.Boo神话”背后总结一定的经验与规律。
一、跨文化传播:“动”的喜剧
与奇观的“去谜化”
在内在意义上,港产喜剧以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语言风格、生活方式等)和价值观彰显在地性与主体意识,令香港观众在银幕上“看见”、指认作为共同体的自身,完成文化身份的自我形塑。然而,港产喜剧所奉行的本土主义,又使之成为一个“以文化反文化”的“谜化”的文本,其向内开放的喜剧性,会在某种程度或某些信息层面上形成一个谜,使得处于这一文化空间外部的群体被隔绝开来,进而稳固香港人面对本土文化与话语体系的优越心理。{5}例如,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在本土与海外市场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直至新世纪两部功夫题材喜剧《少林足球》《功夫》的出现,周星驰电影才显示出其海外影响力,足以证明“谜化”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折扣。
客观地说,许冠文的电影不乏俚语笑料、方言歌曲等“谜化”元素,但亦看重奇观的跨文化的吸引力及其对“谜”的消解作用。在日本院线公映的4部许冠文电影,展现出与汤姆·冈宁提出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相似的气质,其重点在于通过对视觉特性的操控以及直接的呈现和展示行为,诉诸观众的注意力,将能量向外倾注于得到认可的观众,以令人兴奋的奇观提供快感。{6}日本外语片市场亦表现出对奇观电影的明显偏好:80年代,票房突破10亿日元的65部外语片中,动作片多达37部,科幻片、歌舞片次之。这与动画、喜剧电影占主导地位,动作片影响微弱(在130部高票房电影中仅占7部)的日本国产片市场形成鲜明对比。{7}这意味着,日本市场对于以动作片为代表的奇观电影的需求,主要由外语片满足。而许冠文的电影正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动作成分在喜剧中作用。日本媒体人佐保畅子指出,70至80年代风靡日本的许冠文喜剧,改变了日本人对笑剧概念的理解:“比较日与港的‘笑’有什么分别,简单地说,日本传统的‘笑’是‘静’,相反地‘Mr.Boo’的‘笑’是‘动’。”{8}具言之,日本传统笑剧,如以口述故事为核心表演形式的“落语”(Rakugo)或双人喜剧“漫才”(Manzai),本质上都属说听(verbal)的幽默,更为注重演员的语言、音调等对喜剧效果的表现,肢体动作居于从属地位。即便是喜剧电影,重点也往往在于说听性笑料,如喜剧演员伴淳三郎、花菱阿茶子总是在情急之下喊出“阿佳帕!”“简直是乱套了!”,将从困境中逃脱的情景,用语言而非动作表演出来。{9}与之相比,许冠文的电影注重笑料的视觉呈现,对身体动作的开发与运用是主要的呈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许氏喜剧的动作化一方面承接喜剧、功夫片两支重要流派,对其后的功夫喜剧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则强化了香港喜剧电影的奇观性质,《半斤八两》在日本市场的票房成绩证实了奇观策略在跨地域、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有效性。
所谓许氏“动”的喜剧,首先体现为喜剧中动作的专业化倾向,如《半斤八两》引入“高空逃生”情节,这一“险极生乐”的手法在《卖身契》《摩登保镖》里屡试不爽,更成为此后成龙电影的代表性场面。《半斤八两》以洪金宝任动作指导,吴宇森任策划,亦说明了许冠文电影在动作表现形式方面的尝试。其次,许氏喜剧中喜剧效果的营造,关键在于动作呈现的密集性。电视制作出身的许冠文,在“无线电视”(TVB)《双星报喜》时期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喜剧编剧方法:“22分钟时段里,除了许冠杰唱歌占3分钟,一个短剧占五分钟外,所余的时间,需由28个有分量的笑话组成。”{10}于许冠文而言,转投电影领域意味着将这一“拆解”策略应用于90分钟的电影中,当中的语言笑料基于媒介特性被转换为强调动作的视觉笑料。许氏喜剧正是以连缀的动作奇观制造应接不暇的喜剧性时刻,令观众忽略叙事之单薄,其动作设计密集且富于变化,具体表现为几种形式:其一,以巴斯特·基顿式的追逐、打闹模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营造滑稽或机智的喜剧情境。其中,追逐、打闹等非叙事因素,或与叙事性相结合,如《半斤八两》《摩登保镖》的故事设定(侦探、安保模式)为“追逐”提供了逻辑的合理性,使之成为一种架构故事的方式;或独立成篇,如《卖身契》以碎片化的动作笑料堆砌了一出贯穿影片始终的追逐戏,重申许氏喜剧重奇观、轻叙事的特质;在另一些情况下,追逐、打闹戏仅仅作为悬置叙事的华彩片段(《鸡同鸭讲》中“鸡鸭乱斗”场景)。其二,以夸张的手法表现漫画式的身体与动作,主要呈现方法有二:一是在“模仿”情境中突出喜剧动作的“卡哇伊”(Kawaii)向趣味,《半斤八两》的“鸡体操”、《摩登保镖》的影子戏、《神探朱古力》的乔装段落以及多部影片中的“米老鼠式音乐”(Mickey Mousing)皆是例证;二为展现角色身体的极端状态,如伤残的肢体(《半斤八两》《摩登保镖》里腿、手的受伤)或“陌生化”的身体(《卖身契》的人体标靶,《摩登保镖》中手与身体的分离)。其三,强调动作场面的重复性,在情节的“对称”与巧合中制造反转的笑料。许冠文在《半斤八两》里追回钱包后反被警察追捕,意外落网,生动地演绎了“白费功夫”“自投罗网”等情节带来的喜剧效果。
许冠文电影置经典叙事电影那种按照故事的因果逻辑、人物的心理动机而线性发展,最终统一于一个完整、闭合的结构惯例于不顾,转而强调人物的喜剧性表演、身体动作所形成的视觉奇观对观众的吸引力。奇观的出现、变化与发展带来了视觉快感的不断“升级”与无限延伸,许氏喜剧正是以这种疯狂的速度魅力,令电影成为一种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主动追逐观众的目光游戏。如《半斤八两》中主人公利用特制相机偷窥美女,却因太过入迷而随偷窥对象一起落入泳池,该场景的笑料并未止于此,又抖出“西装遇水缩短”的包袱使人物的窘况升级,令观众捧腹的同时,塑造出角色好色、寒酸吝啬的生动形象。类似地,在本片的一场跟踪戏中,许冠杰饰演的实习侦探上演惊险刺激的追车场面,制造出一连串夸张的撞车奇观:汽车的保险杠、风挡玻璃、车盖接连报废。在此,纯粹的视觉笑料、物理景观代替叙事性因素构建情节,滚雪球般地令喜剧性不断增生。而后守财奴老板拿出计算器统计财产损失,计算器因运算过载,火星四溅,成为将喜剧效果推向极致的“点睛之笔”(Punchline)。上述两场戏是许氏喜剧的创作模式——“度桥”(想点子)的体现:将奇观按照情景喜剧的逻辑组织排列,每一个笑料都是为了更大的笑料做铺垫,从而呈现出一系列游离于叙事时间之外的,直面观众的“展示”动作。此外,许冠文电影所频繁使用的画面定格、段落间“划像”过渡等手法,使得影片的时间呈现断裂、离散的状态,这一分明的中断感,宣告着许氏喜剧本质上是对奇观、奇观段落的展示,观众的期待也由叙事电影的观影沉浸感与幻觉转为对奇观的追求。
除逗笑的表演、动作之外,许冠文喜剧亦注重电影镜头自身的视觉吸引力。在冈宁那里,早期电影的电影化手段之于观众是新鲜的,它本身即构成了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吸引力。当特写镜头、慢动作等电影语言变得不再新奇时,其吸引力来源于与表现内容的紧密联系。《半斤八两》中的烹饪段落富有巧思地将视觉动作与运镜思维结合:在这场戏中,主人公将电视健身节目误认作烹饪节目,出现了给鸡肉做体操的滑稽一幕。许冠文在长镜头中组织深度空间(deep space)内部各要素,使笑料在前景的“鸡体操”与后景二人认真健身的画面之间产生,其巧妙之处在于,将本应是声画之间的矛盾(健身节目的声音与“鸡体操”的画面)转换为纯视觉的矛盾,如此,即便没有电视声音作提示,观众也能准确地从镜头内部的反差中捕捉到笑点。进言之,这一视觉上的处理消解了语言隔阂可能来带的文本的“谜化”,营造出放之四海皆准的吸引力奇观。如许冠文所言:“我在《半斤八两》做了一个实验,完全用视觉思考,减少对白,希望影片可以去到全世界,《半斤八两》是成功的第一步。”{11}
二、形式美学:搭档策略、即物性与MV美学
许冠文喜剧在日本市场的受欢迎,亦在于其在人物、动作、音画设计等形式层面探索,并契合了日本观众的喜剧消费习惯与审美趣味。
首先,在角色关系上,许氏喜剧展现出与日本传统艺能“漫才”相似的喜剧策略。类似于“漫才”里“找茬者”(tsukkomi)和“装傻者”(boke)的角色分工,许氏喜剧围绕许冠文、许冠英形成了“一精一傻”的固定搭档模式:许冠文通常扮演刻薄悭吝的老板,对许冠英饰演的笨拙伙计百般刁难,由此,笑料来源于性格反差极大的搭档之间的整蛊和斗法。“找碴者”与“装傻者”间口头的误会、斗嘴等,在这里进一步呈现为动作上的冲突与笑料。
其次,许氏喜剧的动作设计彰显出一种与日本人的“即物”{12}思维相呼应的实用主义特质。具体而言,许氏喜剧强调角色行为的机动与机智,由此展现出一种应势而谋、顺势而行,注重实用与变通的“即物”美学。许冠文电影中的身体动作具有应情景的随机性,如《半斤八两》里,窃贼在现代的超市里使出一套黄飞鸿的“五形拳”。“厨房大战”场景中,香肠串、鲨鱼齿等食材被用作打斗的武器,笑料围绕动作与其发生空间的矛盾性展开,在“不和谐”的喜剧情境中,凸显出角色根据实用需求改造环境的能动性。另外,对道具的意想不到的开发与利用,在电影中处处皆是:马桶疏通器可以成为绝处逃生的利器(《摩登保镖》),魔术道具作为身体的延展,生发出非常规的喜剧性(《卖身契》),不一而足。可以说,许冠文的电影标志着香港喜剧的动作由“周全完整性”向重视自由机变的“无因果随意性”的转变,亦是日后的无厘头喜剧的雏形。{13}
此外,在音画设计上,1970、1980年代的日本电影注重以现代的视听手段拓展影像的多重内涵,体现之一便是充分发掘电影歌曲(主题曲、插曲等)对影像画面、气氛的烘托和诠释作用。《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人证》(片尾曲《草帽歌》)、《阿西们的街》(插曲《阿西!阿西!》)将电影的主题与情绪高度浓缩在2至3分钟的“音乐视频”(MV)里,丰富了观众在听觉层面的感知。当MV美学在电影中蔚然成风时,许氏喜剧切合时宜地进入日本市场。在《半斤八两》《鬼马双星》等片中,许冠杰演唱的流行歌曲与影像的蒙太奇、视觉笑料相辅相成。《半斤八两》的开场片段便是粤语歌曲、市民喜剧在音画上的出色结合:无声画面展现一组高楼镜头后,许冠杰的《半斤八两》随之响起,写实的街头影像显露出现代摩天大楼之外的,更为异质的世界。在此,低下阶层趣味的俚俗歌词、具感染力的演唱,配合着电影独特的运镜,如以高角度镜头俯拍街头来往的市井小民,贴地镜头呈现高跟鞋与破洞布鞋的所指的对比,道尽草根阶层生存的辛酸无奈。许氏电影与音乐一方面切中时弊,讽刺老板尖酸刻薄,替打工仔发声(“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家阵恶揾食”);另一方面又以超然的姿态表现一种“认命”感(“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是这种“双重束缚”,矛盾地揭示了一种辛辣与犬儒并存的时代情绪。{14}进言之,许氏喜剧中影像与音乐的融合,不只是单纯的形式层面的问题,而是以其在题旨与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指向了MV美学的更高范畴。
在文本外部,我们发现,许冠文1970至1980年代的作品序列呈现出清晰的创作路径的转变,即从早期以《鬼马双星》为代表的闹剧,“落实”到《半斤八两》《卖身契》等具有写实精神的市民喜剧,而后又发展出《鸡同鸭讲》《合家欢》等兼具现实性与情感性,略带温情、感伤气质的人情喜剧。重要的是,这一转变与日本喜剧电影的发展脉络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具言之,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古川绿波、伴淳三郎、花菱阿茶子主演的闹剧是日本喜剧片的主流;1950年代,伴淳三郎、森繁久弥等闹剧演员开始摆脱以稀奇古怪的技艺使人发笑的路子,在《三等董事》《粪尿谭》等片中通过生动活泼的表演展现劳工阶层的生存窘境,描绘“平庸之人竭尽全力逞强”的生存方式,开辟了写实主义喜剧的支流;{15}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松竹公司推出长达48集的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这部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平民喜剧,将松竹蒲田制片厂时代的轻喜剧传统发扬光大,同时塑造出“寅次郎”这一国民级的喜剧形象。《寅次郎的故事》风靡银幕二十多载,这亦是人情喜剧的全盛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许冠文的电影不仅以打闹、写实与抒情的多样化面貌满足观众的需求,更和日本本土的喜剧经验与传统形成指涉关系。我们不妨对比同时期进入日本市场的外语片,如《回到未来》系列、《鸡尾酒》等,可以发现,喜剧更多的是作为科幻、爱情片等既定类型中的一种成分,而非明确的消费。这些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好莱坞的科幻、爱情故事本身固有的吸引力,而不是散落其中的逗笑因素。相较之下,许氏喜剧与日本本土喜剧之间的指涉性,超越了美学上的相似与重复,所实现的是对日本民众的喜剧消费趣味、文化心理的准确把握,进而令许氏喜剧更易获得日本市场的接受与认同。
三、主题含蕴:喜剧的现代性转向
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地区,日本、香港的电影自然地内含着对现代性的思索,即:当本国/地区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迈入现代,现代性并生增长时,电影如何以其文化功能,去处理本民族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冠文电影正是在香港粤语喜剧的脉络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许氏喜剧部分继承了1950、1960年代粤语喜剧传统的一面,又在不断增长的本土性与主体意识中,自如地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从劳工阶层生存境遇出发,讲述打工仔“搵食(谋生)艰难”的讽刺喜剧是1950至1960年代香港粤语喜剧的一大主流。有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喜剧称为“低下层职业大全”{16},各类小贩、侍应、外卖员、魔术师、售票女郎为讨生活施尽手段,在苦涩的窘境中惹人发笑,如《马票女郎》《警察捉小偷》《抢食世界》等。这些影片的职业背景、贫困主题、道德色彩与情节笑料(老板对打工仔的欺压以及二者的斗法)反复出现于日后的许氏喜剧中,其世俗趣味背后的写实精神与尘世关怀亦值得肯定,如《抢食世界》直指失业、行业倾轧的现实,《楼下闩水喉》《一楼十四伙》等片则反映1950年代战后移民涌入,香港的居住空间受挤压的问题,同时抨击富者不仁,歌颂小人物们守望相助的精神。然而,1950、1960年代粤语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传统价值观念与保守的意识形态,电影结局中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往往是在重申“邪不胜正”的二元道德论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将矛头对准一个泛泛的现代资本社会。究其原因,可解释为战后二十多年里,中国与港英政府在意识竞逐方面的低调退缩,令香港未有任何社会阶层和集团,能够对港人定下集体目标和生活志向,{17}加之当时处境下主体性的某种残缺,令彼时的香港喜剧片又或香港社会,更多的是在重复一种无关乎本土意识的,作为“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雷蒙·威廉斯语)的模糊的“传统”。进入1970年代,作为社会主体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目睹了香港经济的腾飞,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一个发达的现代金融都市呼之欲出,辛苦耕耘、“向上流动”成为港人所认同和骄傲的价值。政府的公屋制度也令新一代不再敏感地受困于父辈那种“漂泊”“北望”意识,而产生“家在香港”的身份归属感。电视“入屋”亦孕育了香港的普及文化,制造一种本土的集体经验,这一切都使得“香港性”不再抽象。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许氏喜剧,一方面是对1950年代粤语市民喜剧的复兴;另一方面又摒弃其作为“剩余文化”的一面,构建以香港新主体为中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同时展现出一种基于自身经验的现代性。
一个明显的体现是,与1950、1960年代粤语喜剧“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不同,许氏喜剧在商业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弱化了金钱、资本的道德指涉,对个人利益持开放态度。尽管此前的粤语喜剧也涉及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如聚焦小人物一朝发达的“马票狂”模式电影(《马票狂》《无端端发达》《马票女郎》等),但出于道德说教目的,这些影片往往在故事结局安排暴富者复贫,受尽嘲弄,从而固守脚踏实地、诚实守信、安于本分的传统价值观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鬼马双星》中骗术高超的“老千”许冠文非但未被丑化,反而被赋予“师父”光环,引来许冠杰的崇拜和拜师,在一场戏中,二人对赛狗博彩进行精彩的概率学分析,逐利、投机主义被巧妙地置换为个人的机智与对机会的把握;《抢钱夫妻》里,“赚快钱”在主人公“身患癌症”的设定下获得合乎情理性,跳出了二元的道德判断;《鸡同鸭讲》对于金钱、资本的态度,呈现出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故步自封的老许最终接受了丈母娘的投资,对传统烧鸭店进行现代化、股份制改革,又重包装与营销,在求新求变中令餐饮生意恢复红火。同时,许氏喜剧代表着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本土化,其“打工仔电影”意不在抨击牢不可破的阶级对立与劳资矛盾,而是凸显其中的灵活性。在吴俊雄看来,许冠文的电影“就像处于一种旧秩序已经不存在,新秩序究竟怎样做才好的情况”{18},《半斤八两》《卖身契》等片即是对这种新秩序的探索,电影既突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雇主与雇员的契约关系,又强调契约精神以外的“小聪明”,在中西磨合中弹性地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本土化调试。如《卖身契》全片围绕打工仔耍尽小伎俩“偷契约”展开,《半斤八两》里的雇员则获得了议价的权利(向雇主争取“五五分账”),最终达成互惠互赢的合作模式。此外,许氏喜剧对社会的洞察与批判,较之此前的粤语喜剧亦有进步。1950至1960年代的小市民喜剧,在意识形态上往往是驳杂不纯、态度妥协的,充满迎合低下阶层梦幻价值观念的逃避主义色彩。可以说,这些影片在技巧甚至桥段上不断向卓别林偷师,在批判精神上却和卓别林喜剧相反。{19}许冠文的电影同样着眼于小市民身上的喜剧性,但已摆脱滑稽剧窠臼,表现一种与社会背景、时代情绪相勾连的复杂性与批判性,如《鬼马双星》《抢钱夫妻》反映市民社会金钱至上、赚快钱的心态,《半斤八两》挖苦人性贪婪、精于算计,《天才与白痴》则以精神病院镜射社会的反常。
相较而言,日本电影呈现出一种物质与精神上“遁入传统”倾向。陈林侠敏锐地指出,日本电影凸显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压力,转而迂回地借助传统的伦理、价值观、思维方式,完成现代性危机的“神话”式解决。{20}山田洋次的《寅次郎的故事》细腻地还原了东京葛饰柴又小镇上质朴、纯粹的生活状态,通过复现已然消逝的地方记忆,将现代的空间变回充满邻里情感的“地方”,点滴间流露出淡淡的怀旧之情,对记忆中的理想化的“过去”感慨不已。传统与现代的抵牾在伊丹十三的喜剧则中通过固化的性别模式体现,在《女税务官》《民暴之女》《超市之女》等“女人系列”影片里,男性无一不作为现代性的负面因素(贪婪、争权、逐利等)存在,而女性总是以传统精神与道德良知化解其中的危机,令社会趋于稳定。近年的日本电影中甚至出现了一类独具特色的“森林系”电影,《阿弥陀堂讯息》《幸福的面包》《小森林》系列、《宁静咖啡馆之歌》《哪啊哪啊神去村》等影片强调自然对都市人的“治愈”功能,现代人在“亲自然”的日常生活中体味平凡可贵,在达成“心物同一”之后获得禅悟,以抵御现代性带来的浮躁与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许冠文电影之于日本观众的独特性,在于提供了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两分法”之外的,思考现代性的方式。例如,同为“经营”题材的影片,伊丹十三的《蒲公英》《超市之女》与许冠文的《鸡同鸭讲》有着本质不同。《鸡同鸭讲》里,传统烧鸭店在与西式炸鸡店的竞争中获胜,在于引入并改良了后者的现代化经营模式。《蒲公英》《超市之女》的重点则在突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日本“匠人精神”在商业社会中的可贵。如《蒲公英》的女主人公为煮好一碗拉面,接受了练武般的严格训练,在锻炼捞面的臂力、煮面的速度等一系列场景中,神话式地展现出对烹饪传统食物近乎执迷的狂热,这实则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坚守专业精神的重要性。类似地,《超市之女》中的旧式超级市场“正直屋”正是凭借日式的“款待”(Omotenashi)、诚信等传统服务精神,最终打败大型资本垄断超市。总的来说,许氏喜剧有其传统的一面,同时能够在逐渐稳固的本土意识中,于银幕上自信地再现出一套基于香港自身经验的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当中亦不乏冷观的批判态度。正如许氏电影的正面结局,往往不是通过排斥现代性来反衬传统的当下意义,而是探讨现代性的正向价值与积极出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许冠文喜剧一方面在对粤语喜剧的复兴中,令香港喜剧的形式与风格臻于完善,对后来的功夫喜剧、无厘头喜剧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其在日本市场的成功,又使之成为一个极佳的跨文化传播样本,具体表现为:从跨文化策略的角度看,许氏喜剧本质上是展示动作奇观的“吸引力电影”,从而以视觉策略消解了港产喜剧这一向内的“谜化”文本所暗含的文化折扣;在形式层面,许氏喜剧与日本本土电影形成美学关联及深层指涉,相较同时期的外语片,更能贴近日本受众的审美趣味;在主题内涵上,许冠文的小市民喜剧完成了粤语喜剧的现代性转向,展现出与“遁入传统”的日本电影所不同的、更为自信的处理传统与现代之矛盾的方法和态度。在香港本土电影持续没落,并且过于依赖动作电影的今天,回望许冠文喜剧,亦是在重提香港电影可贵的喜剧传统。曾经可谓贬义的“过火”与“癫狂”,如今看来,是于香港电影必要的差异性与多元性。从许冠文的电影中重拾、焕新喜剧传统与经验,或是香港电影重新出发,提升自身文化竞争力的一条思路。
注释:
{1} [美]大卫·波德威尔著,何慧玲译:《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2}张燕:《跨界之魅: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电影的全球拓展》,《电影艺术》2004年第2期。
{3}票房数据来源自[日]电影旬报社:《电影旬报十佳85回全史(1924—2011)》,电影旬报社2012年版。
{4}票房数据来源自Hollywood(UPI).Chow, Past Reporter, Now Very Rich Filmmaker. The Daily Herald. Provo. 22 October 1979. Retrieved 9 March 2021.
{5}唐佳琳:《构建中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香港喜剧电影研究》,王海洲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6}[美]汤姆·冈宁著,范倍译:《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
{7}数据整理统计自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 (MPPAJ)。
{8}[日]佐保畅子:《在日本的Mr. Boo》,《am 730》2011年12月5日。
{9}{15}[日]佐藤忠男著,应雄译:《日本电影史(1941—195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9页、第408—411页。
{10}刘天赐:《提防电视》,转引自钟宝贤:《香港影视业百年》(增订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49页。
{11}许佩琳整理:《许冠文:我梦想以电影分享对世界的看法》,吴君玉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七:风起云涌——七十年代香港电影》,香港电影资料馆2018年版,第128页。
{12}日本学者源了圆指出,日本独特的“风土”(即作为环境的具体的自然)造就了日本人的“即物”性格:被分成小块的自然景观,阻碍了超越自然物的“自然观”的形成。日本人难以去设想某种抽象、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的存在,而是与一个个的自然物结成了个别主义式的关系。叶坦进一步将日本人重感觉、经验,轻抽象与思维的“即物”性格,总结为一种文化模式上的实用主义,即日本人基于实际需求选择、吸收与创新外来文化,使之成为本体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过程,“即物”由此成为一种强调实用性与变通性的民族文化心理。见[日]源了圆著,郭连友、漆红译:《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6页。叶坦:《日本文化深层结构研究》,《日本学刊》1992年第3期。
{13}康宁:《香港喜剧电影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第66页。
{14}朱耀伟:《岁月如歌:词话香港粤语流行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26页。
{16}吴昊:《二十年香港粤语喜剧电影的初步内容分析》,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7}吴俊雄:《寻找香港本土意识》,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8}陈秀英、吴君玉整理:《黄金年代的前夕:谈七十年代香港电影与社会》,吴君玉编:《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七:风起云涌——七十年代香港电影》,香港电影资料馆2018年版,第28—29页。
{19}澄雨:《小人物看世界——粤语喜剧片的意识形态》,吴俊雄、张志伟编:《阅读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67页。
{20}陈林侠:《日本电影的苦难叙事、现代性转型及意识形态功能——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核心(1980—2016)》,《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2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