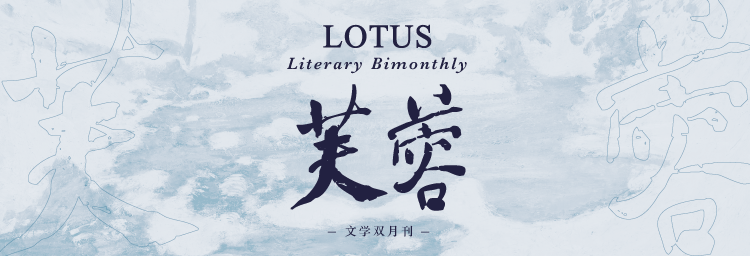

《扶贫志》。
为精准扶贫抒写信史
——读报告文学《扶贫志》
文/蒋祖烜
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志业,也是文学书写古老的母题之一。为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献礼,湖南省精心策划出版了《扶贫志》一书,意图通过讲好湖南扶贫故事,展现广大扶贫干部和脱贫群众为梦圆不懈奋斗的精神面貌。《扶贫志》是大时代、大事件、大行动呼唤下诞生的一部有可信、可感、可亲的报告文学力作。作者卢一萍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真诚的写作态度记录了这段民族共同记忆,用一个农民之子的深情致敬理想、致敬奋斗、致敬英雄。
中国有十四亿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夺目的文明,却始终难以彻底摆脱贫困的阴影。为了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开创了扶贫事业的新局面。如果把过去八年的中国乡村做一个影像回放,那一定是一部山乡巨变的历史大片。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有这样的决心和激情,用仅仅八年的时间完成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的脱贫任务。这是中国全部的贫困人口。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时刻,必然彪炳千古。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首倡地,在过去的八年中,始终积极担负起首倡之责。它的脱贫历程是一个范本,足以供人体认中国扶贫事业的波澜壮阔。
十八洞村是一个村民不足千人、人均耕地仅有0.83亩的纯苗族村寨。它曾是个“美得让人心痛的地方”,从前来到这里的人,心灵总会被美丽和贫穷同时震撼。2013年,十八洞村225户中有136户是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这样的地方要脱贫,还不能“搞特殊化”,扶贫工作队不仅要为十八洞村探明走出贫苦的道路,还得让经验“可复制、可推广”,这个任务是艰苦卓绝的。
事实上,对湘西地区的扶贫时间远早于2013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始终未能彻底撬走贫困这座大山。由于地理等原因,湘西地区发展极为缓慢。直到20世纪,湘西还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土家、苗、瑶、侗等民族和少数汉族零星聚居在大山中,不绝如缕地向外散发神秘的气息。像十八洞村这样的苗寨,贫困是根深蒂固的。新一轮扶贫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精准”,即精确地对准贫困人口,把工作落实到具体的人,深入分析每一个贫困村、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因人而异制订帮扶方案,因地制宜发展集体产业,最终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蓝图绘就后,要真正彻底拔除贫根,需要志存高远、埋头苦干。比如,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的龙秀林,他是花垣县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不仅对扶贫政策、扶贫思想有深刻的领会,也擅长做群众工作。但当他带领扶贫工作队入驻十八洞村时,情况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悠久的贫困历史已经彻底磨去了人们的斗志,他们已经习惯了“等、靠、要”,扶贫干部一来,村民就一起上门要钱。龙秀林的扶贫工作必须从扶志开始,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摆脱贫困是扶贫干部的志愿,也应该成为贫困群众自内心生发的斗志。
自2013年以来,以十八洞村为标杆的中国脱贫成绩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而在这场全民族的伟大行动中,十八洞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历史的标志,它既是民族事业胜利的一座丰碑,也成了一个有讲不尽的故事的文学符号,是一首必将在民族集体记忆中回响的大型史诗。
中国全面脱贫再次有力证明,世界文明之路并非独木桥,中国道路为人类命运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文学价值、文学创新、文学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学者的文学理论、作家的文学创作、批评家的文学批评都偏好于批判,多以质疑的姿态面对社会发展。中国脱贫攻坚的胜利、十八洞村的胜利是一座巍巍大山,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出现在写作者的个人生命和艺术生命里,并开始得到文学的回应。同时,庞大、丰富的时代内容也触发了文学形式的创新,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成为伟大历史的传唱者,而《扶贫志》就是响应时代呼唤而生的,兼具史志价值和文学品格的报告文学力作。
《扶贫志》的作者卢一萍是一位川籍作家,也是一位军旅作家。他与湖南的文学缘分要上溯到26年前,《芙蓉》杂志为他的小说《黑白》专门开辟了一个叫《长篇未定稿》栏目。2006年,卢一萍又为20世纪50年代参军进疆的湖南女兵写下一部非常深情、厚重的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他在湖南、北京、四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寻访了上百位女兵,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三易其稿,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首次全方位地还原了湘女进疆的史实,是八千湘女真实命运的缩影。作品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卢一萍的报告文学是沉静、开阔、厚重的。这与他的小说理想完全不同:他的小说个性、先锋、自由,任凭自我在广阔的天地间横冲直撞;他的报告文学却收敛得多,常常不事雕琢,只做最朴素、最虔诚的记录,似乎生怕文字技巧影响了天然的故事。这一风格,也延续到了《扶贫志》之中。
卢一萍又是一位出身农民家庭的作家,对农村、农民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他会做每一种农活,熟悉每一块田地的厚薄,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每一份心情都能感同身受。离开土地多年以后,他对农村有了更冷静的观察和思考,也萌发了深入农村、书写农村的心愿。
读完《扶贫志》后,我感到,卢一萍是新时代中一位具有太史公精神的作家。
湖南文艺出版社发出写作邀请时,卢一萍一度非常犹豫,主要的原因是时间紧、任务重。四川和湘西同为西南官话区,虽然语言不构成特别大的障碍,湘西对他而言毕竟是异乡,要深入一片土地、理解一方人民并非易事。最终,军人的血性还是鼓动卢一萍迎接了挑战。这使得他在接下来的近十个月,几乎每天都只敢睡五个小时,身心完全沉浸其中,乃至忘记了疲惫。
2020年3月上旬,春寒料峭,新冠肺炎疫情也才刚刚得到控制。怀着一颗为父老乡亲立志的决心,卢一萍踏上了艰苦的采访之旅。他以大湘西地区为范围,40多天日夜兼程,走遍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德、张家界、怀化,行程达1.53万公里。为了捕捉细节,卢一萍深入30多个村寨,采访了90多位亲历者,收集了长达5700分钟的采访录音和20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
《扶贫志》是在大量口述史的基础上诞生的。卢一萍把湘西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忠实地记录下来,清晰地再现了每一座村寨、每一张面孔、每一个笑容。《扶贫志》分为十八章,以饱满的形象、曲折的故事、丰富的细节讲述了十八种人生、十八种经验、十八种情怀。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追寻着光明,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卢一萍为每一个业已离开土地的人,描绘了一个可信、可亲、可感的回得去的故乡。
我认为,报告文学写作一定要舍得下苦功夫、下笨功夫,要走向田野,寻找仍带有泥土腥气的故事。时代是文学永恒的源泉,文学是时代不朽的见证者。习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作家只有响应时代的号召,作品才能有质感、有深度、有分量。
文学又不同于新闻报道,艺术的力量一定是藏匿在细节中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大时代、大事件中,应该继承古老的太史公精神,立言以不朽。这需要舍我其谁的担当、无穷无尽的耐心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实话实说,当下有能力写出《扶贫志》这样作品的作家不少,但愿意如此付出的作家不多。卢一萍在乡亲的屋檐下、在院坝里,甚至在田埂上进行采访,他得到的故事一定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扶贫志》也必将成为历史的存照。
《扶贫志》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显现出了史志文学的独特气质。它用“志”的方式和态度写就,是可考证、可对质的。
所谓志,指的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物等情况的文章。志是史学的,记载了文明的进程和梦想;志也是文学的,出色的史志作品,一定是有细节、有生活、有味道的。比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作品,都是既真实,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使命与史志一脉相承。《扶贫志》的史学价值寓于文学性之中,其艺术性又超越了手艺技巧的范畴,向历史性、思想性迈进。它在报道和虚构之间、史学与文学之间寻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
《扶贫志》是一部具有史学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是社会人类学前沿个案的调查成果。这里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文献资料具有较好的概括性,指向明确、集中,涉及的主题也比较广泛、深刻。它是田野调查的指明灯,在对一地、一事、一人开展个案调查前必须有丰富的资料积累,田野调查才不会漫无目的,甚至南辕北辙。此外,文献材料也是理解和解释一手材料的重要抓手。《扶贫志》参考的文献材料来源广泛,有政策文件、历史著作、学术研究、湘西名人传记等。这些材料不是为《扶贫志》量身定制的,但为《扶贫志》的人物活动搭起了舞台,能够带领作者和读者深入大湘西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肌理。卢一萍也通过文献材料,尝试勾勒过去四十年中国乡村的变迁史,带领读者通过历史的逻辑理解当下、展望未来。
而口述史是《扶贫志》最大的亮点。它既是《扶贫志》材料的重要来源,又作为一个独立模块被直接呈现在文本之中。口述史是个体的、感性的、差异化的,将口述材料编入正文,是让人民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确保了《扶贫志》中的故事真实,且有血有肉。文本的创新为读者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再现了历史现场、事件细节和个人立场,极大地丰富了读者对扶贫行动的想象。
《扶贫志》是现实的、在场的,也是介入的。报告文学必须具有历史性和思想性。文学书写必须与概念书写果断诀别,绝不能沦为概念的表达。报告文学更强调走出书斋,必须掌握翔实的材料和如茧丝、如牛毛的情感,而不能单凭技巧和想象。这是作家的责任。《扶贫志》存在多重视角,有社会、历史、当事人、记叙者……视角频繁切换、交叉赋予了这部作品全面性和深刻性,让读者在个体的经验中,洞见宏大的历史。卢一萍深入现场,贴近大地,凭借着对人物、故事和环境的深入观摩和描写,全景式地描绘湘西大地图景,不断地审视、追问精准扶贫行动在当代中国、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上的价值。这让《扶贫志》的意义溢出文学影响力的边界,比同类题材作品更富有真切感。
《扶贫志》是高度审美化的。从本质上说,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而存在。报告文学与经典文学,在艺术上是共享审美标准的。文学是人学,必须以描写人为中心,它的对象和目的都在人。《扶贫志》成功地塑造了大湘西脱贫攻坚战的人物群像,这是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书中的人物不是概念表达的工具,也不是反映现实的载体,而是一群鲜活生动、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和个性的人。作者按照人物身份进行分类记叙,把每一种身份的人都收纳进来,性格迥异,形象鲜明。此外,《扶贫志》在大叙事中力求细部的丰盈。人物心灵深处的悲欢、幽微的心理变化、曲折的思想历程是文学表达的重点,也是文学有别于报道的关键所在。《扶贫志》的成功在于细节的成功,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存在大量的行为细节、语言细节、心理细节,比如龙秀林的绰号、田金珍的肥猪、龙先兰的酒、谭艳玲的百褶裙……作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抓住了这些细节,在故事中凸显出来。这些细节中,蕴藏着丰沛的感情。每个人都可以在《扶贫志》中找到熟悉的影子,或自己,或亲友,或熟人……
综上,我认为精准扶贫是一件历史必志之事,卢一萍是一位潜心写志之人,《扶贫志》是一部蕴含史志品格的报告文学力作。这部作品面向时代、面向历史、面向世界,是中国文学在2020年的一大收获。《扶贫志》《大地颂歌》《从十八洞出发》《江山如此多娇》《乡村国是》《梦圆2020》等优秀文学影视作品的涌现,也证明了湖南不仅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也能讲好湖南扶贫故事。这也将成为湖南故事的新起点,我们一定把伟大祖国、伟大政党、伟大人民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为乡村振兴、民族复兴凝聚起磅礴之力。

蒋祖烜,祖籍湖南澧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发表散文和诗歌作品多部。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