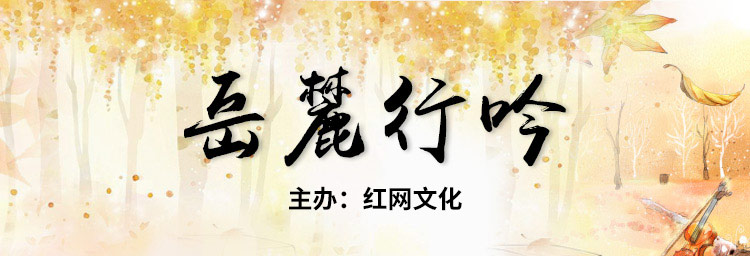

李锐/摄
重回母校炮院
文/郑杰
很多人,因为陷于事务,总是无暇回自己熟悉地方看看,位于湘水之滨的长沙炮兵学院,是我人生重要驿站,我在这里淬火负笈几年,数百个日日夜夜,这里有我难以萦怀的军旅情思。1997年,从这所军校毕业,此后,到南国军营,再到洞庭湖畔距长沙不远的另一座湖湘城市,时光弹指一挥间,母校一别23年。最近十几年,我因工作经常穿梭于居住地与省会之间,但一次次都与母校擦身而过,就在我与这片故地渐渐疏离时,一次偶然又不偶然的机会,让我与母校突然重逢。
那天是个周末,初夏阳光温煦灼热,此时长沙已走出疫情困扰,正撸起袖子热火朝天地复苏她作为“山水洲城、快乐之都”那份本真的洒脱曼妙与火热喧嚣。岳麓山上,梅溪湖畔那些经历过寒冬风雪的植物果疏,在潮湿空气的抚摸里,有的正在蓬勃生长,有的正在孕育果实,树树浓荫掩映的大街,随处可见行人攘攘熙熙身影。
中午,在湖大附近一个小酒楼,我得已和多年未见的几个湘籍军校同学贵铭、铁兵、晓春相聚。这是去年底就定好的约定,只是囿于疫情阻挠,这场聚会姗姗来迟,但我们还是把酒言欢,共叙桑麻,边吃边聊中,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到毕业后各自的经历情感人生。当然,席间话题重点还是围绕我们的军旅和母校炮院。
年月如草,时节如流,很多挥之不去的旧时影像,蓦地,在我们脑海中起起落落。炮院所在地长沙天心区黑石铺,当时,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条不太宽绰且坎坷不平的沥青路连接炮院与城区中心,沿途丘岗、菜地、荷塘、水渠犬牙交错,两边簇拥着密集的院落和民居,这些民居褊狭、黯淡、破旧,黑色的、赭色的屋脊,高低不一,覆盖倾轧,波浪翻滚,显得零乱不堪,落魄颓废,同时,也缄默无声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坦露它的沉寂与荒芜,都市繁华曼妙和灯红酒绿无法辐射到此,与其说是城区,倒不如称它乡村更为贴切。
依水而生,学院校区伴湘江故道而建,横贯南北的京广铁路就在校区西院的围墙脚下穿过,带着那个年代特别标志的绿皮火车和闷罐货车,每天都会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湘水和京广线分别以流淌和延伸的方式,向着浩瀚洞庭,向着大海,向着远方而去,并把我们建功军旅的梦想也带向远方,带向祖国大江南北的一座座军营,带往无数个冷月孤悬白雪皑皑的边关哨卡。
席间,我提议,“饭毕,由没有饮酒的晓春同学驾车,我们一起回母校看看,到曾经摸爬滚打的地方看看。孰料,话音刚落,便掌声应声即起,这提议,似乎一下成了大伙不谋而合蓄谋已久的决定。从河西到河东,越野车跨过银盆岭大桥,再上芙蓉路,晓春同学启开高德地图手机导航向母校方向快速行驶。一路上,我们几个都在寻觅这座城市过去的记忆,但长沙,早就不是二十几年前的长沙。橘子洲还是橘子洲,东塘仍是东塘,蔡锷路还是蔡锷路,坡子街还叫坡子街,只是相比昨天,今天的它们更加流金淌银风情万种。
抵近黑石铺,我们都很激动,那种近乡情怯忐忑不安的滋味,一如和某位老友阔别相逢。黑石铺,我已不敢和它相认,眼前的地貌地物与原来格格不入,曾经的野岭荒郊早已荡然无存,无处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林立高楼和繁花绿树,广厦万间,如果没有高德导航,母校,我们只怕是很难找到您的。
大概是下午1点半左右到达学院的,徘徊于校园之间,我们仔细打量这个无比熟悉的地方,竟都热泪潸然,也不禁回望起那段军旅。学院共三个院区,中院,西院还在,东院没去,不知道还存不存在?学院校门门牌己换成国防科技大学炮兵学院的字样,这是上世纪1999年的事,彼时,在部队院校一轮合并中,这所最初创建于1978年的炮兵院校,与长沙政治学院、工程兵学院一起并入国防科大本部。
中院是学院办公区及生活区,它还是记忆里的老样子,门口依然有卫兵把守,里面的小荷塘还在,火箭雕塑还在,一排苍劲挺拔的粗大香樟树还在,沥青路面仍如当初整洁开阔、纤尘不染。而西院所在教学区,由于多年不再招生,往昔军歌嘹亮,铁马奔流的喧嚣盛景已无法重现。曾经人声鼎沸的学员宿舍,图书馆,训练场冷冷清清,销声匿迹,礼堂和教学楼悉数淹没在深而茂密的杂树枯草之中,显得幽深寂寥,绿浪汹涌。正是午后时光,我伫立在通往教学楼的那条林荫路上,在阳光透过枝叶洒下的一地碎银里,有两只鸟儿正闪动翅膀一跃而起,继而扑腾、扑腾地飞上路边那排葱郁的梧桐树上,顿了片刻,又向湛蓝圣洁的天空而去。在这片辽阔明媚干净幽远的空旷里,我凝视了许久,沉思了许久,恍惚看到有几个穿着军装戴着眼镜的军校教员正夹着教案朝那抹幽深之处走出,即刻,却转瞬不见。
很多有形的东西都消弭成无形,但我仍在试图找回曾经的记忆。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正因为失出,所以才需要用文字去记叙。眼前这片被闲置了的西院,就像一座被周围繁华世界遗弃了的荒岛,孤独寂寞依偎在湘江边,这让我的眼睛又开始湿润。从西院到中院有一条地下通道,当初修建,是囿于人防工程考虑,孰想,平时却成了教员、学员们通往中院生活区的便捷通道。我在老部队工作时,听军嫂刘姐说过,她和爱人与这条通道之间的浪漫故事。刘姐爱人欧阳枫是我们营长,俩人是高中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欧阳枫和刘姐都考上了省城大学,欧阳枫在炮院,刘姐在农学院,本来在高中校园就已经萌芽的爱情种子,移植到省会长沙后,便进一步茁壮成长恣意汪洋。刘姐还说,每隔一个月,她都会坐公交从农院来炮院与营长(那时还叫恋人)相会,但她又不敢去学员宿舍,因为只要去宿舍,恋人那些室友同窗就让他们两个下不来台。他们只好转移到地下通道,诉说相思之苦。她说,她给欧营长织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在这个地道送给他的,这件毛衣,欧营长穿了好多年,一直舍不得扔掉。关于,这条地道与我们学员之间的故事,我只挂一漏万提到这一件,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被丢在岁月的风尘里。
穿越一片小树林,我们又踏过一条落叶满地的小径,七弯八拐后,总算找到原来中队的宿舍。站在灰色的两层水泥楼下,昨日的一切清晰可见,只是破烂的门窗,斑驳的墙壁,厚厚的青苔,疯长的野枝茅草,还有那满墙的爬山虎让我恍若隔世……
在母校,我们足足逗留了两个小时。之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去路上,我还摇下越野车挡风玻璃,望了望那个卫兵站立的岗位,那个地方曾经属于过我,多少个艳阳天,多少个风霜雨雪的夜,我都记不得了。
有一位曾经的老首长,跟我说了这样一席话:“军改后,他去了一趟老部队,但因为撤编,原来热闹的营院已成一座空营,他置身凄凄荒草之中,就像茫茫海面上一只无处落脚的鸟儿,心中弥漫着根须被生生斩断的无望,不知归向何处。他很后悔没早点回去看看。”
是的,世事无常,逝者如斯,事情总是充满变数,无论是故乡,还是母校,还是某个与你生命发生过重大交集的地方,那都是我们的精神故地、心灵圣土。
回去要趁早,哪怕回去只拍几张照片,只与故人简单握下手,在青草摇动的小径采摘一束花,这样做过,往以后的日子,才不会惆怅,才会少一些遗憾,多一份心安。

郑杰,曾服役广州军区某部,现居湖南常德市,供职公安工作,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公安文联会员。文学作品散见《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战士报》《散文百家》《湖南日报》《广西日报》等军地刊物,特稿纪实作品在《知音》《家庭》《华西都市报》刊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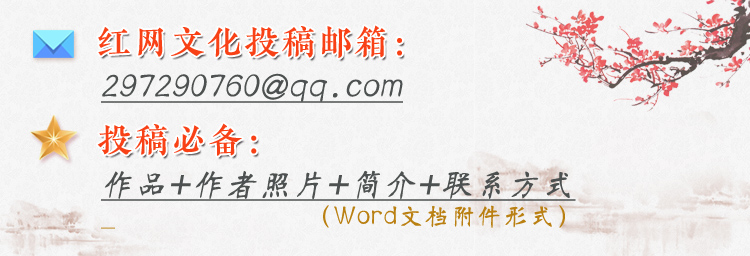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