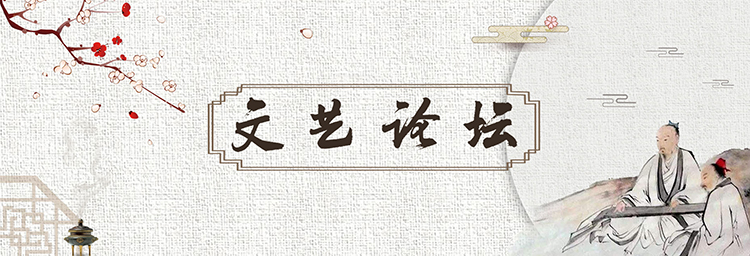

《江湖儿女》: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作者电影的类型化与市场化
文/李卉
摘 要:作为贾樟柯电影的集大成之作,《江湖儿女》在互文叙事的意义上,成为作者电影的典型文本。与此同时,高额的制作成本与工业化的宣发流程,则凸显了其走向市场的意图,反映在创作上,则是对黑帮类型与现实风格的杂糅并置,并由此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批评,争议的焦点围绕在作者电影能否以及如何类型化与市场化,而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则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关键词:贾樟柯;《江湖儿女》;电影工业美学;作者电影;互文;类型
作为贾樟柯电影的集大成之作,《江湖儿女》开启了本年度对“贾樟柯电影宇宙”的集中探讨。身为典型的作者导演,贾樟柯一直有意建立其电影文本之间、电影文本与时代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对话性,《江湖儿女》通过引用和重写散布于“贾樟柯电影宇宙”的互文本符号,延续了贾樟柯电影一贯的主题和风格,同时在叙事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类型化”尝试,在与香港黑帮片形成“互文”的同时,进行了颇具作者风格的改写和重新演绎。与此同时,作为贾樟柯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江湖儿女》在制作与营销层面进行了诸多符合当下电影工业体制的调整和转型,凸显着贾樟柯在艺术性/商业性、作者性/体制性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其所取得的成绩与引发的争议,映射着“体制内的作者”在当下中国电影工业中的求索之路。
一、互文叙事与贾樟柯的电影宇宙
作为一个典型的作者导演,贾樟柯在多年的电影创作中,一直有意建立个人电影之间的细微联系,他曾坦言,“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他剪成同一部电影”{1}。《江湖儿女》的出现,成为开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一把钥匙,不论是内容上的主题呈现、人物塑造、空间设置,亦或是形式上的影像风格、叙事结构等,都与他以往的电影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在凸显作者风格的同时,亦招致了“自我重复”“故步自封”的批评。对此,贾樟柯多次在采访中否认《江湖儿女》的“自我致敬”,而认为其是对《任逍遥》《三峡好人》等电影叙事留白部分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儿女》呈现出典型的作者性与互文性叙事特征,其文本意义应置于“贾樟柯电影宇宙”交织的文本网络中进行解读。
“互文性”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指的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这一广义上的互文性理论将社会历史文本和意识形态因素引入了封闭的结构主义分析,进而攻击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20世纪70年代,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将广义的互文性理论重新引入结构主义视域,将其狭义化为“跨文本关系”之一种,即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存在的引用、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性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可操作的、建设性的互文性理论。狭义的互文性理论并不认为作者已死,反而重新激活了作者研究,并成为此后互文性理论应用于文本批评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
《江湖儿女》作为贾樟柯电影的集大成之作,延续了其对转型期中国民间社会与底层群体的关注,并将其提炼为“江湖”与“儿女”两个颇具古意的语汇,以此回眸并总括20年来的电影创作,在交织的文本网络中抽丝剥茧,构成了一次反向命名。有意味的是,这一“命名”的灵感本身亦源于电影史的丰厚遗产,贾樟柯在2009年拍摄纪录片《海上传奇》时,曾采访《小城之春》的主演韦伟女士,于交谈中得知费穆导演有一部未完成的遗作,名为《江湖儿女》{3},这一片名当即“击中”了他,并唤醒了其成长岁月中由香港武侠片与黑帮片浸润而生的“江湖情结”,由此构成了《江湖儿女》电影创作的前文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贾樟柯对“江湖”的另类塑造,并激发了观者与受众层面的互文性联想与感知。
在文本内部,《江湖儿女》的互文性叙事体现在对散布于“贾樟柯电影宇宙”的互文本符号的引用与重写,影片主角巧巧与斌哥直接借用了《任逍遥》中的角色名字,并杂糅了《三峡好人》中的人物身份与命运轨迹。除此之外,大同、三峡、矿区、歌舞厅等空间选取,山西方言、港台流行音乐等听觉元素,关公、UFO等意象符号,三段式的板块状叙事结构,长镜头、不同画幅与影像介质的拼贴等影像风格,再一次被贾樟柯从其电影宇宙中提取,整合进《江湖儿女》的叙事系统之中。基于个人经验与时代的共振,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以互文性叙事建构起了自成一体的“电影宇宙”,并将其指向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从而在相互印证的互文本痕迹中凸显了一以贯之的作者风格与记录时代的文献性影像意识。
相比于《任逍遥》《三峡好人》对世纪之交的大同和移民潮中的三峡等真实时空的记录和表达,《江湖儿女》对其互文本的引用则多为间接形式,在怀旧视域中力图还原时代细节,如片中巧巧家所在的矿区职工宿舍,与《任逍遥》中巧巧的家同为一个取景地,“除了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变了,所有的东西都没变”{4}。这种“不变”给贾樟柯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曾说,“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5}而在《江湖儿女》中,贾樟柯将对“变动”的关注转移到对“不变”的追寻,在拆迁的废墟与重建的楼宇之间,寻找被遗留在原地的“不变”的孤独之物,在电影中,它们指的是废弃矿区的职工宿舍,是宛若江湖旧梦的麻将馆,也是巧巧所坚守的江湖情义。这是一种在加速的现代社会之中的古典主义伤怀,一种在急剧变动中的回眸、静观和审视,反映在叙事文本上,则是对已有影像文本的直接引用,如片头的公交车段落来自于贾樟柯在2001年用第一台DV拍摄的日常生活素材,三峡段落中的库区景观、流浪歌舞团表演等来自于贾樟柯在2006年拍摄《三峡好人》和纪录片《东》时所录制的素材。影像文本的直接引用加强了叙事的真实感,营造了一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直接引用的互文本在插入文本机体内部的同时,也会使文本机体自身产生变异,生成新的叙事面貌,如片头的公交车段落拼贴了2001年真实拍摄的DV素材与赵涛的表演场景,这一日常的生活空间与巧巧的江湖人身份产生了碰撞,凸显出贾樟柯对“江湖”的独特理解,即江湖寄生于日常,大哥亦不过凡人,从而区别于港式黑帮片所渲染的浪漫化、传奇化的江湖故事,为整部影片于纪实和虚构交织中展开叙事定下了基调。
二、“类型”叙事与贾樟柯的江湖想象
从《天注定》开始,贾樟柯的电影逐渐呈现出某种类型片的特质,尝试“用写实的方法拍出类型电影的非写实感”{6}。《江湖儿女》延续了这一创作趋势,在叙事上借鉴了香港黑帮片的类型架构。香港黑帮片在八九十年代对大陆民间社会的影响,构成了贾樟柯的成长环境,多年以后,他又将这种成长记忆借由黑帮片的类型程式呈现在《江湖儿女》之中,形成了一种杂糅了个体记忆、类型元素与社会现实的非典型性“类型”叙事,并在其中寄寓着贾樟柯对“江湖”的独特想象。
《江湖儿女》采用了三段式的叙事结构,讲述了2001年以斌哥为核心的大同黑帮故事,2006年以巧巧为核心的三峡闯荡故事,以及2018年巧巧与斌哥重聚大同的重逢故事。其中,对黑帮片类型元素的借鉴主要显现于第一个叙事段落。首先,《江湖儿女》采用了黑帮片典型的人物谱系设计,即由大哥(斌哥)、小弟(李宣等)、女人(巧巧)、中间人(拥有警察与黑帮双重身份的万队)等组成的江湖人物群像。其次,《江湖儿女》对黑帮片的借鉴还体现于对“江湖秩序”与“兄弟情义”等核心类型要素的打造中,开篇第二场戏即通过斌哥调解老贾与老孙的债务矛盾,树立起以关公所代表的道义为意识形态约束的江湖秩序,在这个有序的江湖中,斌哥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港式黑帮片中的“话事人”,即最有发言权、可以做决定的人。第三场戏伴随着叶倩文的《浅醉一生》展开,这是贾樟柯在《小武》《站台》《二十四城记》后,第四次在电影中使用《喋血双雄》的主题曲,以营造一种江湖感的氛围。此间,斌哥与一众兄弟喝“五湖四海酒”的场景,伴随着“肝胆相照”的台词,迅速建立起了20世纪80年代港式黑帮片黄金时代的江湖气象。
除此之外,“暴力美学”作为香港黑帮片最为重要的美学特质,同样渗透于《江湖儿女》的叙事之中。不同于《天注定》对“暴力”行为的严肃思考,《江湖儿女》中的暴力场面更具形式化的审美意味,斌哥与飞车族小年轻的打斗场面作为片中唯一被正面展现的暴力场景,呈现于4K的超高清分辨率镜头与浓郁艳丽的色调之中,斌哥从容不迫破窗而出的动作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流畅的运动长镜头以小景别穿梭于打斗场面之中,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伴随着巧巧的枪声再次响起,抽了一半的雪茄与皇冠车标上缓缓滑落的血迹,预示着斌哥江湖生涯的终结。在这里,大哥成为时代暴力的受难者,枪既是保命的武器,亦是通往牢狱的诱因,主角的暴力行为被赋予了自保的正义动机,并伴着肝胆相照的兄弟情义与生死相随的恋人之情,李宣的挺身而出,巧巧的义无反顾,给这场热血街头的暴力行为蒙上了浪漫而温情的色彩,暴力美学的道德困境在“他们以身相许,如此红尘笃定”{7}的情义之中消解了。
贾樟柯在采访中提及《江湖儿女》的创作初衷,“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能拍一部电影,写写我们的江湖。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8}。“街头的热血”是黑帮类型片之所长,在第一叙事段中已被渲染地淋漓尽致,而“时间的雕塑”显然是文艺电影之所长,因而在《江湖儿女》后两个叙事段落中,港式黑帮片的类型色彩快速退却,转变为贾樟柯惯常的写实路线,叙事重心由斌哥转移到巧巧,斌哥的由江湖内而江湖外,与巧巧的自江湖外走入江湖中,形成了时间洪流中两条逆向的人物命运轨迹,其间人物身份与自我认同的变化已然超出了黑帮类型片的范畴,呈现出更为符合现实逻辑的生命常态。
贾樟柯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江湖儿女》的重点在于“儿女”,而非“江湖”。“叙事性作品最核心的创造所在,是寻找、塑造出可信可感的人物形象。无论采用哪一种电影语言、电影方法,人应该是电影一直关注的重点和焦点”{9}。类型电影颇为倚重、精心构建的情节因果关系,在《江湖儿女》中被淡化,着力突出的则是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如黑帮片中主角的敌手在《江湖儿女》中是隐而不显的,二勇哥被杀与斌哥被袭击的缘由被归于年轻人想出头,这种无因的暴力指向的是时代变革中社会结构的失序,“时代”这一抽象而宏大的名词取代了黑帮片中具象化的敌手,成为阻碍主角实现目标的主导性力量。这里所说的“时代”,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有着明确的所指,即我们身处其中的、亲身经历的中国社会转型,电影中人物命运的浮沉,昭示着商品化经济浪潮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摧毁与重建。在这样强大的现实逻辑面前,《江湖儿女》的情节叙事走向了黑帮片类型规则的反面,锒铛入狱的大哥并未东山再起,曾经“肝胆相照”的兄弟也未能坚守“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江湖道义,第一叙事段中少年意气的江湖气象仿若一场大梦,梦醒时分是贾式江湖的中年颓丧、一地鸡毛。
在第二叙事段中,利益和欲望成为江湖的主题,与时代对抗的主角从斌哥变成了巧巧,在2006年的三峡这一特殊的时空环境之中,一切固有的东西都在坍塌,废墟之上流溢的是毫不掩饰的欲望,巧巧先后经历了财物被偷、贞洁遭威胁、情感被辜负等多重打击,在饥饿与赤贫的生存危机之中,也不得不走上婚礼骗吃、酒店骗钱的“混”江湖之路,江湖的情义法则与文化精神在此荡然无存。有意味的是,第二叙事段中泥沙俱下的江湖气象,暗合了后九七时代香港黑帮片中“江湖”的转变,“利益与欲望才是今日江湖的主题,义气更成为往昔的童话”{10}。而这昔日童话般的情义江湖,才是贾樟柯真正怀念与心生向往的,第一叙事段中所引用的《英雄好汉》(1987年)与《喋血双雄》(1989年),均为香港黑帮片黄金时代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情义”远超过“利益”,男人的尊严即便面临挑战,也终将通过复仇而寻回并重建。《江湖儿女》中,这一寻回尊严、重建秩序的任务被置于巧巧这一女性角色之上,从而区别于传统黑帮片中或为红颜祸水、或为被拯救对象的女性形象,许多评论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然而,正如贾樟柯所言,“我不是在赞美女性,我是在反思男性”{11},巧巧身上所寄托的是贾樟柯对情义江湖的怀旧,是昔日大哥而今泯然众人的叹惋,这种执念使得巧巧在仰望星空奇迹降临时刻的顿悟,化为对斌哥理想的继承,在她面前看似有广阔的天地,她却自愿回到了大同,重建作为主角的斌哥与作为导演的贾樟柯等男性们恋恋不忘的江湖旧梦。
三、中国工业体制中的电影作者
陈旭光教授认为,电影工业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做好‘体制内的作者’”,而这个体制指的“不仅仅是票房、商业化市场、制作、营销等的要求和现实规则,也是中国社会体制、道德原则和现实规则等本土性要求的总和——例如中国的电影审查制,‘接地气’的要求,老少皆宜合家欢的理想”{12}。以第六代导演的身份踏入影坛的贾樟柯,同样需要经受“中国式体制”磨合的过程,与一些顽强坚持的第六代导演不太一样,贾樟柯走过了一段由体制外的独立制片向电影工业体制迈进的道路。《江湖儿女》以高达8000万的制片成本,打破了贾樟柯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低成本文艺片路线,实现了创作上的“工业化”转型。尽管作为典型的作者导演,贾樟柯在《江湖儿女》的项目操作中依然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但面对相对文艺片来说如此高额的投资和当下中国电影不可逆转的工业化趋势,贾樟柯在创作观念与实践层面均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体现出作者导演对电影工业体制的灵活借势与把握。
这一“工业化”转变首先显现于《江湖儿女》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多达12家的出品公司远远超过了贾樟柯以往电影的融资渠道。《江湖儿女》开启了贾樟柯电影新的融资模式,即以电影人为主导的独立制片公司(贾樟柯名下的北京西河星汇影业)、海外资本(法国影视公司MK PRODUCTIONS)、老牌国企和民企(上影集团、华谊兄弟)、新兴影视公司(欢喜传媒、自在传媒)、互联网企业(淘票票影视)相互联合,以共担风险、资源互补的合作式融资结构。除此之外,贾樟柯在进行融资之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考量,力图选择与自身创作理念相符合的影视企业,借由中性的资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保障艺术品质的同时,努力寻求与资本和市场和谐共处的方式。
如此高额的投资之下,《江湖儿女》在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转向。除了启用柏林影帝廖凡作为主角之外,在配角的选择上亦启用了徐峥、张译、冯小刚、张一白、刁亦男等明星演员和导演进行客串,显然有着电影宣传与票房上的考量。此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流畅而动态的镜头设计、摆脱粗糙走向细腻的影像风格等,也使得《江湖儿女》在故事性和美学风格上更亦被大众所接受。尽管贾樟柯依然强调冷静和克制,强调电影的开放性和多义性,但却不再将作者电影和工业电影截然对立,而是认为“如今作者电影也开始逐步强调传播,而工业电影亦逐渐体现出作者的色彩”{13}。不断完善的电影工业体制和电影市场环境,为艺术电影和文艺片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江湖儿女》《地球最后的夜晚》等艺术电影,凭借导演和主创的知名度及多样化的宣发手段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主流商业院线体系中取得了对于艺术电影来说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
正如贾樟柯所言,“选择用电影来表达自我,就选择了一个大众媒介。”{14}为了获取更多的观众,贾樟柯开始主动寻求在工业渠道内宣传和推广电影,知乎问答、虎扑发帖、与流量明星杨超越的跨界对话、《我就是演员》和《朗读者2》等综艺推广,加之以积极的微博宣传和线下路演,《江湖儿女》可谓贾樟柯作为导演参与宣发环节最为深入的一部电影。相比前作《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在营销热度、票房收入、观影人次等层面的提升是巨大的,6994万的国内票房已然是贾樟柯电影至今为止最好的票房成绩,尽管相比8000万的制片成本来说,6994万的票房收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贾樟柯这么多年来能够持续稳定地进行艺术电影创作,与其独特的品牌经营和营收渠道密不可分。作为拥有超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导演,贾樟柯几乎每部电影都入围了世界知名的国际电影节,并屡屡获奖。相应的,其电影的销售模式也非常国际化,从《小武》开始,国际发行和版权收入就是贾樟柯电影的一大收入来源,每年世界各大电影节在举办电影竞赛与展映之时,版权交易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据称,在《江湖儿女》上映之前,MK2已经卖出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9个国家的电影版权{15}。这些版权包括海外的电影发行权、院线放映权、电视台放映权、DVD等音像制品复制权等。这一独特的品牌经营与销售模式,为贾樟柯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与更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随着贾樟柯在国际上知名度的提高及其电影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意义,贾樟柯由曾经体制外的独立电影人转变为体制内的重要角色,2015年担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2016年出任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201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的转换使得贾樟柯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对完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培养电影创作人才的呼吁和实践,对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目前,贾樟柯名下拥有西河星汇、暖流文化两家电影公司,并入股以上传媒,成立青年电影短片新媒体平台“柯首映”,扶持青年导演创作;2017年发起创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反哺故乡、培育地方电影文化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广泛对话和交流。在中国电影工业不断发展的当下,贾樟柯不仅借势增强了其电影创作的影响,也以其实际行动不断推动着中国电影工业体制的完善,在电影作者身份与工业体制运作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平衡。
然而,作者电影与工业体制在相互借势之时,亦相互掣肘。《江湖儿女》在走向市场之时,同样面临着艺术电影商业化运作的困境,即在扩大受众范围的同时,遭遇着影迷群体的不满与普通观众的不解。《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影片“是个用灰暗镜头讲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的负面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观众的心理预期和艺术电影的叙事风格之间的落差,营销中着力凸显的“黑帮江湖”“情深义重”“儿女情长”,在电影中表现为江湖不再、情义消散、英雄气短,对于不熟悉贾樟柯电影的普通观众来说,本想看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爱情故事的观影预期并未达到,也难免会“心里有点堵的慌”。《江湖儿女》与同档期电影相比,在文青聚集的豆瓣获得了较高评分,而在普通观众更多的猫眼和淘票票平台,其评分则明显低于另外两部商业电影。而这正是艺术电影在跨圈层传播之时不可避免的困境,同样的问题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在此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类型叙事与作者风格的融合,如何准确地把握营销宣传与影片内容的契合度,成为《江湖儿女》等艺术电影能否顺利走向市场的关键。
其中,《江湖儿女》与港式古惑仔电影《黄金兄弟》的对比颇有意味,同为主打“江湖情”的影片,《黄金兄弟》在宣传中着力渲染郑伊健、陈小春等“古惑仔二十年再聚首”“港片再雄起”“友情岁月和青春情义”“并肩作战与动作戏场面”,以打造纯正的港式江湖和兄弟情义,从而与《江湖儿女》的本土江湖和儿女情长形成鲜明对比。从营销热度和票房收入来看,《黄金兄弟》对港式江湖怀旧式地重现显然更符合大众对“江湖”的想象,并在类型叙事的成规中满足了普通观众的观影期待;而《江湖儿女》反类型的叙事方式,在成就影片艺术深度的同时,也抛弃了类型电影的观影快感,在主流院线的票房竞争中自然难以胜出。
《江湖儿女》所遭遇的自我重复、类型夹生等多重批评,反映了影片的商业诉求和艺术追求之间的断裂,亦表明近年来的贾樟柯正在努力寻找作者性与体制性、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努力从《山河故人》之时便已初见端倪,并始终伴随着评论界及影迷群体的不满和非议。然而,在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工业化和产业化语境中,艺术电影若想在主流院线市场中分一杯羹,就必须面对艺术性/商业性、作者性/体制性之间的矛盾。对此,“电影工业美学”或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作为当下学界对中国电影的最新思考,由陈旭光教授提出的“电影工业美学”,要求“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16}此间,类型电影创作、“体制内的作者”作为“电影工业美学”在文本内容和生产机制层面的重要内容,正在成为贾樟柯等部分第六代导演进行转型的关键,如陆川的奇幻电影《九层妖塔》,娄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融入了犯罪片的类型元素。但转型的同时,他们也普遍遭遇了类型夹生、艺术水准降低、偏离作者性等批评的声音,而刁亦男、曹保平等新力量导演则深谙“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如刁亦男在黑色电影类型框架下创作出的《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曹保平的犯罪悬疑电影《烈日灼心》《追凶者也》等,都兼具艺术性/商业性、作者性/体制性,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在主流院线市场中也收获颇丰。与之相比,贾樟柯在处理作者电影与类型叙事的关系上,则显得颇为犹疑,从而使得《江湖儿女》呈现出前文所述的风格上的显著断裂。而其新作《在清朝》,据称是贾樟柯首部商业类型片,由此可窥见贾导走向市场的雄心,而作者电影的类型化,显然是其所选择的走向市场的策略,我们期待在新片中看到贾樟柯的进一步转型。
在中国电影工业体制和市场规范不断完善的当下,曾经以体制外独立制片而登上历史舞台的第六代导演,开始更为深入地参与到电影工业体制的运作之中,其作品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商业性。在此过程中,艺术与商业、奖项与票房、作者表达与工业体制之间的矛盾与耦合,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并竭力去平衡的问题。贾樟柯作为其中较为偏向艺术天平的一方,在近年来的创作中也开始尝试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型,从《山河故人》到《江湖儿女》,再到据称是贾樟柯首部商业类型片的《在清朝》,这一转型的过程将始终伴随着本文中所探讨的作者风格与类型叙事、作者导演与工业体制、艺术电影的市场化生存等诸多问题。《江湖儿女》作为贾樟柯转型路途中的重要驿站,携带着过往的余绪与未来的征兆,成为探讨这诸般问题的典型文本,至于它将通向何方,未来会给我们答案。
注释:
①贾樟柯、王泰白:《我不想保持含蓄,我想来个决绝的(对谈)》,载贾樟柯:《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②Julia Kristeva , Bakthine ,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Sèméiol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1969,P.146. 转引自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③这一作品后由朱石麟、齐闻韶在费穆导演筹备的基础上完成拍摄,于1952年在香港上映,讲述的是忠义技术团流浪卖艺的江湖生涯,与团员之间的爱恨情仇和伦理故事。
④贾樟柯、梁文道:《梁文道对谈贾樟柯:我们都是无辜卷入时代的“炮灰”》,看理想公众号,2018年10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27_yQY15pfcpvC1opFF61
w)。
⑤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载贾樟柯:《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⑥贾樟柯、余力为等:《在<天注定>第一次主创会议上的讲话》,载贾樟柯:《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⑦⑧贾樟柯:《江湖从头说》,《青岛报纸》2018年9月24日。
⑨{11}贾樟柯:《我不是在赞美女性,我是在反思男性》,《青岛报纸》2018年9月24日。
⑩左亚男:《黑色江湖:类型中的对话 后九七香港强盗片研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2}陈旭光:《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13}贾樟柯、寇淮禹:《贾樟柯:当代艺术影响了我的电影创作》,《新京报》2018年12月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1339895751240160&wfr=spider&for=pc)。
{14}江宇琦:《为什么观众不买贾樟柯的账》,毒眸公众号,2018年9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e_trsbEiph0M
l3wbNTDBiA)。
{15}斯塔西:《谁在为贾樟柯的高价文艺片买单?》,娱乐资本论公众号,2018年9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j_Z
qryarGbYpp4p7apyotA)。
{16}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