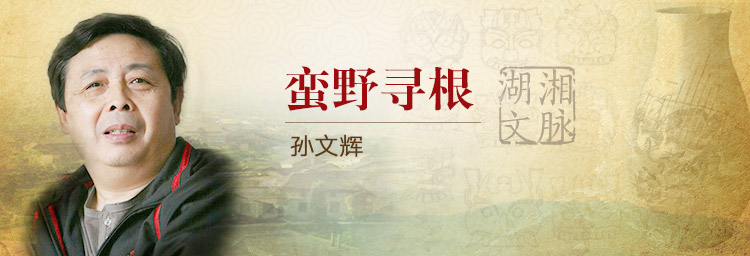

侗族文化在湖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特点十分显着,但这个民族的起源却众说纷纭。
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通志·武备志·苗防一》载:“苗有倮、瑶、僮、仡佬、伶僚之分,其处广西边者为僮,处云南边者为倮;处湖广零陵、宝庆边者为瑶;处靖州、天柱等处,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者,为仡佬、伶僚,皆苗也。(《辨苗纪略》)”侗族,就是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之伶僚。
魏晋南北朝以来,侗族的先民被泛称为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侗僚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明史》称侗族农民起义领袖吴勉(贵州黎平兰洞人)为“蛮僚”。明代邝露在《赤雅》中说:“侗亦僚类。”
唐、宋、元、明、清时期,封建文人多称侗族为峒民、峒蛮、峒人、峒苗、侗人、洞家等。侗族内部有三种互称,一为gaeml laox (金佬),二为gaeml jaox(金皎),三为gaemldanx(金坦)。gaeml或jaeml的意思是两山之间的谷地或者溪河两岸较为平坦的小盆地。侗族人民喜欢居住在依山傍水的山谷与溪河两岸的盆地中。这种地形,历史上多称为峒或垌。住在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峒民”或“峒人”。
自唐以来,封建王朝在湘、黔、桂边区设置羁縻州峒进行统治。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说:“羁縻州峒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至今湘、黔、桂三省(区)交界的侗族地区,仍有不少村寨保留着峒的名称。历史上把居住在州、峒里的少数民族称为“峒丁”、“峒民”或“溪峒之民”。后来演变为对侗族的专称。
在明代,统治者为“隔越汉境”,在洞口、洪江、会同、武冈等地域迁徙大量汉人,将苗人聚居区“不得与靖州相接壤”(《湖南通志·武备志·苗防一》),结果,苗、侗被隔越的同时,侗族也被隔断为北侗与南侗两个文化区域。
在湖南,新晃、芷江地区成为了北侗文化区,其地的文化受苗族文化的影响增大;而自身的文化特征逐渐淡化。
而在南侗地区的、特别是通道县,侗族文化特征更加明显,强化。
造成这种隔越的重要原因,就是明初的苗侗农民大起义。
侗族古歌唱道:
兰洞生下林朝素,黎平生下吴勉王,
三千天府,九千地门,
白天邀集七千兵,夜晚集合八万人。
兵马杀上古州城,古州无获空回兵。
回身杀到哪里?
打到武冈府、武冈城,
水牛黄牛骡马拿不赢。
官家心肠坏,杀狗杀猫血淋身。
断了黄旗和皂旗,
兵马难前进,只好复转身。
回转到哪里?回到墓乡山岭;
水牛黄牛和骡马,摔断腿脚路难行……[1]
古歌唱的是侗族英雄吴勉和林朝素(Liene xeeuc suv),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明洪武初年,明朝为一统大中国,从靖州往西向贵州“苗疆”实行武力推进政策,今黎平等侗族地区成为首当其冲的前线阵地。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因无法忍受朝廷的武力征服与压迫,吴勉率领当地侗、苗等少数民族发动武装起义。
吴勉(1334-1385),元末明初黎平五开洞(今贵中潮镇上黄村兰洞寨)人,官方史籍中记载为“吴面儿”。
吴勉起义军由上黄出发,先后攻下五开洞附近的各处村寨,然后占领黎平,直捣古州(今榕江),古州官僚逃窜,只余一座空城;义军转身杀向湖南靖州,击败靖州守兵,并杀死靖州卫指挥使过兴父子。
明王朝急命辰州卫指挥杨仲名前往镇压。同年十一月,明军击败义军。吴勉遂率领义军残部退往天府洞(今黎平茅贡)一带的丛林中休整,继续与明军抗衡。
洪武十八年(1385)四月,吴勉自称“铲平王”,再次举起反明义旗。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20万,一度占领今湘、黔、桂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明太祖立即命令楚王朱桢挂帅,出动30万大军。明军到达靖州后,派人前往黎平招降吴勉,被吴勉严词拒绝。明军即以靖州为基地,在诸峒派兵分屯立栅,与土著杂耕;并步步为营,向黎平进剿。吴勉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带领余部回到上黄继续作战。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明军进攻上黄义军总部,诱擒吴勉及其子吴禄,押送京师后处以极刑。
吴勉起义失败后,侗族地区的斗争并未平息。明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在今锦屏县设置铜鼓卫,圈占土地三百五十四顷,激起侗人反抗。林宽(?-1397),贵州锦屏上婆洞人,其父林让曾参加过吴勉起义。吴勉起义失败后,林宽成为了侗族农民起义的首领。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林宽集10万众侗族义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反抗斗争。义军攻克龙里、新化、平茶等千户所。朝廷调湖广军前来镇压,潮门桥一战,官军被杀死千余人,只得退守卫城。后朝廷又调集30万大军进讨,因敌我众寡悬殊,十二月,林宽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侗族农民起义两次之后,汉族屯田军民的大量来到这一地区。据葛剑雄着《中国移民史》统计:“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迁入靖州和辰州两地的江西籍移民氏族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25%,估计民籍移民总数约为15.4万人。”[2]如果加上军籍的屯垦人数,比例将会更大。
经过不断移民、屯田和发展,北侗地区的民族融合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了显着的变化;而侗族民族英雄吴勉和林宽的故事,仍在南侗地区广泛流传,直至今日。
一、战争催生的款文化
不理解款文化,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的侗族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南侗文化。
什么是款文化?
宋人杨诲在《受降台记》中记载:“淳熙三年(1176)靖州中峒姚民敖组织起义,环地百里合为一款,抗击官军”(《靖州直隶州志》卷十)。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载:“门欵:彼此歃血誓约,缓急相援,名门欵。”可见宋时“五溪蛮”就有歃血盟款、相互救援的组织形式。明人刘钦所著《渠阳边防考》记载:“其曰峒蛮者……皆从古无大豪长,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说明在明代,侗人合款已经成为规模和惯例。
款,是一个巨大的、复合的文化空间。它是侗族的军事文化、法制文化、历史地理文化,民族习俗文化和侗族文学艺术的总和。
创始之时,它是民族战争中的产物。
款,首先是一种军事组织形式。
《出征款》这样说道:
一伙寨老,一伙头人,
才是发起联村联河,
才是领头联寨团款。
联村进场,团款进坪。
我们要像蚂蚁聚众杀穿山甲,
我们要像蜜蜂合力刺毒蛇。[3]
在“款”这种军事组织中,一个寨子就是一个“小款”,侗寨沿河建村,寨老和头人们商量,联村联河,几个小款联寨团款,就是一个“中款”。数个中款联合,就是“大款”。
通道县芋头寨杨再善、粟保林口述的《开款坪》中,告诉我们合款的基本情况。这一情况是源于“寨老四汤公,有古书一本,记载了侗家村寨,集众合款各款坪”:
上四洞、四头、杨柳坪合款是第一,
下四洞、陈横合款是第二,
芙蓉、江口、太阳坪合款是第三,
上粟、下粟、上大阳坪合款是第四,
…………
盘董、盘巴、河坪、保俊、上茵坪合款是第十二,
孟寨、甘冲、坪略、上溪坪合款是第十三。
讲了以上十二款场、十三款坪,
大众合意同心。
就这样约定、这样讲成。
立约威力比天大,合款威力大如天![4]
合款的目的是什么?
村脚像个雄龙洞,村头好比雌龙宅,
村中遍地是金银,合款保护各寨村。[5]
大龙腾腾飞上天,联款威力大无边,
老龙跃跃满河江,合成大款保村乡。[6]
龙是侗寨的保护神,青龙与白虎相对而立,守护村寨。合款时,由寨老们选出来的款首《开款坪》,他通过款词,将参加合款的村寨一一报告款众;公布款坪,即众人集合的地方。其中重点款坪、中心款坪或大款的款坪就称为“青龙款坪”。
开款坪时,款首常常发问,款众齐声回应,此时荡气回肠,声势非凡: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下乡、临口!
款首:杨柳坪合款是第一!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双江、黄柏、龙头、吉利!
款首:棉花坪合款是第二!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芙蓉、针定!
款首:九龙庙坪合款是第三!
款众:是啊!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张黄、老湾!
款首:木榄坪合款是第四!
款众:是啊!
…………
款首:讲到哪里?
款众:讲到梓坛、河口!
款首:大河坪合款是第九!
款众:是啊!
款首:少讲多知。说的都说了,讲的都讲了,
带上青龙坪!
款众:是啊![7]
在战争年代,款众集合之后,就有《出征款》。这也是有呼有应,一呼百应的款词:
…………
我们要像猛烈的阵阵过山风,
我们要像天上突降的冰雹。
我们要像雷公施法击妖怪,
我们要像老虎张牙咬妖婆。
打它老鹰灭种,打它鸱枭没命,
分精怪的肉众人吃,
分妖婆的汤大家喝。
不许谁像鸡那样怕老鹰,
不许谁像鸟那样怕鸱枭!
谁当鸡,会被人拖进林子里杀,
谁当鸟,会被人抓在脚底下踩
青年人拿刀,壮年人拿枪
明眼人射箭,心亮人举旗。
团结紧密像簸箕,团结无隙像葫芦,
紧如盆底,硬像铁箍!
我讲这话像皇帝的言语。
(众)对啦,是啊!
龙头摆,龙尾摇,
弟兄们,拼命打!
龙头立,龙尾抬,
兄弟们,打得好!
好日好时,旗开得胜,
让我们起款出征吧!
(铁炮响起,队伍出征)[8]
二、和平时期的村规民约
战争把侗人团结起来,也使侗寨成为了一个极有组织的社会。
在漫长的岁月里,战争毕竟不是经年累月之事,为了使自己的氏族常备不懈,“款”,即变化为“条款”的形式,成为一种乡规民约。
“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侵来祸难息;祖先为此立下款约,订出侗乡村寨的俗规”。最早的俗规是从防护开始的,通道县粟保林、石万顺口述的《立约》,留下了款首对庚辰村、前戊午村、后戊午村、大坪村等寨子的防护部署:其中村脚、河边、村中、村头、每个寨子都由谁来把守。“村村有人把守,寨寨有鸡报时,事事有人处理,防备村里出事。”在布防的同时,也指出某些人的陋习:“四通有个龙姓人,塘作三破,田作三卖,卖田不卖田塍,留田塍种豆,留田坎种菜。务农怕劳累,懒做又好闲;脚歪心不正,手勾又眼浅。”同时,也讲到其它寨子的一些妇女,“裙带不捆紧,裙子不穿好,蓬着头、拖着发,三天不洗头臭如蚯蚓,九天不洗澡臭像死蛇,”[9]虽然,这《立约》款中未列出处罚条例,但款首是以这些陋习来警示众人,号召“共同整好寨子”。
款的组织形式被固定下来,到了和平时期,款约就有了发展。款约成为了约束侗人行为的准则;并且,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个村寨内部。
“当初村无款规,寨无约法的时候,好事得不到赞扬,坏事没有受惩处。”因此侗人立下规约,将其刻在石碑上,于是就有了“石头法”。
《石头法》规定了具体的款约,哪些事是允许的,哪些事是禁止的。为了维护款约的尊严,款约同时也制定了评判的标准和处罚的尺度:六面阴(死刑)、六面阳(活刑),六面厚(重刑)、六面薄(轻刑),六面上(有理)、六面下(无理)。如不准偷盗牛羊,如偷盗并被人掌握了真凭实据,就会“把犯者三个一处葬,五个一坑赶时埋。”如不准偷盗钱物,就要游乡示众,连同他的父母一起赶出村寨。如不准窝藏坏人、制造内哄,不准男刁女滑、爱富嫌贫,不准风流浪荡、拐卖强奸,不准移动界石、越界掠夺,不准夫妻打架、相争吵闹。与其相应的处罚也有不同,重的如“破产赔偿,家财荡尽,富者吃穷,贫者吃光”;轻的是赔偿银钱,或让犯者自省。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秉公正直讲理,不准徇私枉法。[10]
款,成为了维系侗族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的支柱。它逐渐发展成为侗款文化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的部分。
三、侗人史话
侗款,是侗族世代传承的神话、传说、历史的载体;本属民族的古歌,但由于战争,巫事被款约所替代,古歌也就化解至侗款之中,讲唱的艺术形式在款文化中也演变为吟诵的形式。少数民族古籍之《侗款》一书纪录了侗民族传承的人类创世史、万物源流史、宗支史和民族英雄史。
1、人类创世史:
像众多的民族史诗一样,侗款《九十九公合款》也讲述了人类的来源:
人类最早的始祖母棉必(Miinc bic)在脚乡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蛋坏了,一只白蛋孵出了松桑;棉必在脚山又孵了四个蛋,其中三个蛋坏了,一只白蛋孵出了松恩。这样人类就有了生儿育女的根。
松恩生下了七个子女,他们分别是蛇王、龙王、大熊(虎)、雷公、姜良、姜妹、猫郎。一天,七兄弟到山里比试技能,姜良让他们各自寻来青藤将自己捆在树蔸上,然后放火烧山。这时,松恩喊道:“虎快进山,龙快进海,蛇快进洞,雷快上天,猫快爬岩,人快去水旁。”这样,众兄弟才幸免遇难。
雷婆公主忿忿不平,要找姜良报复。春夏相交之际,雾满山头,雷响四方。雷婆从天上劈了下来,姜良取来青苔包在头上,雷婆踩着青苔跌了一跤,被姜良捉住,关进了仓里。
姜良上山打猎,让姜妹看守雷婆。雷婆找姜妹要碗冷水喝。喝了冷水之后,雷婆化着闪电破仓而逃,但被姜妹抓住了手。雷婆拔下一颗牙齿,对姜妹说,给你作个瓜种去吧。姜妹接过牙齿,种到地里。她常用扇去扇瓜苗,结下了一只葫芦。
雷婆上天之后,发起了漫天洪水。姜良、姜妹请啄木鸟啄穿葫芦,兄妹坐到葫芦里,救起来一群黄蜂。黄蜂与姜良一起上天与雷婆打仗,雷婆被黄蜂螫得像只鼎罐,只得请来野画眉与姜良的画眉谈判。雷婆做出了七个太阳,将洪水晒干。但七个太阳又将大地烤得烁热。姜良又让螟蛉虫上天去砍太阳。螟虫砍了五个半太阳,姜良就让它住手。因此,半个太阳成为了月亮。
姜良、姜妹分头去寻找人类,但都没有找到,只得回到家乡,一起居住。三年之后,他们生下一个孩子来。孩子是个怪胎,无头、无耳、无腿、无脚,像个冬瓜一样。手放到哪里他哪处吮吸,饭放到哪里他哪处吃。姜良就把这个孩子丢弃在山冲口。
天上的仙婆看到就拿刀来砍,把孩子砍成了五份。这样肉变成了侗人,善良温顺;骨变成了苗人,强悍坚硬;肠变成了汉人,聪明乖巧;剩下的肝和碎肉变成了瑶人、壮人、花衣苗人……
从此,人类又繁殖起来,布满了平地山岭。
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在各个古老民族的神话中都见到过的“碎尸”神话。
同样,在通道县坪坦阳烂挖掘整理的《人的根源》也讲述了这个故事,不同的是,八个“兄弟”按长幼分别是母帝、龙王、虎郎、猫郎、蛇郎、雷公、姜良、姜妹;姜良和姜妹是最小的弟妹。而姜妹生下的儿子“白饭不吃,甜奶不喝”,也是个怪胎。
在城步县八村挖掘整理的《人的根源》讲述的这个故事所不同的是,这个儿子被碎尸之后,手指变成了山岭、骨头变成了岩石、头发变成了山泉溪水、脑壳变成了土塘田地、牙齿变成了黄金白银,肝肠变成了长江大河。
这些都与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神话相似。
2、万物源流
在这一类“创世款”中,《侗款》一书还纪录有《行年和芦笙的来由》《牛的来由》《猪的来由》《鸡的来由》《鸭鹅的来由》和《龙灯的来由》等传说。
《行年和芦笙的来由》,“行年”,该书注释曰:“侗族有以村寨为单位集体做客的传统娱乐活动,即是甲乙两寨先有预约,在春节期间甲寨的男女老少吹着芦笙到乙寨做客,乙寨则以东道主的身份,大办酒席并吹芦笙迎接,为期三日,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11]款词是这样讲解“行年”的起源:“行年根由起何处?是那古州起的根。”这仅仅说了“起源”的地点,而起因也非常模糊:
说起原由话长,
因为姜良置规章在前,
姜妹置约法在后。
父置田塘在山林,
母开金路给人行。
父办鸡尾插头上,
母织暖布盖在身。
换了老竹长新竹,
换了长辈换年轻。
老的过了后生接替,
父辈过了儿孙继承。
兄长过了,小弟随后跟。
到了我们这一代,
说什么不稳准,
讲什么不成文……
结果,也未说出什么根由。人们把讲款的人称为“款师”,往往款师的记忆也有差错,款师间的传承也有遗误,行年的根由也就变得不明不白了。
再看芦笙的来由:“根由起何处?是那古州起的根。”款词说道,也洞的陈现是制造芦笙的人,他试制吹管乐时,开始用木簧、继用竹簧、再用牛角簧,结果都吹不响。他的父母拿出银两,让他去靖州、黎平寻找,结果,转到古州六洞买到一斤响铜、二两白铜,请铜匠锻成簧片。有了铜簧片,陈现再用竹管钻孔,装上簧片,分别制成格列、各略、纳鲁、筒耿、筒辅、筒头等各种型号的芦笙。从此,“笙歌缭绕飞满天,小伙翩翩游乡间”。
《牛的来由》,说的是在神农时代,人们开荒种田用锄用耙好费力。一天,神农去到海边观看,看到波涛中冒出金水牛一对。玉皇大帝吩咐道:“你们去人间耕田,什么地方都要耕到。”水牛道:“只要百姓莫拿刀,官府莫杀牛,我就能做到。”玉皇大帝答应了牛的请求,从此官府不再杀牛了。这里,我们看到了王朝禁止“杀牛祭”的历史,演变成为了神话。
《猪的来由》,准确的说,应是“家猪的来由”。款词告诉我们,在大山深处,住着杨姓父子,他们种豆种菜,都被山猪吃光了。他们邀欧姓父子和陈姓父子等四个寨子的人,围捕了山猪;并请木匠造猪圈,用潲、糠、碎米、包谷喂山猪,结果猪身上长起九层肉、九层油。侗家就用这猪肉待客。这就是猪的来由。
《鸡的来由》《鸭鹅的来由》同样描写的是野禽到家禽的识货过程。
《龙灯的来由》说的是禹王开河道,一直开到了海边,看到龙王爷追逐一颗宝珠,特别好看。后来汉人朝见皇帝,叫人扎个龙灯,庆贺新春。侗家学习汉人,也做龙灯来祭天敬神,从此风调雨顺,国家太平。
万物的来由虽然有些简单,像是些低幼阶段的学习资料,但在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款师们所作的知识的启蒙,还是值得肯定。
4、侗族迁徙史
侗族也有自己流离颠沛的历史,侗人通过侗款将其保留下来。
《侗款》一书的《宗支款》,就形象地记录了芋头寨人的迁徙史。
通道县双江镇芋头侗寨古建筑群,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通道县西南9公里,占地11.6公顷。明洪武年间(1368—1398)始建寨;明嘉靖三年(1508)户增人旺,建筑规模扩大,形成村落。清顺治年间(1644—1661)遭火灾,复建后形成以芋头溪流为轴线向两边分布的7个聚居群。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建寨脚桥及龙氏鼓楼、牙上鼓楼。清嘉庆五年(1800)建中步桥和塘坪桥。清道光、光绪年间分别维修驿道和牙上鼓楼。
芋头侗寨古建筑群因山就势,结构造型具有典型的侗族风格,鼓楼、门楼、芦笙场、古井、凉亭、萨岁坛、古墓葬群、侗族楼屋及青石板驿道等一应俱全,其中鼓楼4座,花桥3座,门楼1座,古井2口,萨坛2个,吊脚楼居室78栋。芋头侗寨的建筑属于典型的山地沟谷侗寨山脊型和山谷型建筑模式。寨内民居采用“杆栏式”建筑为多。有的采用架立的吊脚楼式,以适应南方山区气候湿润,多蚊虫的特点。屋顶悬山式,盖小青瓦或覆以杉皮,使得建筑物色彩朴实,质感宜人。寨内的1.6公里长,1米宽的驿道为明万历年间修建。
《宗支款》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侗族老人杨进文捐献的抄本进行的整理。心口相传,芋头寨杨氏的历史被生动地记录在字里行间。
芋头寨杨氏的祖先,随同罗、曹、石、陆、张、徐、李、陈等九大宗族,从江西府太和县[12]迁徙了到湖南衡州一个叫“湖洋、洋学”的地方。因为战乱,不久又迁徙到靖州飞山寨。由于飞山税捐沉重无法生存,九族人又迁徙到通道犁头岭。但此地干旱无水、无法耕种,他们又沿河而上,来到了江口太阳坪。九姓人居住在一起,人多地少,只好杀牛祭天,卜问生息之处,结果,由于意见不和,非议难当,杨氏一族只好迁往他乡,来到平溪。不久他们又发现平溪人偷盗成风,只得迁往下乡、琵琶、七树。杨氏一支来到此地不久,又因这里的人礼仪繁复、人情债难于应酬,又举族搬迁至黄柏。至黄柏又因为与当地人的一次争吵,被迫迁往龙头。又由于缺水迁往格龙格坳。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先后搬迁到了旋美洞琵琶寨,格山,应溪禾、溪冲头。
在这里,杨氏宗族一支开始出现了可以道出祖先名字的谱系:岩雷、正雷—→通成、明胜—→胜再、传再—→文龙、胜龙—→全花、松文—→正雷、富雷、元雷……文龙—→胜龙、胜虎、胜文、胜武—→正道、正明、正法、正富、正贵—→秀香、秀山、宝南、宝兴—→保杨、保通、友定、有传—→庆海、庆相……
如同芋头寨杨氏的《宗源款》一样,通道县黄柏乡杨氏的《祖先古州来》,通道县梓坛乡石氏的《祖宗从古州来》,也都讲述了自己家族的迁徙史。古州,即今贵州省的榕江县。这两支宗族,就是从榕江迁徙至通道。他们与芋头寨的先人,是来自不同的两个省份。
少数民族的迁徙史文献一般存世不多,侗款为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侗款,是一种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因为,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侗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侗寨也已打开寨门迎来八方宾客,侗族文化进入当代,也不可避免地融入未来的社会,但侗款的曾经存在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珍惜它、保护它、传承它,让它依然“活”在侗寨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它能有活态的形式保存到未来,它必然是我们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是我们侗族一种独有的文化财富。
[1]《侗款》P258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2]葛剑雄《中国移民史》P352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3]《侗款》P241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4]《侗款》P12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5]《侗款》P12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6]《侗款》P16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7]《侗款》P16-1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8]《侗款》P241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9]《侗款》P40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0]《侗款》P4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1]《侗款》P357 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2]这里,有一些疑问。从江西太和迁往湖南的氏族,均为宋代迁徙的汉人;而且这些汉族达到梅山地区后,即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安家落户,开始修编自己的宗谱;不会去“杀牛祭天,卜问生息之处”,更用不着迁徙至湘西南边陲。在宋开梅山后,少数民族叙述家庭史时多隐瞒自己的族籍和历史。


孙文辉,湖南益阳人。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编剧。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湘文化研究会、梅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扫码下载时刻APP
扫码下载时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