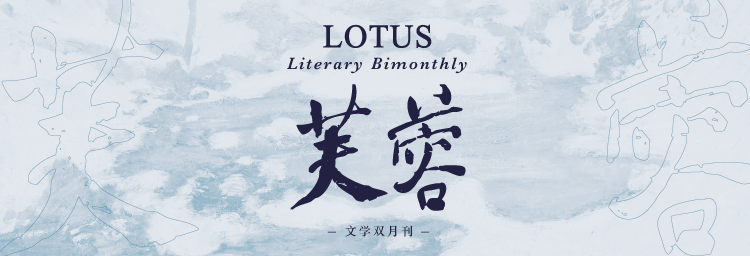

海边的向日葵(中篇小说)
文/肖勤
一
那天凌晨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干瘦的修车仔抱着个婴儿来看急诊,说换尿布着了凉,幺幺咳了一整天,刚睡着,他怕半夜醒了再咳,抱来让青玉给开点药。
不咳的药就行。满身机油渍的修车仔表情焦灼不安,说到幺幺刚睡着时,下垂的眼皮不停抖动,他伸出手抹了抹眼角,那是一双与他年龄完全不相符的手,异常干瘦、骨节突出、指甲漆黑、指缝中也全是黑色的机油渍。青玉有些心痛,但她还是带着职业性的不满询问——白天就咳为什么半夜才送来?宝贝妈妈呢?
他妈……跑了,我白天忙修车。修车仔说着眼圈红了,抱紧怀里毯子裹着的婴儿,毯子很旧,已经洗得半掉毛,上面粉色猪小胖图案脏得不行,像极了一只被人遗弃的小脏猪。
那时候青玉压根没想到这个生病的婴儿有问题,她只觉得眼前是个可怜的打工娃,没承想遇到的会是狼。还好职业使然,她绝不可能不看病人情况就乱开药——必定是要看一眼孩子的。
你把毯子揭开我看看。她搓了搓手,让即将接触婴儿的手指变得温暖些,春夜的诊室有点寒凉。
修车仔却慌乱挪开,哀求说不看了吧,一动他就醒,又得咳,下午咳得都吐奶了,奶粉贵。
青玉心头一软。
她和于合结婚快十年了,还没有孩子,于合说不急。可每次看到软软糯糯的奶娃她总会心颤。
于是她用羽毛般细柔的声音说,还是要看看的,我动作轻一点。
不看了,你就开点药吧。修车仔坚持,开点止咳糖浆什么的,幺幺不娇气,喝点糖水就好了。
青玉温和地笑了,说,你大半夜跑来看急诊就为了开一瓶止咳糖浆?什么止咳糖浆管用?你要自己会开方子还来医院做什么,对吧?说话间,修车仔紧张的表情和他那头枯黄的头发让青玉的脑子莫名响起警报,心头没来由地咯噔一下,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于是,趁修车仔不注意,她迅捷伸出手,一把掀开虚掩在婴儿脸上的毯子,手指不经意间触摸到一片冰凉。
只瞥了一眼,青玉顿时全身发麻。
那是个死婴,面色乌青。
之后的事青玉记不太全了,她当时实在吓坏了,满脑子都是小婴儿,恍惚间那小婴儿竟睁开眼,死死盯着她,小眼睛血红……再一转那血红的眼珠又变成了修车仔的,他像一匹顶着秋天草垛的疯狂的狼,眼里长出獠牙,死死咬着她,然后大声狂吼——害死人了!医生害死人了!
午夜时分的医院顿时像涨潮的海水一样翻涌起来,杂乱紧张的脚步声纷至沓来,医院这种地方向来是不缺人的,不到两分钟,整个走廊和大厅便挤满了,连送外卖的小哥也丢下摩托不甘落后地挤到人群前面来。人人皆媒体的时代,无须提醒,有人录像有人拍照,兴奋成一团。
惨白的灯光下,年轻人抱着死婴在大厅里狂声嘶吼——就是她!就是她!大半夜的,我来了一个多小时,她却在睡觉!就是她耽搁时间,害死了我娃!
青玉无辜茫然地呆站在大厅导诊台前,完全傻了,眼前白晃晃全是手机,都对准着她,她下意识挡了一下脸,但这个动作让她显得很心虚,混乱中她大脑一片空白麻木,又仿佛塞满了东西,婴儿死亡的气息和那青紫色的嘴唇,像福尔马林液体一样湿答答包裹着她,人们在说什么、吼叫什么、对着她照什么,她完全不知道……她只看到院办张主任和院纪检室的李主任急火三丈冲将进来,铁青着脸,他们没有跟她说话,甚至青黑的眼眶和白冷的眼仁中还带着划清界限的生冷和戒备。
查监控。主任皱着眉,冷静地控制住局面。
青玉长长松了口气,回头间却看到满脸泪水的修车仔站在人群中,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却又如释重负的表情。青玉来不及思考,只觉得很快事情就会水落石出。
电脑屏幕上,凌晨一点二十一分,修车仔抱着婴儿冲进大厅,步伐零乱,他挂了急诊,然后跑到她诊室门口。画面里,修车仔伸出手,明显有敲门的动作,然后他停下来,探了探头,缓缓坐到旁边的候诊椅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抱着婴儿到门口停顿张望,再次敲门,最后又退回来坐下。直到凌晨两点二十九分,他才再次走到门前,推门而入……
她值夜班睡着了,就是她耽搁了我家幺幺,幺幺才八个月啊!修车仔紧抱着死婴,动作夸张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
青玉怔怔地看着屏幕。
现在她全身是嘴也说不清。
她哪里睡觉了?算算她已经失眠好几天了,修车仔只是做了个敲门的假动作——他知道医院有监控,他的敲门和等待都是圈套,婴儿早在来医院前就死了,否则半夜三更来挂急诊的,谁会老老实实抱着病娃坐在那里等一个多钟头?
但她说不清楚,场面太混乱,死婴又明明白白摆在那儿,惨白的小脸,灰白的小嘴唇,细得像小猫爪一样的小手指,它们无助地卷曲着,像要抓住什么,让人不忍目睹。
尸检!尸检可以查出死亡时间和这婴儿的死因……青玉步伐零乱,追着一言不发的李主任匆匆走出监控室,在拥堵的人群中挣扎出一句。
尸检?人群立即炸开了锅。
青玉忘记了,筑城是一个有着诸多独特风俗的西南边地,比如放在山洞里不埋不弃的棺材、比如幼儿出门必须系在衣襟的剪刀……这个充满现代工业气息的城市,内里依然是神秘古老的纹理,有些习惯是天长日久不容更改的,在这里,惊扰年幼死亡的孩子是最大的忌讳,就连安葬和悼念也必须秘而不宣。
朴素的人群显然被激怒了,他们义愤填膺七嘴八舌地凑上来。
当保安把青玉从挤攘推打中解救出来时,青玉的眼镜已经给打没了,马尾散落,白大褂还被扯掉了扣子,这些都不算,不知挨了谁耳光,脸上火辣辣一片。
快走啊!保安狼狈地躲避着挥舞的拳头,狠推了她一把——你快走。
青玉这才回过神来,惊魂未定地逃出急诊大楼,跑上平安大街,失去扣子牵绊的白大褂像一对白色的蝴蝶翅膀,悲凉地颤动羽翼。一辆辆夜车从她身边拐着弯惊险万分地驶过,她一边狼狈不堪地闪躲,一边回望身后那闪着巨大红十字光芒的急诊大楼。
卖甜酒汤圆的女摊主愕然地看着她,手里的勺子高高举起,在青玉看来,这女人也是要攻击她的,全世界都在攻击她。
她慌张惧怕地看着微胖的女人,往后退了两步,差点被马路牙子绊倒,仓皇间,什么东西从她眼里淌下来,滚烫。她抹一把湿痛的脸,胡乱脱掉白大褂,摔在湿漉漉的地上,转身跑向车流。
二
青玉并不喜欢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四面都是山,又常不见太阳。连绵的群山间,巨大的银色输送管将矿石从山上运到城里,像一条盘在天地间的贪吃蛇,城里到处是巨大的烟囱,它们向城市输送着复杂的气体,除了这令人呛咳的气体,街上到处充斥着汽车尾气、火锅、烧烤和烈酒的味道,浑浊混乱。不像家乡那座临江的小县城,四季温润,干净得像幅画,春雨季节,雾雨笼着青葱的茶山连绵入云端,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这座野蛮生长的城市里有于合,这是她执着地留在这个地方的全部勇气和理由。
雨丝细柔如绒毛,夜半的城市灯火迷离,她的照片在医院门口的宣传栏里闪着朦胧的光芒——那是个知性又冷静的女人,位居筑城十佳最美医生榜首,她目光安然,正对着诗和远方微笑。
然而此时此刻,和那张照片同样面孔的女人却成了一只惊慌失措的过街老鼠,只能且必须在一盏盏窥探的夜灯下扑向滚滚车流。
紧急刹车的出租车司机没有生气,这是医院门口,半夜从医院里飞奔出来的都是需要天使拯救的人。
需要帮什么忙?人到中年锋芒过去,司机声音温和如天使。
她说不出话,握着车门把手的手不停发抖,眼泪成串滴落。
司机收回眼神,缓缓把车驶出平安大街,到了红绿灯才问,走哪儿?
煤、煤矿村。青玉好不容易说出三个字,喉咙里有温热的液体淌过,是的,煤矿村,那里是她的家,她和于合的家。
出租车绕行而上,爬上筑城唯一的城中山,这里是老矿区,曾经繁华喧闹,是筑城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黯淡在岁月的褶皱里。
青玉在半山腰五道拐下车。
司机看一眼黑麻麻的楼栋,突然问她,家里有人吗?
刚逃出劫难的青玉全身一抖,赶紧答,有啊、有。然后跳下车飞奔向院门。
其实家里根本没人,怎么会有人呢?于合已经离家多日不归。
打开门,一股寒湿扑面而来,这个春天总是阴雨不断,墙壁是冰的,空气也是。青玉没开灯,蜷缩进沙发,目光呆滞,脑子里放电影一样不断闪回医院的一幕幕。
从小到大,她一直是个温纯老实的好孩子,成绩好,但不够机灵,所以当不了班长,永远当学习委员。高中班主任常说,这孩子就是太老实,以后成事成在这个上,败事也要败在这个上。这话今天是应验了——现在回想起来,她在候诊大厅里失控地大喊尸检,简直就是作死。
挂钟已指向凌晨四点,于合又不回来了吧?自从她在他手机里翻到那些照片后,于合便避而不见,这在以往的生活中是不曾有的,于合是一只洒脱顽皮的金毛,阳光大男孩那种类型;又有点像拉布拉多,见到陌生人比见到亲妈还亲,总之从来就不是沉默倔强的类型,一个人突然间变成这样,情况显然比青玉想象中严峻。想到这里青玉有些惊慌,什么东西正在迅捷地从她手心消失,她即将一无所有——在这个她抛弃全世界换来的城市。
那些鬼照片眼下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于合回来,这城市除了于合她什么也没有。
青玉摸出手机,翻看于合数日前发过来的旧信息——那个纪录片快播了,改片、加班、不回。
青玉不知道“那个”纪录片到底是“哪个”,仔细想来,这些年两个人各自忙着,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并不多。她在急诊,每天看得最多的除了鲜血就是濒危病人,这样的事回来不想说也不便说,吃饭时不行,睡觉时更不行,那就是没时间了。于合则是忙拍片子,经常一出门就是个把月。二人一个经常上夜班,一个整天不是出了门就是准备要出门,要凑一起吃个饭都有点难。因为作息时间不同,不到三十五岁他俩已经分房睡了,偶尔于合会半夜摸过来,轻车熟路却又匆匆了事,青玉高兴又生气,觉得他不像是来亲热,倒像是半夜起床上厕所,这话说出来恶心的到底是自己,只有不说,但情绪憋着,久而久之她就不愿意了,于合只好黑着脸又钻回他那边睡去。
除非咱们要个孩子。早晨起来,有时青玉会主动撒娇以示妥协。
于合不买账,才华横溢的他对他们现在的房子、车子、位置都不太满意,尤其是房子,这是他父母当年房改时买的厂区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最热闹最俏式的地方,现在成了筑城最旧最老的地方,在山上不说,住的人还鱼龙混杂。
我要让宝宝住在观山湖看风景。于合骄傲地梳理着他桀骜不驯的卷发,亲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还须努力。
没想到革命道路走到一半,宝宝还没要成,于合却把初心弄丢了。那啥,就像科里组织学习时大家哄笑成一团的段子,说老王死了一条狗,他伤心得不行,想给它留个坟,于是跑到山上生了堆火想先把它火化,结果烧着烧着味儿挺香,最后老王忍不住,就把狗肉给吃了。主任老鼎慢条斯理说完,环视了会场一周严肃地说,你们不要笑,这个段子是告诉你们,“不忘初心”四个字说出来容易,要坚持下去是很难的,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把初心给丢了。
老鼎就是个乌鸦嘴。
握在手里的手机从未如此灼热过,犯错的是于合,可他至今都没有主动打过一个电话,她确定要打过去吗?告诉他她需要他。
需要他——这样脆弱又卑怜的话青玉说不出口。自尊心卡着她的喉咙,最终她选择了放弃。
微雨不知何时已停,天快亮时,山顶墨色的树梢影间竟然升起半弯残月,是上弦。月光透过窗帘浅浅淌满屋,如忧郁行走的挽歌,她看着那缕月华,鬼使神差地缓步走上阳台——后来想起这一刻,就跟撞了邪似的。
从七楼向下望,弯曲向上的盘山水泥路像古老致幻的魔法符号,一束车灯沿着它诡异地驶上山,最后绕进楼下的院子,那是一辆白色宝马,它小心翼翼驶过寂静的夜,如划过水波的幽灵,无声地停在单元楼下。
天都快亮了啊,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人,和她一样煎熬在所有人都安然沉睡的夜里。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副驾驶位走出来,洒脱地甩了甩卷发,带点慵懒、带点狂放,正是令她沉醉多年的模样。
是于合。
青玉的心漏跳了半拍后,然后剧烈地跳动起来,像当年初恋时一样,她快乐得变成一只鸽子,伸开白色的翅膀扑棱扑棱想要飞下阳台去。可她还没来得及探出身子欢声低唤他的名字,紧接着又一个纤细的人影从驾驶位钻出来,追上前紧扑向于合。
于合被她扑得急冲了两步才停住,他有点紧张地左右张望,拿手去掰那双手。
那双手却肆无忌惮地紧箍着不放。
青玉愕然张大嘴,仿佛被箍的不是于合,而是她,窒息的感觉一浪接一浪朝她打过来,她紧张的喉咙发出临近死亡的人才会发出的喑哑的嚯嚯声。
好半天,于合转回头用力地推了超短裙一把,好像是生气了、拒绝了,然后眨眼间他又突然把她搂回来,就像歌剧里的演出,生离死别的两个爱人,推开抱紧,诉尽万般离别苦、破除万般世间障,最后生死相许——于合最后决定返回去,打开车门那一刻,他下意识抬头朝楼上望了望,青玉吓了一跳,赶紧缩回脖子,把自己潜藏在黑暗里,心脏咚咚乱跳着,好像偷情的人是自己。
……
上午十点多,青玉在清脆的鸟鸣声中昏昏沉沉醒来,正是红嘴蓝鹊喂育幼鸟的季节,煤矿村后山树林里的鸟鸣声一天比一天嘈杂。
她从沙发上挣扎起身,蓬头垢面地走向卧室。
卧室空荡荡的,没人。
客房、卫生间、书房都没有人,她神经质地翻找床脚,甚至打开所有的抽屉,都没有人。
滞后的记忆终于苏醒过来,是了,于合并没有上楼,他被超短裙牵回了车里。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捉走了。”不合时宜地,她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咯咯咯,她被自己逗笑了,声音沙哑,鬼似的,仿佛不见的真是唐僧。
青玉边笑边打开水龙头,捧起水胡乱泼洒,湿答答的头发贴在惨白的脸上。镜子里有个女人在说话——于合,你不回来,我本来想跟你讲的,我看到了一个死婴,好吓人。
屋子沉静如深海,除了涓细的水流声,无人回答,也无人安慰。
老鼎来电话。
院里的意思,你先在家休息,等网上风头过了再说。老鼎闷声闷气地说。
哭了一早上的青玉这才意识到昨晚的事没完,也就是说,昨天晚上她的天塌了两次,然而这并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现在她还被压在废墟里,却无人营救。青玉颓然打开手机微博,果然在网上看到了陌生的自己,表情惊恐狰狞,下面的跟帖铺天盖地,问候全家的、祝早升极乐的、送她癌细胞免费三件套的……青玉按捺着性子往下翻,到最后实在看不下去,手指哆嗦,眼前发黑,胸口越来越紧硬。凭着医生的本能,青玉强迫自己放下手机镇静下来,走进厨房,她得吃点东西才能撑住。打开冰箱,拿出几个鸡蛋,她想煎荷包蛋,结果接连打四个蛋都掉到了地上。青玉索性将空碗狠摔到地上,胡乱披了件开衫下楼去吃东西——网友都在咒她死,可她要死也得当个饱死鬼。
煤矿村听起来是村,其实是座矿山,20世纪80年代,筑城最老最早的一批厂区房就建在这里,顺着狭窄的山路从山脚到山顶,一路蜿蜒向上全是房子,后来矿没了,厂也没了,煤矿村成了三不管地带,到处是农民、工厂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乱搭的违建房,密密麻麻的鸽子房和厂区房交错在一起,彼此见缝插针、如同天作之合,容纳三教九流,于是整座山成了一个混乱怪诞又充满烟火气的所在,有租房的有吸粉的,有正经开美术音乐培训班的,也有卖臭豆腐卤菜的,当然,还有贩假货和搞手机贴膜批发生意的。
于合不愿意要孩子的原因,是担心这里环境不好——孟母三迁那是亡羊补牢,我们先完成硬件条件这叫未雨绸缪。
厂区房值班室斜坡上有棵经年的老槐树,树皮斑驳,枝条如魔。楼下的老青砖围墙被包装厂的老保卫科长抠开了个洞,一对来自乌江渡的中年夫妻从他手里租过来,螺蛳壳里做道场,竟在小小的洞子里支了个棚架卖起了早餐和油条。
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热腾腾的大油锅刺刺刺发出面条膨胀满足的响声。一旁的长条案板上,一大竹筛油条金黄灿烂地围绕摆放着,像朵喜庆的葵花。再往边上是个小铁炉,上面烧着锅豆浆,汤浓,香气浓郁。
这对夫妇青玉已经很熟了,去年疫情防控期间两口子没抢到口罩,青玉还把家里仅有的一包口罩分了他们一半。
老槐树花期刚至,垂下累累白玉籽般将开未开的花串,在阳光下闪着晶莹光泽,见有人走过来,树下的女人笑得和花一样香甜,美女,几根油条?
她摘下脸上的口罩,清了清干涩的嗓子,说,一根油条、切四刀,一杯豆浆、不加糖。
好脾气的老板娘看清是她,笑容顿时僵在脸上,舔了舔细薄的上唇,尴尬地扭过头,动作飞快地夹了根油条,敷衍了事切了四刀麻利地装进袋子,然后有意无意半勾着滑润的手指。
袋子便缓缓滑坠在常年浸满油的木案上。
青玉伸出的手在空气中尴尬地停留了半秒,最后,她缓缓拾起油条袋,沉默地转身。
还出来晃啥子嘛,身后传来女人压低嗓子的嘀咕声,换成我就不出来了。
谁?咋个了?坐在油条摊旁剥毛豆的老奶立马凑上来。
那个医生,昨天半夜把一个奶娃耽搁死了不认账,还嚷嚷要尸检,唉,巴掌大个娃,尸检这样的话她也敢讲!老板娘叹气,平时看上去多好的人,去年还送口罩给我家。
嘁,送个口罩就是好人?老奶故意提高嗓门说,现在的医院和医生惹不起,我屋头老汉住个院,就花了不少冤枉钱。
没完了是吧?青玉愤然回过头,身后的声音戛然而止,再看几张脸,各看一边,仿佛刚才的聒噪根本不存在,只有脸上冷然的笑意和不屑在太阳的斜光中显得十分真切。
记住,你给我装孙子。老鼎的忠告响起在耳边,不要去跟帖、不要去辩解,要懂策略,一定要降热度,你一个人吵不赢全世界。更何况他们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相信他们认定的东西。
老鼎说得对,青玉强忍怒火,把油条和豆浆扔进身旁的绿色垃圾桶,大步流星地走了。
一整天青玉没有吃东西,阳光照进屋又退出去,云朵在窗外的天空飞逝,最后归于夜色,她还是没开灯,房间里只有笔记本电脑在漆黑中闪着诡异的蓝光,魔鬼一样吐出一条又一条跟帖,句句是利剑,条条都诛心。
二十四小时过去,她已经成了网络红人。呵呵,人生何其有幸,她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名满江湖”。
门锁咯嗒一声响,于合进屋来,齐肩的卷发有点乱,神情也是。
青玉一阵狂喜,于合是特意赶回来安慰她的吧。青玉按捺着激动的心情,佯装镇静地扣上笔记本电脑,端坐在沙发上,身体却微微发颤。
然而于合径直去了卫生间,青玉听见里面响起懒散的刷牙声、水声,然后洗衣机嗡嗡响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于合打着哈欠,提着昨晚和女妖怪离去时穿的那件风衣走向阳台。
他沉默地穿过客厅,仿佛她是个透明体,他完全看不见。
但她却看得见,她看到他跟往常一样,仗着人高马大,懒得用晾衣竿,踮起脚去够晾衣竿,没想到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吓得不轻,狼狈万分地抓住洗衣机边框轻骂了一句我操。
以往这种时候,她肯定会扑哧一声笑起来。但现在青玉笑不出来,她感觉自己正一寸寸淹没在无边的海水中,委屈、绝望,统统涌上来,她挣扎着试探——你没看热搜?
于合停下脚步,表情有点愕然,也许他已经做好了犯忌桃花被兴师问罪的准备,不想青玉另起一行,问的话也无头无脑,搞得他脑子一时转不过来,略显迟滞地反问,忙片子,什么热搜?
没什么,青玉彻底失望——照片的事,你不准备解释点什么吗?
于合歪歪头,无情且残酷地展开一个洒脱的笑容,道,青玉,我们都是骄傲的人,不是吗?
青玉听不明白,她骄傲过吗?她一心都是他和工作。
你是挺骄傲,也很辛苦,不是在拍片就是在拍片的路上,或者说,不是在某些人床上就是在去往床上的路上。青玉冷冷说完,转头看向阳台。
阳台上,那件卡其色风衣正刺眼地高高悬挂着,像战袍、像盔甲、像插到她阵地上的胜利旗帜,还好老天有眼,此时无风,否则它一定会猎猎飘扬给她看。
哪儿来的?青玉故作平静。
于合回头看一眼,不自然地说,自己买的。
你从头到脚连袜子都是我买,什么时候自己买过衣服?青玉冷笑。
那你还问什么?你觉得这样子有意思吗?于合取了根棉签掏耳朵,嘴角扬起,带点痞味,一股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青玉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她正身陷沼泽、一点点被吞噬,他却无视她的生死,甚至还要补上一脚。青玉咬紧牙关,进行最后妥协和争取——于合,我们聊聊好吗?我遇到……
于合霍然起身,声音冰冷,打断她说,我累了,想休息。
(节选自2023年第2期《芙蓉》中篇小说《海边的向日葵》)

肖勤,女,仡佬族,1976年生,贵州遵义人。代表作有《暖》《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丹砂》等,已创作两百多万字小说,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芳草》《山花》等刊,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并入选各年度选本。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小等》《碧血丹砂》。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贵州省第十四、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小说奖,《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等。有作品被译为英、韩、法、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
来源:《芙蓉》
作者:肖勤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