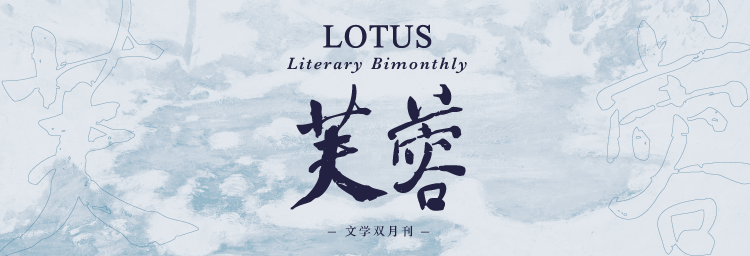

爬行村(中篇小说)
文/石钟山
一
夜生和春草是脚前脚后爬行出村的,之前他们已经约好,在后山那片松树林里集合。他们已经这样约会几次了,每一次都轻车熟路。这一次不同的是,夜生已经下了决心,要让春草成为自己的人。
他们的约会在正午时分,正值盛夏,天气奇热,从天不亮就出门劳作的村民,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鸡和狗在树影下也无精打采,漫上来沉沉的倦意。
夜生和春草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和牲畜,他们悄无声息地向后山梁爬去。夜生这一年18岁了,四肢健硕,他像只猿猴,左右腾挪,跨过了一条水沟,抓住了一块岩石,轻松地攀跃上去,不远不近地就看到了春草。春草比他早出村,正蹲在一棵树下等他。春草年方十六,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脸红心跳,害羞地把头低垂下去,一缕刘海儿耷拉在眼前,春草的样子娇羞无比。夜生就爱看春草这个样子,他为她着迷。
两个人是一年前好上的,在这之前,两人一直眉目传情。夜生的目光大胆,春草在触碰到夜生火辣辣的目光时,像受惊的小鸟,无处飞无处落的样子。就在一年前,春草在自家田地里摘棉花,夜生在自家田垄里锄地,两人在一条河旁相遇了。那会儿天已擦黑,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的,上游也许是下雨了,不宽的一条小河,突然涨满了,来势汹汹的样子。来时这条小河还很平静,潺潺淙淙的,春草记得,自己还在河边洗过脸,梳了头,她冲水面上的自己笑了,她也被自己标致的眉眼打动了。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个美人。
暴涨的河水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夜生会水,别说这条河水涨成眼前这样,就是再涨一倍他也能游过去。春草则不然,她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河水。犹豫间,夜生在她身边说:我背你过去。声音不大,口气却坚定。春草把目光投过来,有几分紧张和娇羞。夜生爬过去,捉住了春草的手,突然发现春草的手又细又滑,他的身子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他拉过她的手,把自己的后背亮给她,她半推半就地伏在他的背上。她嗅到了一个即将成熟的男人的味道,这种陌生的气息,差点儿让她晕厥过去,她无力地伏在他的背上。他说了句:抱紧我,咱们过河了。她醒悟过来,双手从他脖子下缠绕在一起。夜生自然也体会到了她的存在,她在他的背上,化成了一股软香的气体,令他意醉神迷。他不知自己是怎么游过河的,当他四肢触碰到对岸的土地,才觉得时间太短了。短得他似不曾体会,没来得及玩味就结束了。他们的身体分开,他还恍怔着。
就是这一次迫不得已的身体接触,两个人的关系就变了,他们的目光经常寻找着对方,然后蛇样地缠绕在一起,难舍难分又激情似火。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主动约她,他们在后山那片落满松针的树林里,约了几次会,听着风声吹着林涛,发出奇怪的声音,嗅着松树特有的气味,这片松树林就变得圣洁起来。
他四肢着地,轻松地一跃就来到了她的面前,两人的呼吸都开始变得粗重,他伸出臂膀把她揽到怀里,她顺从地贴紧他,他瞬间就涌上了某种冲动。他耳语说:我背你。她“嗯”了一声,翻身又爬到了他的背上,正如两人第一次身体接触一样。在这一年时间里,两人每次约会,都会重复这样的游戏。他驮着她,像一匹马一样向山梁那片松树林奔去。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力气,左腾右挪,身体腾云驾雾一样。很快来到了那片松树林,微风吹过,树枝摇摆,风穿过松针又发出奇怪的轰鸣。地上落下的松针,干燥洁净松软,他突然把她压到身下,这次约会,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让春草成为自己的人。她在他的身下娇喘咻咻,面红耳赤。他伸出前肢去解她的粗布衣服,她一惊,双手本能地护在胸口,他俯下身,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耳旁,一遍遍地说:春草,我要你,我要你,我受不了了……啊啊……他笨拙地去脱她的衣服,最初的惊恐过去之后,她在配合着他,让他把自己的衣襟解开,又褪去裤子。当两人赤着身体相拥在一起时,他们感受到了林间阴凉的风,浓郁的松树气味,刚才在来时路上,两人身上出的汗,立马就干爽了。两人相拥在一起,放纵地在松针上滚动着,松针在他们的身下听话又顺从。她的尖叫惊飞了林间一群歇息的鸟。他们的呼吸和松树林的嗡鸣融合在了一起,后来他们就被松树的香气融为一体了。
他们仰躺在松针上,像铺了厚厚被子的床,松软舒适,他们看到了头顶上的树冠,树冠空隙处露出的蓝天,他伸出上肢,狠狠地又把春草搂在胸前,两人耳鬓厮磨。他微喘着说:春草,你是我的人了。春草似乎要睡着了,梦呓般地应和着:夜生,我是你的人了。她的手在他健硕的胸前游走着,游到他的嘴边,他突然含住她的手指,用力地吸吮着。她的身子又一次酸麻起来,化成了一摊水,软着浸着,天地在摇晃。
当傍晚来临时,日头向西隐去,松树林的涛声大了起来,他们汗湿的身体被风一次又一次吹干。暮色终于四合了,他们开始穿衣服,当一切停当,相互打量着,确认和来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了。他说:咱们回吧。她又“嗯”了一声,目光望着他就多了种眷恋和不舍。
他说:我回去就和我爹说,让他去你们家提亲。
她点点头,咬了一下嘴唇,又一次扑在他的胸前,湿湿地把他罩住,两人又温存了片刻,他终于放开她。她说:那我先走。他说:好。她在他的视线里轻快地爬出树林。她爬行的样子优美无比,高高翘起的臀,修长的双腿,两只手臂因为从出生就爬行,此时饱满而又结实。她隐去的样子,似在跳舞,轻盈、协调,像头小鹿,俏皮又灵性。
待她的身影消失在林间,他才从松树林爬出去。得到满足的身体有些懈怠,却无比畅快幸福,曾经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他爬在山梁上,望着山下各家各户屋顶上升起的炊烟,一种巨大的幸福在他身体里绽开了。他心想:最美不过人间。这么想过了,他向前爬去,四肢灵活,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像匹马,健康、壮硕、协调有力,他对自己年轻的身体充满了自信。他心里多了事,盘算着如何向父亲开口,让父亲去春草家提亲。爬行的速度就慢下来,心事重重的样子。
二
夜生是在夜晚的时候出生的,于是就有了夜生的名字。从有记忆开始,他就是爬着走路的,村子里除了木家的人,所有人都是爬着走路的,他从小到大没觉得爬有什么不好,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所有人都爬着走路,在夜生的印象里,爬着走路是天经地义的事。爬行村四周都是山岭,除了山岭他们没见过别的,山外的世界他们没看过,没见过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于是,爬行村的人一律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一种会说话的爬行物种。当然,爬行村外面的虎豹豺狼还是有的,它们也在用四肢行走,和爬行村的人类所不同的是,动物们是不穿衣服的,一身皮毛就是它们的装扮了。他们这些爬行人类是穿衣服的,他们能把棉花纺织成粗布,用树叶把粗布染了,粗布裁剪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不仅遮羞,还御寒凉。一年四季温度不同,衣服薄厚也不同。这就是爬行村人和动物们的不同。
夜生与好朋友雷声年龄相仿,两家住得很近,只隔着一条小河沟。两人从小就对眼,还是顽童时,两人就隔着一条水沟一起哭,又一起笑,他们学说话时,河沟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地咿呀学语。再大一些,他们觉得隔河相望的确是劳神费力,他们要走到一起玩耍。不知是谁先发起了过河的动作,两人一边爬,一边冲对方笑着,同时爬到了河边,水沟不宽,几米的样子,但很湍急,哗哗啦啦的流水声把两人的笑声淹没了。两人隔河建立起来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此时的信念就是爬过水沟来相见。他们没有料到,水太急,他们又小,两人相向着爬到水里就被水冲走了。他们的手已经握在了一起,那天有许多爬行村的村民看到夜生和雷声手牵着手,在湍急的河沟里翻滚,他们本能地把头探出水面,浪花声还没有淹没两个人欢快的笑声。他们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水流再转过一个山弯,就是一个深潭,如果两个人被冲到潭水里,将必死无疑。
那个深潭被村民称为死鬼潭,每年都会淹死几个孩童和大人。盛夏的时候,村民都会去潭水里游泳洗澡,这是全村唯一洗澡的天然好地方。人们遵守着一条规矩:男人当日洗,女人就次日。盛夏的傍晚,在山弯处的水面上,都会传来一浪又一浪的欢笑声,有时是男人发出的,有时也会是女人。他们在水里寻找到了快乐,但仍有人游到潭水中央,游着游着,有的就会沉下去,在水里挣扎一番,冒出几个气泡,人就不见了。人们就相传,这是水鬼在给自己找替身,找到替身的水鬼,自己就转世托生了。虽然每年都会有人淹死在深潭里,但这仍然阻止不了人们避夏消暑的热情,每到傍晚,全村人大呼小叫着,拖家带口地来到潭水边,洗澡纳凉。人们都很谨慎,只在水边嬉闹一番,很少有往水里游的人。村里有几个水性好的年轻人,试着游到潭中心,一个猛子扎下去,想探明这潭到底有多深,不论他们怎么努力,终是不能触碰到潭底,然后他们只好悻悻而归,坐到岸上,冲着潭水发怔。
当夜生和雷声在水沟里翻滚嬉笑时,雷声的父亲应声爬了过来,四肢着地,像马或狗一样狂奔过来,腾空一跃,一手抓住一个孩子,甩在岸边的草地上,仍心有余悸的样子。两个孩子并不知道危险,他们觉得刚才的一切很好玩,也很刺激,他们躺在草地上,舞弄着四肢,咯咯地笑着,扭着脸望着对方,他们牢牢记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生死友情。
后来,他们又大了一些,隔在两家人中间的水沟已经成为不了两人友情的障碍了,他们四肢着地,只轻轻一跃就到了对岸,或者他们故意把身子弄湿,就爬行过去。水还是那么湍急,他们四肢健硕,孔武有力,这点儿水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在夜生和雷声八九岁的时候,两人相约着上山割猪草,他们从懂事开始便参与劳动,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在劳动中认识了自然,大自然也成了他们最好的老师。割完猪草后,两人就坐在林边歇息,雷声突然看到一片桑葚林,桑葚正结满枝头。他们从小就喜欢吃这样的果子,桑葚从青转黑,饱满又沉甸甸地坠在枝头上。雷声拉了一下夜生的衣襟,夜生也看到了,两人欢呼着飞快地爬过去,当他们抬起头伸起前肢去够枝头的桑葚果时,却够不到,枝头下的果实早就被人采过了。但眼前让人垂涎欲滴的果实,他们又岂能轻易放过。
雷声和夜生踮起脚,抬起上身,攀着枝杈竟站立了起来,他们那天采了很多果子,吃得嘴唇都乌紫了,肚子鼓胀起来。当他们离开树下,雷声惊奇地叫了起来:夜生,你看我。夜生看见雷声站立起来,高大而又威严的样子,夜生学着雷声的样子,也站立起来,世界在他们眼里一下子就变了样子,以前他们认为高大的树木矮了一截,地上的花草也变小了,他们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雷声还用力跳了起来,伸手去抓头顶上的空气,雷声咧着嘴说:夜生,我都摸到云彩了。两人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感到新奇,他们鼻子下的空气似乎也和往日不一样了。
雷声用手拍着脑袋,冲夜生眨着眼睛说:我不是在做梦吧?
夜生把雷声的手抓过来,找到他一只手指咬了一口,雷声叫了一声道:你咬疼我了。夜生吐了口水说:那咱们就不是在做梦,梦里不知道疼。两人拥抱在一起,他们躺在地上打滚儿,他们的身体压倒了一片蒿草。两人躺在草地上,隔着林隙望着蓝天,抑制不住兴奋。
夜生说:雷声,咱们可以站起来的。
雷声说:站起来眼前就不一样了。
他们又想到了父母和其他亲人,他们突然疑惑了,他们能站起来,亲人和村民都能站起来,但为什么不站起来呢?站起来世界大了,还能采摘他们以前不曾采摘到的野果,把上肢解放出来,他们还能干许多事。两个少年在草地上困惑着。
后来,他们爬起来,又试着站了起来,果然他们再一次成功了,发现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他们那天就直立行走着走出树林,越过山岭,把割到的猪草背在背上,一路向村里走去,当他们看到村民时,就大声地喊:我们能站起来了。我们站起来能采到许多果子,还能摸到天……他们一路喊叫着,双脚生风地向村子里跑去。
看到他们的村民,伸长脖子,像看到两只怪物,眼里流露出惊讶惶恐的神情。两个少年不在意村民的眼神,他们向家里狂奔而去,要把这一发现告诉亲人,他们要让亲人站起来。当夜生闯进自家院子时,母亲正蹲在墙根补衣服,见到夜生的样子,竹针刺破了她的手指,接着她惊叫一声:快趴下。夜生来到母亲身边,不由分说,拉过母亲的手,又蹦又跳地说:娘,你也能站起来,和我一样。夜生没料到,遭到了母亲一掌,这一掌打在夜生的脸上,他的脸火辣辣地疼着。夜生猝不及防,捂着脸,吃惊又委屈地望着母亲。
母亲呵斥道:趴下,你这不听话的孩子。
夜生从没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脾气,不解但还是趴了下来,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父亲回来后,夜生看见母亲和父亲嘀咕着什么,母亲的话还没说完,父亲的目光就转了过来,寻找到角落里的他,然后怒不可遏地四肢着地奔过来,狠狠地扯过他,提起一根木棍朝他打来。有几下打在他的脸上,也有几下打在他的腿上,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他的叫声还没有消失,他听见河沟对面的雷声也发出同样的号叫。
那一次,夜生在屋里躺了足足有一个月,不仅腰疼、腿疼,心也疼。他知道自己的腰断了,腿也断了。他在屋里曾大声喊过雷声,河对岸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雷声挨的打不会比自己挨的轻,也许被他爹打死了。他爹是个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还顺带着把他娘也打了。
一个多月后,夜生终于能爬行了,他艰难地爬出门去,爬到河边,他一声又一声地叫着雷声。雷声家的门开了,爬出雷声,两人隔河相望。他们从对方的脸上都发现对方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节选自2023年第1期《芙蓉》中篇小说《爬行村》)

石钟山,作家,编剧。迄今创作长篇小说《大院子女》《春风十里》《五湖四海》《向爱而生》共计36部,中短篇小说300余部篇。计1500万字。根据本人小说改编及原创的电视剧30余部,1500余集。其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飞天奖三次、百花文学奖三次。
来源:《芙蓉》
作者:石钟山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