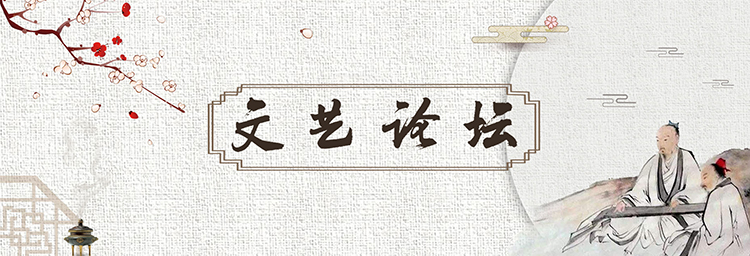

嘉绒语与阿来创作关系初探
文/李昌懋
摘 要:阿来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越来越多地提及自己的母语是区别于标准藏语的嘉绒语;并在其作品,尤其是《云中记》的空间描写中,成功地、潜移默化地将嘉绒语的空间与方位感知模式带入汉语之中,使得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会采纳其上游—下游的空间轴线,来理解文本发生的场域,这正是阿来嘉绒认同的无意识流露的结果。
关键词:阿来;嘉绒语;《机村史诗》;《云中记》;方位词
一、嘉绒语的基本情况
阿来出身并成长于嘉绒人之中。对于阿来的创作与嘉绒地区、族群之间的关系,已有相对充分的研究;但对阿来的作品中,对嘉绒语的描写,以及他在以汉语书写嘉绒人生活这一“跨语际实践”中,其作品中体现的嘉绒语影响,则尚大有深化讨论的空间。
嘉绒人操一组关系密切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其系属在上个世纪的研究中曾有藏语方言、藏语支语言与羌语支语言等多说{1},而根据最新的研究,嘉绒语群被认为是藏缅语族中与藏、羌并列的独立语支,且与彝缅语的关系比藏语更近{2},其最为密切的亲属语言是已经消失的西夏语{3}。嘉绒语确实保有许多古藏语词汇,但学界如今一般认为这些词汇是嘉绒语从古藏语中借入的,而非二者的同源词。要说明的是,藏语的三大方言间也存在互通困难的问题,而嘉绒语群内也包括了几门并不能互通的语言{4},但藏语与嘉绒语的区别之大仍远不是两组语言内部各语言之区别所能比的;更重要的是,就社会语言学而论,两者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共通语,藏语使用者多承认卫藏话为标准语,而在嘉绒地区,四土话则曾经处于交际语地位,“虽各家庭语言在大家庭中互不相通,但各土司各寨子之间又仍能互通往来,有共同用语,这种通用的外交语即称嘉绒官话,这种现象就是如今,也照样保持着未能改变”{5},这种语言也正是阿来的母语{6}。另外,“解放初中央民族学院还专设了嘉绒族研究班,创制了嘉绒民族拼音文字,将其该地民间故事,用该文字拼音写记,在马尔康理县金川一带嘉绒人中去念读,反映很好,比藏文译音准确易懂”。{7}
嘉绒语和藏语的差距过大,造成嘉绒人在学习藏语时往往有困难,五十年代初的情况是:“嘉绒区小学生学习藏文困难,除教员(喇嘛)的教法不当外,主要因当地口语与藏文相差太大,还因儿童还要学汉文(儿童父母思想上认为上学学汉文将来有用,而学藏文只是念经用,可以到喇嘛寺去学)。因此,人们认为在生活上,学藏文是‘白白拉拉’(‘无用’的意思),大金河东屯民族小学竟拒绝喇嘛教藏文。”{8}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当时嘉绒地区的中小学中推广藏语文教学的失败,因而到阿来上学的年纪,本地学校就都已改用汉语文教学了。阿来在多篇散文、演讲中所感叹的,自己从上学起就只能“在汉语中流浪”,不能掌握藏语文,因此要使用汉语文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其母语既缺乏书面语,而又与其被认定的民族身份藏族的“通用语”差距过大的特点{9}。
二、阿来对自身母语的称谓与描绘之转变
阿来本人在2008年前曾长期将自己的母语称作“藏语”,但他从九十年代起,就在各种文本中提及,自己的“藏语方言”是无法与其他的藏语互通的。在《尘埃落定》中,阿来表述并试图解释本地语言与藏语的区隔:“远征到这里的贵族们,几乎都忘记了西藏是我们的故乡。不仅如此,我们还渐渐忘记了故乡的语言。我们现在操的都是被我们征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当然,里面不排除有一些我们原来的语言的影子,但也只是十分稀薄的影子了。”{10}即少数来自藏区核心区的征服者被多数被征服者同化。这种描写试图缓解当地人本土身份与藏族认同间的张力,却也微妙地声明了书中的“黑头藏民”即土司们以外的一般百姓与其他藏族的区隔,此外还依然赋予藏族身份以由崇高的土司地位所象征的上位性。
新世纪以来,类似的描写更多,例如,在《达瑟与达戈》中,有一个场景引起过许多学者的注意:色嫫向达戈表达自己想成为歌唱家的理想,认为达戈打猎对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帮助。阿来特意指明,“歌唱家”这个词色嫫是用汉语说的。{11}不止一两位学者指出,阿来强调这个细节是在用汉语词汇侵入机村语言的现象象征现代性对机村社会的侵入。但阿来在同一个场景里,也强调了“远方的藏语”即语言学上的“藏语”,同样是随“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被输入机村这样的嘉绒地区的:“她说这话时,脸上泛出了更明亮的光彩,并且立即就唱了起来:‘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西若若,照啊到了雪山上,依啦强巴若若!’这歌中的藏语也是远方的藏语,而不是机村的当地方言。”{12} 达戈对此的反应是:“捧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求求你,停下来,不要唱了。’”而色嫫的回应却是:“两眼放着晶晶的亮光问:‘我唱得比收音机好听吧?’”“收音机”是现代化与革命话语的传播者,而汉语和“远方的藏语”都正是借助收音机里的特定现代性方案才得以影响机村的现实。机村本土人群在这里的“藏族身份”,其实是与“中国身份”处于同心圆结构中,一起有待于通过“收音机”等现代性事象来习得。
在2000年代后半段,阿来经常被一部分藏族知识分子及藏族网民批评,其部分原因在于,阿来一再表达对藏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的支持,并认为自己未曾受惠于藏族的书面文学传统{13}。出于在母语问题上曾受到的诘难,兼有不愿再被指认为具有“藏族代言人”身份的考虑,阿来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母语并非标准藏语,生活经验也不能代表整个藏区,而不再像初成名后到当时为止那样,会在演讲访谈中直接提及自己与“藏语”“藏族”的关系;在2008年完成了更早时即决定参与的“重写神话”系列中的、描写康区的《格萨尔王》后,更是如此。兹寥举数例:
“我所在的藏语的嘉绒方言区,并不是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流传地。格萨尔史诗流行最广泛的地区,也是这个故事的原发地区,那是另一个方言区了。所以,在这些地区搜集或体验这些故事和这些故事的演唱时,我也依然需要翻译。”{14}
“ 藏语的康巴方言和我家乡的嘉绒方言大不相同,我只能大着舌头吐出一些简单的词。”{15}
“我所讲的这种嘉绒语,今天被视为一种藏语方言,而很多远方的人群却讲着另外的语言,近一些是藏语里各种方言,远一些是不同的汉语……”{16}
“我在藏区长大也有藏人的血统,我最初讲的不是汉语,也不是真正的藏语,而是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在那种语言当中有很多原初性的和印第安神话,民间故事相似的民间故事资源,神神鬼鬼的东西很多,但其实又是直指人性的 。”{17}
在《云中记》中,阿来也两次提到“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语”。{18}
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来开始更多地点明自己母语的名称,而不再泛称其为“藏语”,或特称其为某种“藏语方言”。
三、阿来作品中的嘉绒语方位系统影响
阿来不仅越来越明确地指出自己的母语,还逐渐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示出受到嘉绒语和嘉绒文化持续影响的空间感知系统。向柏霖指出,“在嘉绒语的所有方言中有一些特殊的‘方位词’。这些方位词一般是当状语使用的,但是也可以修饰其他名词、当主语或宾词,而且后面可以放方位格标记,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分析成名词,并称之为‘趋向名词’。这些趋向名词和动词的趋向范畴的前缀有直接的关系”{19}。他列举了三组这样的趋向名词,分别以汉语对译为 “上—下”“上游—下游”“东—西”。2020年,Zhang Shuya对多种核心嘉绒语中上述“动词的趋向范畴的前缀”之语义进行了抽象化分析,并最终认为原始四土话起初有三个方位参考系:上—下(to - na)、斜上—斜下(ro - r?坠),东—西,或上游—下游(kV - n?坠){20}。其中,其活跃程度最高的一个参考系是“kV - n?坠”即“上游—下游”,这一范畴还可以表示“东—西”,也可抽象为“向心—离心”,以及“里—外”。这说明,对于嘉绒人来说,其空间感知是以其生存境内的主要地貌即河谷为依据的,与多数藏族以“上—下”为核心的方位体系相区别{21}。相对于藏族传统上宏大的“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多康六岗”的族群空间认知,嘉绒地区的“我族”空间认知基本上锁定了草地以南,康区以东,羌族聚居区以西和成都平原西北之内的几条平行的河谷,这种认知与其语言中的方位参考系互相影响,深深烙在本地人的潜意识中,使得他们在使用其他语言言说时也会流露此种空间认知的痕迹,例如,王田在对杂谷脑河流域的研究中,就发现当地族群(以几种嘉绒语的使用者为主)在使用汉语时,会自称居地“西路”“西沟”“西道”等,并且会根据河谷走向使用“上半截、下半截”来区分沟内居民。{22}
阿来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常常以河谷作为展开情节的场景,并反复使用“上游—下游”来定位其文本中的空间方位与人物的动作与行动。此外,在现代条件下,沿河行进的(普通)公路也可以视为河流的变形与象征,阿来如是说:“一川河水,如影随形跟着公路,始终应和在窗边。”{23}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曾批评“中国人不太具有空间感”{24}“不懂得分区”“不该拒绝河流带来的公共空间”{25},在该书中,作为大渡河支流梭磨河流域的儿子,他将“走通大渡河”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我知道,正是这条大河所来的方向,这条蜿蜒的情感红线,正是这条大河的千折百回。”“顺着大河溯流而上,我就可以循着一条人们不常走的线路回家”{26}。接下来他也坚持按照河谷的流向行走:小金川、梭磨河、并且在表述自己的行进方向时交替使用“东西南北”与“沿某流域”,而以后者为主{27}。甚至嘉绒地区的神山嘉木莫尔多,他也使用河流的走向来定位:“就在大小金川及其众多支流逐渐汇聚的这一地区的丛山之中。”{28}不过,他在有些段落,依然纠结于自己的行走是“上升”还是“下降”,对于“上—下”这对方向表现得比较敏感,如第五章第4节“上升还是下降”,试图将公路翻越山脊沟通两个不同流域的路段的升降赋予某种哲学意味,从上文我们指出的其他藏族与嘉绒人不同的方位体系中,我们不难识别出,阿来的这种方位纠结折射出的依然是其认同的纠结。
在《机村史诗》系列中,阿来同样展示出类似的空间与方位感知。《随风飘散》的结尾处,提及在修好的公路上装运木头。《天火》中,多吉被捕后脱逃,是押解过程中,在去乡里的公路上跳车后跳河。《荒芜》中,泥石流的灾害对村落的影响之大也与河谷的地形与河谷农业的生计样态密不可分。《轻雷》中,这种方位书写更深可玩味,故事的主要舞台双江口镇上的木材检查站就因两条河谷、两条公路的交汇点出现与得名:“检查站修在两条公路交会处……一大一小两条河流在訇然奔流中撞在一起,在镇子下边陡峭的崖岸下腾起一片迷蒙的雾气和沉雷般的声响。只有几年短暂历史的镇子因了这两条河两条路的交会而有了一个名字:双江口。”{29}然而,尽管相同的汉语名字在经济开发后的近年来反复出现于这片以河谷为主要地形的土地上,可每个“双江口”却都有不同的本土嘉绒名字,比如这一个就可意译为“轻雷”,得名于汇流的河水的响声。可见,在嘉绒地区的本土视域中,所有河流的汇合处都有不可替代的特殊空间节点性质,而在经济开发视域中,它们却仅具备同类的交通节点特征。在《轻雷》所书写的时空中,此地的嘉绒名字如今只能由主人公“喃喃自语”时说出,通用的名字只能是由经济开发实践规定的“双江口”。
这两种空间视野暂时仅仅是使用不同的能指,其所指依然重合,即公路必须依赖河谷的走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如果地理只是一张纸,那么,打开这张纸,从这些出产木材的群山,从这个自治州的腹地,或者说青藏高原东北部通向四川盆地的地方划一条直线,那么,这条公路并不需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从机村开始,打一条隧道,长五到八公里,那条高等级公路穿过觉尔郎风景旅游区(规划中的),这样,汽车可以在危险的盘山路上少跑近百公里路。”{30}于是,事就这样成了。这就是把地理感知为生活空间的本土视角,与把地理感知为“一张纸”的开发视角的根本区别。后者起初可能看似未曾改变本土空间的物理—地理形态,只是在其上堆叠了两种空间观念,而一旦开发视角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得到贯彻,这种地理形态的改变也将是迟早的事。嘉绒地区以河流走向为核心的空间感知体系,也将随这种开发的推进,被以“东南西北”方位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化”—“全球化”空间感知体系所取代。
在《河上柏影》中,阿来在题目中即点明,其书写对象的生境是河谷。具体而言,是大渡河、岷江、嘉陵江“这三条大水边上的任何一个村落” ——“如果不太拘泥于细节,而从命运轨迹这样的大处着眼,这个村子和坐落在这三条大水边的那些村子真的几乎一模一样”{31}。而这种空间格局又被书中主人公亲眼见证的漂流场景所强化。而在《蘑菇圈》中,阿来同样使用“三条大水上游河谷”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书写与认同的对象: “不止机村,不止是机村周围那些村庄,还有机村周围那些村庄周围的村庄,在某一时刻,都会出现这样一次庄重的停顿。这些村庄星散在邛崃山脉、岷山山脉和横断山脉,这些村庄遍布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那些高海拔的河谷。”{32}河流的走向再次成为读者感知其文学空间结构的主要依据。
在《云中记》中,阿来更进一步地揭示出,河谷作为当地居民最小族群认同单位的事实:同一条河谷(即当今行政区划下的瓦约乡)中的村庄,尽管如今有着宗教的差异,但共享着“规矩”,包括祭祀山神阿吾塔毗(或按佛教习惯称为金刚手菩萨之化身)(166页)、路遇的两人互相“告诉”即交代近况(25页)、每个村落都有家庭内传承的“祭师”(210页)等。不按这些规矩做事的人,会被嘲讽:“您不是瓦约乡人?怎么像个外乡人一样不懂规矩?”{33}而如文本中余博士所说,这一“文化单元”又附生于峡谷的“地质单元”之上(304页)。阿来不厌其烦地反复铺陈了该河谷内的人群渊源与地理空间格局:“云中村也是祖师托梦给阿吾塔毗让他在这里率领族人扎下根的地方。森林地带土地肥沃,气候温润,云中村很快人丁兴旺。有很多族人进入更深的河谷,变成了瓦约乡的七个村庄。”(166页) “断崖一垂而下,直接到了岷江边上,而在对岸,则是一片平畴沃野,村庄与田野相间分布,那就是和云中村同属瓦约乡的几个存在,江边村最靠近江流。而山前村最靠近山脚……根据流传了上千年的古歌和传说,山下几个村子的人和云中村人是同一个祖先。”(232页)“根据传说,瓦约乡的几个村子,都是从云中村派生出来……阿吾塔毗带领部落在森林中开辟耕地和牧场,建起了云中村,人丁兴旺后,就有一些人慢慢向山下河谷迁移。”(258~259页)“云中村坐落在一个突向峡谷,逼着江水转了一个大弯的山鼻子上……这大象鼻子已经折断不止一次了。每一次折断都造成一个滑坡体。滑坡体就是因为奋力前拱而破碎的象鼻子,一次又一次,滑坡体坠入江中,江水慢慢把这些泥沙荡平。这就是对岸那些平整土地的来源。”(304页)
需要说明的是,阿来在描述河谷内村落间的方位关系时,使用了“山上”“山下”,但稍加思考,不难发现,他使用的这对概念并非汉语母语者一般所理解的同一山体之“上”“下”,因云中村与其他村落分处河流两岸,并不处于同一山体;他也偶尔用“东”“西”,但面对“转了一个大弯”的河流,此处的“东—西”方向显然也不可能垂直于河谷。依据基本的地理学知识,河流弯曲部内侧的“山鼻子”,滑入江中后由江水冲击成的河谷平地,不可能位于该“山鼻子”的正对岸,而是随河水流向其水流下游方向的斜对岸。也就是说,云中村与河谷中其他村落的方位关系,除了分处河流两岸、以及不同的等高线上之外,也应该是分处于河谷中的上游—下游,这在文本中的证据是,阿来使用过一次“更深”来表述村落之间的方位(166页)。由此可知,当阿来使用“更深”之外的其他汉语方位词如“山上、山下”来描述瓦约乡村落间的方位关系时,他所希望读者明了与理解的,也很可能正是这种可勉强译为“上游—下游”、相对难以用汉语准确表述的嘉绒语中的空间方位关系。在这个语境下,阿来对村落间空间关系调动不同方位词的反复描述,可能正是他试图把母语嘉绒语中的类似空间感知体验译介进汉语的尝试,是其嘉绒认同的无意识表达。再结合这些村落在文化上之同、宗教上之异、与人群关系上之分居源与流,所显然象征着的阿来对某种本真性嘉绒身份的自觉想象(信奉苯教的云中村在民间传说中是河谷中最古老的村落,其他村落居民均是由云中迁出之裔),我们可以说,在《云中记》中,阿来在有意识与无意识层面都有着为表达嘉绒认同而写作的动机。
刘伟指出,非母语写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是将母语中的文化事象与思维特点译介入写作用语中{34}。阿来本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令汉语成为“多元共建”空间;他进一步指出:“中文这个称谓,我想意味着这是多民族国家的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国家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把这种语言描述为一种单向的规划——汉化。一种民族主义将此当成文化的胜利,另一种民族主义自然将此当成一种文化的失败,而真正的语言现实是当一种语言成为国家语言,有许多其他语言族群的人们加入进来,使用这种语言,利用这种语言进行种种不同的功能的书写时,其他族群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和捕捉了这些感知呈现了这些思维方式的表达,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这种非母语的语言。”{35}在《云中记》的写作中,阿来自承:“我从我叫作嘉绒语的第一母语中把那种泛神泛灵的观念——不对,说观念是不准确的,应该是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中文中来……我还是把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使我能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因为执着于现实的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嘉绒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命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何将这样生动的感知转移到中文里来,也是我面临的一个考验。”{36}阿来通过了这种考验,他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尤其是《云中记》中,成功地、潜移默化地将嘉绒语的空间与方位感知模式带入汉语之中,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会采纳其“上游—下游”的空间轴线,来理解文本发生的场域,这正是阿来嘉绒认同的无意识流露的结果{37}。
注释:
{1}摘自向柏霖:《嘉绒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页:“一部分学者认为嘉绒语是藏语方言(王建民、赞拉·阿旺错成:《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另一部分认为嘉绒语时藏语支的语言(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嘉绒语是羌语支的语言(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
②Sagart, Laurent, Guillaume Jacques, Yunfan Lai, Robin Ryder, Valentin Thouzeau, Simon J. Greenhill, Johann- Mattis List: Dated Language Phylogenies Shed Light on the Ancestry of Sino-Tibet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9.116(21),pp. 1-6.
③Lai, Yunfan, Gong, Xun, Gates, Jesse P. and Jacques, Guillaume:Tangut as a West Gyalrongic language,Folia Linguistica Historica, vol. 54, no. s41, 2020, pp. 171-203.
④语言学界一般把嘉绒语划分为核心嘉绒语组和西部嘉绒语组两大类,前者包括分布最广的四土话以及茶堡话、草登话、日部话等;后者包括绰斯甲语(拉坞绒语)、尔龚语(道孚语)等。
⑤⑦雀丹:《嘉绒藏族史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第43页。
⑥阿来出身马尔康县,即过去因由四土司分辖而得名的“四土”。
⑧《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调查者认为:“如果能提高藏文教学质量,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藏文教学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另,可考虑运用藏文字母拼写嘉绒语为日常生活之用。”显然,这一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推行。
⑨在其他藏区,藏语文教育曾经长期在小学中扮演主要角色,即使在“文革”中也未曾中断。又,在阿来较早作品《奥达的马队》(《民族作家》1987年第4期)中叙述者说:“信全是用藏文写的,我自然念不出来,山里的藏族汉子上学都是学习汉文。”此处“山里的藏族”当暗指嘉绒藏族,这里所留白的,是“草地上的藏族”即安多藏族在当时的基础教育里是学藏文的。
⑩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0页。
{11}{12}阿来:《机村史诗·达瑟与达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第33—34页。
{13}可参见“藏人文化网”的相关讨论:网址http://zxdd.tibetcul.com/45758.html,或参看相关论文, 如姚新勇:《“族裔民族主义”思潮与中国多族群文学的立场选择》,《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4}阿来、夏榆:《天上也是人间,神话也是现实》,摘自夏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4页。
{15}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40页。
{16}阿来:《一个中国作家的开放与自信——就从翻译谈起》,《人民日报》2016年9月9日。
{17}阿来:《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选自《如何面对一片荒原——阿来读书札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38页。本文基于阿来在2017年的讲演。
{18}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选自阿来:《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19}向柏霖:《嘉绒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与嘉绒语比邻分布、生境相近、语言系属也比较接近的羌语中,丹珍草在分析阿来的文学语言时曾指出,“羌语绝大多数动词都附加有趋向前缀或可附加有转换功能的趋向前缀,这反映了羌族的方向感念很强,非常重视动作方向的分类……羌语方位词分得很细”(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20}Zhang, Shuya: Le rgyalrong situ de Brag-bar et sa contribution à la typologie de l'expression des relations spatiales : l'orientation et le mouvement associé.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2020.笔者得知该论文存在,并初步了解该论文内容,系根据知乎用户“小云哥哥”在知乎专栏中的文章《Zhang (2020):四土嘉绒语白湾方言的趋向系统——全新的视角和方法》,https://zhuanlan.zhihu.com/p/278574898,发布于2020年11月8日,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2月26日。
{21}关于藏族空间观中“上—下”参考系的核心地位,参看王蓓:《格萨尔王传与多康地区藏族族群认同》,第四章第二节《“上”“下”之间:基本自我定位的确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博士论文。在藏族传统空间认知的宏大尺度下,由于青藏高原西高东低的地势,起源于“高—低”的“上—下”也具有描述“东—西”的可能,这里要说明的是,起源于“高—低”的且可与藏语“上—下”类比的“上—下”在嘉绒语体系中不可与同样可以描述“东—西”的“上游—下游”混淆。“上游—下游”的具体方向是沿着河谷走向而变化的,并不用来描述高度的升降,上—下则表述垂直于两岸山峰的方向,而“斜上—斜下”最为复杂,但最常用的指向是描述人在山路上运动的趋势,即朝向山脊切向山脊线,还是背对山脊远离山脊线,在一些嘉绒方言中,“斜上—斜下”可能与“上—下”混淆,但这两者是不会和“上游—下游”混淆的。(参看上注Zhang,2020;“小云哥哥”,2020)
{22}王田:《从内陆边疆到民族地方》,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4—65页。
{23}{24}{25}{26}阿来:《大地的阶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8页、第27页、第157页、第26页、第68页。
{27}{30}阿来:《大地的阶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大渡河:第30、38—39页;小金川:第78、82、127页;梭磨河,第154—155页;大金川:第188—189页。
{28}阿来:《大地的阶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29}阿来:《机村史诗·轻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第91—92页。
{31}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32}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3}阿来:《云中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211页。
{34}刘伟:《非母语写作与文化翻译》,《民族文学》2011年第1期。
{35}阿来:《我是谁,我们是谁?——在东南亚和南亚作家昆明会议上的演讲》,选自《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125页。
{36}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选自《以文记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
{37}有论者认为,与扎西达娃相比,阿来在作品中,往往出现“时间意识”压倒“空间意识”的情况,因而不能表现出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空间中储存的“藏族民族性”,而这种特点又与阿来的嘉绒身份有关,因为嘉绒“汉化颇重”(丁增武:《“消解”与“建构”之间的二律背反——重评全球化语境中阿来与扎西达娃的“西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这种观点的问题之一是,嘉绒地区自有其独特的传统“空间意识”,不能与其他藏族地区的空间意识互相替代;而正如笔者本文所论证,阿来的写作恰恰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嘉绒人的空间意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李昌懋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