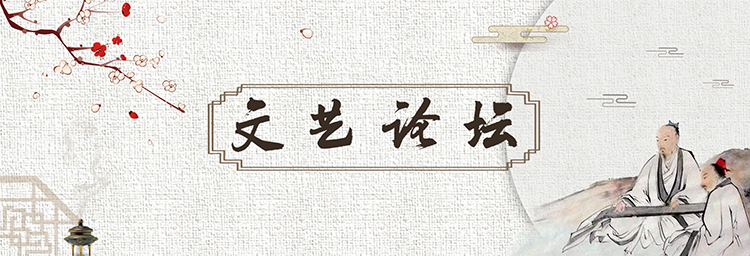

阿来康区与嘉绒历史书写之比较
文/李昌懋
摘 要:在《尘埃落定》的创作之后,阿来的历史书写在总体上表现出重视客观性的特点,而在以康巴地区为题材的历史书写与以嘉绒地区为题材的历史书写中,又流露出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彻底地贯彻了对历史的求真态度与实证主义倾向,而后者则对历史的“传奇”化与“神秘”化有所妥协。这种区别,是由阿来对康巴地区和嘉绒地区之间的不同情感态度所造就的。
关键词:阿来;《格萨尔王》;《瞻对》;《机村史诗》;历史书写
对于自己在世纪之交的创作,阿来说:“2000年,再一次漫游故乡大地,写作并出版长篇游记《大地的阶梯》,再次梳理地方历史,再次寻求自己与植根其中的大地与族群的关系。正是这样的思考让写作再次停顿,并一停数年。”{1}阿来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在2002年曾出版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而《空山》第三部《达瑟与达戈》的写作也在2003年就开始了{2};但这恰恰让他自己的以上表述显得更为意味深长;因为这说明阿来非常看重他“再次寻求”后更新过的“自己与植根其中的大地与族群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对自己这一时期内在身份认同上的微妙变化是自觉且笃定的,上引夫子自道中提到的虚拟的“休息”,所标识的正是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消化这种新身份所需要的时间;而阿来族群认同的此种微妙变化,又是与他在本次“漫游故乡大地”后所见所闻所写之中,对当下嘉绒藏区所代表的边缘地区现实问题的认知与警惕密切相关的。在这里,阿来认同空间的调整,即从整个“藏区”到嘉绒一地,以及他问题意识的转化,即从民族历史“寻根”向地方当下“问难”,被转化为他设想中写作时间上“应该”要有的空白。
阿来所设想的这一虚假的“创作空白”,实际上表征的恰恰是他的“创作转型”。从这一“空白”之后,阿来的书写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变更。在嘉绒乡土题材的书写中,阿来由以历史书写为主转向以现实书写为主,而历史题材则在他书写康区时才更多出现,并且即使是在书写康区历史的《瞻对》等文本中,阿来也强调,“我不是在写历史,我是在写现实”。{3}在族群身份表达中,阿来越来越淡化自己的“藏族”身份,而倾向于强调,自己在写的是更具普遍性的“中国的农耕的村庄”。{4}从阿来2000年以来的中长篇作品中,以康区为题材者与以嘉绒为题材者中历史意识的不同里,我们也能识别出他对嘉绒地方区别于以康区为代表的其他藏区的情感态度。
阿来在《尘埃落定》时期之后书写藏区的叙事性作品按其叙述地域,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即书写以康区为主的其他藏区的文本:《格萨尔王》《瞻对》《三只虫草》,以及书写嘉绒地区的文本:《遥远的温泉》、《机村史诗》系列、《蘑菇圈》《河上柏影》《云中记》。其中,对于《格萨尔王》,应稍作辨析。根据王蓓的研究,嘉绒藏区并非史诗《格萨尔》的核心流传区{5},阿来本人也在访谈中说:“我所在的藏语的嘉绒方言区,并不是格萨尔史诗的主要流传地。格萨尔史诗流行最广泛的地区,也是这个故事的原发地区,那是另一个方言区了。”{6}在嘉绒地区,流传最广的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阿尼格东,在一些传说版本里,他是格萨尔的化身,但也有说他就是《格萨尔》中反面人物、格萨尔的叔叔晁通的{7}——这其中反映的“历史心性”深可玩味。更常见的说法是,阿尼格东出身嘉绒农家,李菲说,与作为“战神”降世的格萨尔王相比,“阿尼格冬的身影背后似乎隐藏着一张嘉绒农人的面孔”。{8}她还指出,“‘阿尼’指涉英雄祖先的族源记忆。在藏边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阿尼’信仰现象群……(这一信仰现象群)表达了藏边族群身处文化交融地带追忆族源、凝聚认同的紧张与动力”。这与用格萨尔史诗去定位自身族群身份的大多数多康藏族群体形成了鲜明区别。从以上事实出发可以确认,认为阿来在《格萨尔王》中书写的主要是嘉绒藏区是缺少依据的,也不应以该文本为论据去讨论阿来的“嘉绒”认同与嘉绒书写。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阿来的历史观在其《尘埃落定》以来的大多数文本中倾向理性和实证{9}。在《格萨尔王》与《瞻对》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强调要搞清楚“故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10},而在嘉绒题材的作品中,除了《河上柏影》中清楚地表达出类似的态度外,《云中记》《机村史诗》中,阿来似乎都对民间的历史记忆持有一种更温情的心态,对于口头流传的“故事”,更看重其情感价值,且有意无意地倾向证成其真实性{11}。在《格萨尔》中,主人公、神授仲肯晋美曾多次表达自己想验证格萨尔“故事”的真实性,为此不惜冒犯偶遇的喇嘛{12},甚至冒犯他梦中的、以“神”之形象出现的格萨尔,并承担失去神授演唱能力的风险{13},他向神格萨尔抗辩说:“我的听众他们也想知道,姜王侵犯的盐海到底在哪里,姜国和门国的王城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要是找到这些地方,他们就更相信我的故事了。”{14}而晋美梦中的神格萨尔却说,晋美之所以能够得到神授,正是因为他原先的懵懂无知。为了调和“求真”需要的“知识”与“神授”要求的“懵懂”,晋美不自觉地成为“愤世嫉俗”的“阿古顿巴”式人物,并以这种身份得到了梦中人格萨尔{15}的认同与谅解。当然,晋美这种“求真”又决不能等同于学者们所争论的格萨尔其人其事的真实与否{16},晋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打动听众,“让他们更相信我”,而非学者们的“为求真而求真”,其最终指向还是在听众身上实现的某种精神效果。换言之,晋美的形象其实错位地成了某种看似完全不像启蒙者的启蒙者。他一方面以群众身份进入各处的“人民”,另一方面又是每个停留之地的外来者。
晋美的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阿来的自我印象。阿来曾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说唱人,我不自视高贵。这个世界从来就是权力与物质财富至上,在当今时代这一切更是变本加厉……但我认为可以因此从权力与财富那里夺回一点骄傲。”{17}此种经过隐藏的启蒙与教化的姿态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阿来2000年以来的多数文本之中,任容早曾指出阿来在其作品中写作姿态的变化{18},但任氏认为,这种变化是从“藏族青年知识分子”(“我”)到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者(“仲肯”),笔者则以为,阿来式的“仲肯”与其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不如说是“民族发展的启蒙者”,而且这种姿态更明显地见于他书写康区的文本中。在《瞻对》的文本中,以及和《瞻对》有关的访谈里,阿来更加自觉地揭明,自己的写作就是在总结“康区历史的教训”{19}。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阿来一方面搜集大量资料,并确定本书非虚构的文体:“当年写《格萨尔王》,我到处搜集口传史料,不止是格萨尔,我对其他很多地方感兴趣,后来确定从瞻对切入。清代档案齐全,包括史书、官方材料和口传材料。清代六次用兵瞻对,我从几十本材料中梳理,互相补充,尽量还原历史。当我掌握了那么多材料,我发现用不着虚构,只需要找到思路串联起这些素材就成立了。”{20}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以官方材料而非民间材料为主要框架,来建立起其历史叙事:“主要还是靠官方修的史,封建社会修的史虽然也有假,但至少档案是真的。加上从民间搜罗的文史资料,地方志,口传资料作为补充。官方史料是大轮廓,非常坚实,但它缺少细节,民间的东西就可以补充……同一件事,民间材料站的角度不一样,看法也就不一样。这样两相对照,就能挖出好多有意思的东西。”{21}对于写作《瞻对》的阿来来说,民间材料仅仅提供了一种补全历史细节的“角度”,而不曾设想存在价值与政治取向相异于正史的“人民的历史”或其类似物,这种看法相比写作《格萨尔王》时的阿来,可说是更加保守、也更加“客观”了。两者的共同点,则在于都试图建构一种宏大的、客观的历史图景,以达到某种“教训”之目的。基于这种认识,阿来在《瞻对》中多次否定康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形象的正面意义,如贡布郎加即布鲁曼在瞻对民间记忆中的正面情感态度,就被阿来认为不足为训。而对《格萨尔王》原史诗中的人物形象,虽因体裁与作者本人更正向的情感态度,阿来不可能对其做总体否定,但也都尽量将其“人”化,改写得更加“合理”。笔者以为,阿来书写康区“大”历史的努力,在《格萨尔王》中,因有说唱人晋美的经历串联起来的对当代藏区社会的深描,而取得某种平衡,故可谓成功;但在《瞻对》中,却稍显用力过度。
相比于这种对康区民间传奇的“合理化”改写,阿来在《机村史诗》《云中记》中,却对民间传说的价值表现出更大的认可,且倾向于在科学实证上也能全其“真”。《天火》中,绝大多数机村人对神湖色嫫措及传说中该湖上的一对金野鸭与机村兴衰间的联系深信不疑,据说“金野鸭出现了,把阳光引来,融化了(色嫫措中的,引者注)冰,四山才慢慢温暖滋润,森林生长,鸟兽奔走,人群繁衍”{22}。色嫫措与金野鸭因而与机村的起源传说联系在一起。在《天火》中,炸开色嫫措的决定,不但没有扑灭肆虐的大火,还直接造成了意外的伤亡,首次应验了关于色嫫措存废与机村兴衰间的神秘勾连。更有意味的是,在本系列最后的《空山》的末两章里,村民重修色嫫措时发现了史前建筑的遗迹,考古队因此赶来进行了正规的考古发掘,证实色嫫措岸边确为机村附近最早的居民点。机村民众由此推定,这里正是他们祖先的村庄,而考古学家对此予以默认,最终,在机村人、考古队员与上级领导共同的狂欢式宴会上,领导宣布,因水库蓄水即将消失的机村将搬迁到色嫫措遗址所在地即重建后的色嫫措岸边,回到“祖先的村庄”的位置。{23}阿来在整个系列中大部分都在书写机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相继的两种现代化模式下所经历的创伤,但在最后却赋予了它一个如此美好的场景与结局,不仅体现了修复色嫫措这一情节的情感修复价值,还借考古队员的默认,试图在“科学”上也承认传说的正确性,即色嫫措复出,机村也就能够得救。
在同一系列的《荒芜》中,阿来也进行了类似的书写。一部分机村村民传说中的祖源地,觉尔郎峡谷中的废弃古国,被几位替村落寻找新耕地的青年发现;而这一发现,则来自其中一位觉尔郎古国后裔得到的神秘指引:“除了协拉琼巴,谁都不敢去想他们自己怎么能摸着黑从那悬崖峭壁上走了下来。迷离恍惚的协拉琼巴说:‘那有什么,先人指路。’”“反正,我看见了一个人走在前面,反正我听见了他对我说,来,跟着我来吧,不要害怕。反正,我在前面跟随着他,你们也就跟着来了。反正,他对我说,踩着我的脚印走,我也这样对你们说,踩着我的脚印走。结果,我们就平安地下到谷底了。”{24}在探索峡谷的过程中,峡谷居民后裔家族内传唱的古歌中提及的事物一一出现,歌词与谷底风物若合符契,甚至歌中所谓“狼神的魂魄”都出现了。这段传说与谷底移民后裔对古歌的传唱共同在情感上支撑了该家族与社群在饥饿与自然灾害、政治压力下的困难生计,且都被阿来的书写在文中所“证实”。
在《云中记》中,阿来对于云中村历史的书写,同样倾向于证实村落祭师传承的“阿吾塔毗引领下迁徙而来”的传说,而这一传说的情感作用,即是全书的核心立意之一{25}。为了证明该传说的真实性,阿来多次借阿巴的视野为我们介绍了矮脚人的坟墓等考古学遗迹,并让他带领地质队的余博士前往实地勘查了这些坟墓{26}。阿来还借地质队余博士回城后的查证行动证实阿巴观点的合理性:“博士离开云中村后,去图书馆查阅岷江上游的考古报告,知道这种葬式叫做石棺葬。考古报告也证实,采用这种墓葬形式的人不是今天还生活在这个地带的族群……当时余博士还不了解这些。但他确实看到了洞中人类的骸骨。”{27}文本中的这些考古学知识当然是正确的,但对文本分析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知识的正误,而是这些知识在文本中被呈现的方式。这种实际存在的墓葬类型,被阿来用来证实云中村以及云中村所代表的嘉绒地区的民间历史记忆,而阿来的这种操作,却又正成为他流露出属于嘉绒人的独特历史心性的症候:面对康区的历史,阿来倾向于以实证与文献压抑传奇,而面对嘉绒的历史,他却倾向于以实证与文献证成传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倾向似非阿来的故意;最重要的证据,是阿来在另外一些描写嘉绒的新世纪作品,如《大地的阶梯》《河上柏影》中,同样流露出了对实证的、反传奇的历史书写的青睐;只是在一部分较为微观的嘉绒题材作品中,阿来才很可能是无意识地倾向于支持一些传奇性的历史叙事。
除了阿来在进行康区历史书写与嘉绒历史书写时不同的情感与思考取向外,他在叙述两地现实时的情感态度也可能被加以区分。将《山珍三部曲》中描写江畔农区(可以理解为嘉绒)的《河上柏影》和《蘑菇圈》与描写牧区(可理解为非嘉绒的安多、康区)的《三只虫草》相比,二者除情节中本土人群“移民(对牧民来说同时还是定居)”与“打工”孰先孰后的区别外,它们的写法也完全不同,前两者是阿来最常见的写法,即卢卡奇所谓“史诗”式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在较长历史时间尺度内来展现人物成长与变化的方法,而《三只虫草》的展开则抛弃了此种时间性的展开方式,采取了空间式的展开方法;它的核心情节发生在一个虫草季的一周之内,而在本书中阿来试图赋予叙述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厚度的手法,则是随着“三只虫草”的流转,进入官场等更多的社会空间之中。这种区别绝非偶然,也未必可以由出版时《三只虫草》的“童话”定位加以解释,我以为,这是阿来感受到自己之前几次以文学形式书写康区历史时的某种局限后,采取的一种在文学上介入康区的“迂回策略”。{28}
阿来在2001年版《尘埃落定》的后记中说,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地怀乡”{29}。然而,当他离开故乡,迁居成都后,他却坦承,自己曾经并不热爱故乡:“跟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我青少年时代的许多努力,就是为了逃离家乡。”{30}他质疑汉语语境中,对个体“必须”怀乡的意识形态律令:“当我们在学校学习,或者通过阅读自学,在汉语的语境之中,好像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一个人必须爱自己的故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在道德上就已经失去了立身之地。”{31}他放弃了此前虚饰的“怀乡”态度,避免将故乡抽象化,这与他逐步放弃了“族裔寓言”式样的写作是同构的。恰恰是通过对更具体与有机的区域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阐释,他才得以在写作中实现了与故乡的真正和解,从而让自己的认同得以在扎下更深厚根脉的同时,也成长到更高远的空中。概括阿来在文学创作中表达的族群认同流变,我们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面对主流文坛时,泛化的藏人身份显然是更好的敲门砖;而从写嘉绒地区的散文《大地的阶梯》开始,阿来开始明显地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嘉绒认同,一方面是自己重新回家几次采风,一方面是藏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抵制和批评,再加上文学市场也对泛化的“西藏书写”开始厌倦,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阿来才越来越明确自己写的不是“藏族”风情,而是“上达人性,下绘嘉绒”,拒绝了其文学作为民族寓言的中间层次。也正是在这种认同变化的背景之下,阿来笔下的康区历史与嘉绒地区历史,也就开始具备了不同的色彩,分别趋向彻底的“去神秘化”,与对某种“神秘色彩”的温情态度。
注释:
{1}阿来:《流水账》,摘自于氏:《宝刀》,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②梁海:《阿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③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④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⑤王蓓:《格萨尔王传与多康地区藏族族群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博士论文。
⑥阿来、夏榆:《天上也是人间,神话也是现实》,摘自夏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04页。
⑦李玉琴:《嘉绒藏族〈阿尼格东〉叙事差异性解读——兼论故事的宗教特性》,《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⑧李菲:《心像·物像·绘像:阿尼格冬与藏边社会地方历史的图像隐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2期。
⑨郑少雄:《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基于阿来四本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社会》2018年第2期。
⑩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11}在《大地的阶梯》中描写金川之战的章节,阿来的态度也比较倾向于实证与考据,但这与该书作为散文与游记的体裁有关。
{12}{13}{14}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15}在阿来的《格萨尔王》中,晋美梦中的格萨尔有人与神两种形象。
{16}为说明这一点,阿来安排了如下情节:晋美参与学术研讨会,被学者们利用于此种“格萨尔史诗中的人物与事件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事件”的争论。晋美对此感到“不喜欢”,于是主动离开会议。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17}阿来:《玉树记》,选自阿来:《一滴水经过丽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18}任容:《从“我”到“仲肯”——阿来小说中叙述主体的转变》,《阿来研究》2021年第14辑。
{19}摘自阿来:《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第259页:“不,历史是严峻的……历史的教训是严峻的,历史提供的选择也是严峻的……历史让你必须做出选择。”阿来、朱维群:《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凤凰网:“重涉那些历史旧事,我常常吃惊于经历那么多战乱,无论是清朝中枢,还是地方豪强,双方付出那么惨重的代价,却不思根本性的变革。”
{20}阿来、舒晋瑜:《阿来:民族主义的铁疙瘩》,《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8日。
{21}朱又可、阿来:《疯狂的虫草,疯狂的松茸和疯狂的岷江柏——专访作家阿来》,《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2日。有趣的是,阿来将“地方志”与“文史资料”列入“民间资料”中,从这样的分类方式中,可见在写作《瞻对》时的阿来眼里,更严格、更小范围的“民间资料”即口头材料、家谱、日记、寺院档案与商业账簿等对求真的、区别于文学创作的严肃历史书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22}阿来:《机村史诗·天火》,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23}阿来:《机村史诗·空山》,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216页。
{24}阿来:《机村史诗·荒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76页。
{25}关于这一点已有相对充分的先行研究,许多人注意到阿来本人在文中,对阿巴“不一定相信鬼魂”的描述,阿巴承担祭师的责任并非出自“传统信仰”,而出自在现代性下对特定身份的持守。
{26}{27}阿来:《云中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页。
{28}这并不是说《三只虫草》写得不好,我个人甚至将它列为我最喜欢的阿来作品之一,正因为阿来在写作《三只虫草》中投射的意识形态意图,不论是表达族群认同还是表达所谓“世界主义情怀”都比较少,也并未试图去以一种宏大的历史哲学去诱惑读者,这部作品才得以在现实主义的尺度上表现出一种老辣的风格,深刻地洞穿了戴在边缘地区被组织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消极后果上的层层面纱。
{29}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30}{31}阿来:《道德的还是理想的——关于故乡,而且不只是关于故乡》,摘自阿来:《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第132—133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李昌懋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