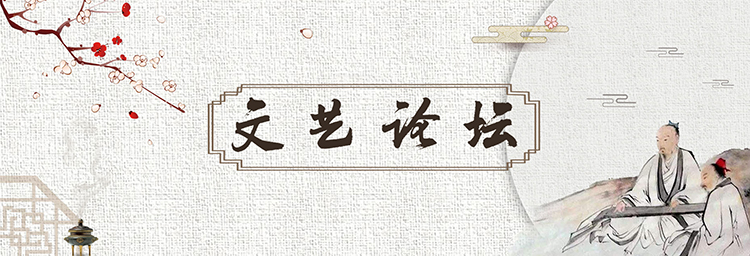
《暴风骤雨》 周立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土改小说的空间叙述与形式
——以周立波《暴风骤雨》为中心的考察
文/康富强 蔡翔
摘 要:对工作队下乡的土改小说而言,其空间叙述与形式是不容忽视的。不仅“时间开始了”,从空间叙事开始也是其重要的叙事特征。对工作地空间的打开和离开决定了土改叙事的进入与结束,不同的空间叙述形式也影响了土改小说的具体生成面貌。不同于赵树理和丁玲土改小说中的内部空间构造法,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扣着工作队的视角,由外而内地进入未知的空间,这意味着小说要处理未知的“暗处”并向内探明。由于这种由外而内的空间叙述形式无法呈现出乡村社会“内爆”的革命路径,元茂屯的土改斗争不得不依赖于工作队不断地向内发动,而“三斗韩老六”就是这一系列的结果。作为典范土改的表达性建构,《暴风骤雨》及其错位的空间叙述形式反映了北满土改的急促性和区域性特征。
关键词:土改小说;《暴风骤雨》;空间叙事;工作队;北满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再解读”思潮中,唐小兵对周立波土改小说《暴风骤雨》的重读已经成为该小说的经典阐释文本。其文章《暴力的辩证法》追踪暴力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时,特别分析了小说的开篇段落并将其指认为“一幅平和、灿烂的田园景色”,“一个和谐的农家情景”①——“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②。
小说开头确实铺陈了一幅七月清早的田园景色,但并不是和睦平静的。“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③突然驶入的这挂四轱辘大车,打破了这个看似和谐的农家情景。这时叙事角还在牛倌个人那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④。紧接着,叙事角瞬时升高扩大并完成了向全知全能方式的切换:“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⑤这个视角的切换是一个巨大的引导,它引导着读者跟随隐含作者的叙述去俯瞰东北农村大地上卷起的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唐小兵在分析这段话时,把关注点放在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工作队到来的时刻。在他看来,“这一刻表现成了历史的真正开端,……我们刚目睹的‘自然景色’(‘空白地区’)便也被摔进了‘历史’的漩涡——作品表现历史新‘起始’的同时,也抹杀了历史,构出一个再生的神话”。“在这里‘历史时间’取代并且压制了‘自然空间’,由此小说的叙述得以展开,由此空间所体现的并存和张力被卷进单质同向的时间流。”⑥这是历史的新起始,是真正的开端,时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现代性的历史时间意识,也即小说的时间形式被评论者紧紧抓住。“时间开始了”,经由唐小兵对《暴风骤雨》开头的经典解读成了理解土改小说叙事的潜意识。但时间是在哪里开始的,如何得以开始似乎被忽视了。这个时间开始的空间是怎样的,如何把握这个空间,又如何将其结合进历史时间中去?土改小说中有关空间的叙述与形式值得认真考察。
一、空间叙事与小说时空体形式
按照巴赫金小说时空体所展示出的时空辩证法,“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凝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⑦。唐小兵分析的空间被卷入单质同向的时间流,其着重的就是时空体形式中时间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但是,时间的标志与变迁也要在空间里展现。所以,这个历史时刻的真正到来,建基于马车和工作队对土改空间的驶入。“东北松江省境内”,“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特别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这些空间语汇也就同样值得重视。它清楚地表明了土改叙事的首要任务是引出并进入工作地空间——元茂屯。也因此,小说《暴风骤雨》的叙事开端是萧队长的工作队坐着老孙头赶的大车进入元茂屯。“马车载来工作队”,这个小说开头的部分,不仅意味着“时间开始了”,也意味着小说是从空间叙事开始的。
从空间叙事开始,是工作队下乡的土改小说一个重要的叙事特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第一章“胶皮大车”讲的就是顾涌赶着白鼻带着大女儿经过洋河、桑干河到暖水屯去。小说以顾涌和胶皮大车为开端,也是引出并进入土改工作地的空间叙事。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是北满另一部著名的土改小说。它的写作时间比《暴风骤雨》晚,主题侧重于“煮夹生饭”。其第一段第一句是,“快要进了腊月天气,松花江沿上刮起烟雪。大道上,一张爬犁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从佳木斯市委来的沈洪,另一个是赶车的老板子金永生。“天气冷,人着急,马也跑得欢,一展眼,前面就是一个村子。”⑧这个村子叫高家村。沈洪坐着金永生的爬犁就是要到眼前的这个高家村去工作。平分土地时,高家村改名为江山村。马加也采用了下乡模式,同样是从进入式的空间叙事开始的。相较于《暴风骤雨》开篇的铺陈,《江山村十日》反而在进入的叙事上显得更加直接。
如何进入元茂屯,如何进入暖水屯,如何进入江山村,其实是工作队下乡的土改小说不得不首先处理的问题。这种引出并进入工作地的空间叙事,也意味着工作地空间如何被打开,土改叙事也就如何得以进入和展开。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中从珠河县到元茂屯的中间环节,即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以及公路上赶车的老孙头就显得尤为重要。公路和老孙头是《暴风骤雨》展开土改叙事的引子。而当斗倒了韩老六,打退了胡子,新的村政权建立以后,萧队长的工作要调动了,这时在土改叙事上结束的要求就出现了。我们看看小说是如何叙述萧队长离开元茂屯的:
一挂四马拉的四轱辘车赶进了操场。马都膘肥腿直的。车子一停下,牲口嘶叫着,伸着脖子,前蹄挖着地上的沙土。老孙头拿着大鞭,满脸带笑,跳下车来。
“又是你赶车呀,你这老家伙。”小王一面搬行李上车,一面招呼老孙头。
……
“在这儿,韩家的车子,把泥浆溅在你的脸上身上,还记得吗?”萧队长问老孙头。
“忘不了。”老孙头说。“那会韩老六多威势呀,……萧队长,你不来,咱们元茂屯的老百姓,哪能有今日?”⑨
赶车载着工作队驶入元茂屯的是老孙头,送萧队长离开的也是老孙头。也许离开时可以换一个车把式,但是在元茂屯和珠河县城之间的公路却是不能换的。所以,即便是离开时的叙事,小说仍然要对公路再一次书写:“在这儿,韩家的车子,把泥浆溅在你的脸上身上,还记得吗?”没错,这唤起了一开始的记忆。当老孙头带着工作队驶入元茂屯时,车子在路上的一个泥洼子里渥住了。“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胶皮轱辘蹍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⑩这一不能忘却的记忆,同时也是小说叙事不能缺少的回忆,宣告了新政权确立下农民的翻身。这是土改叙事的终极使命。这个使命在萧队长离开时必经的公路上进行了检阅。这时,公路作为一个空间载体,正是历史时间的标志。也只有在这时、在这里,唐小兵所引用的巴赫金小说时空体才算是完整的。
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绝不是那个平和环境里无名无姓、无容无貌的牛倌,而是吸引其注意力并带给元茂屯风暴的老孙头。老孙头始终是空间叙事的枢纽,在很大程度上是时空化了的。按照空间叙事研究的一般分析,老孙头这样的人物形象是与空间意象结合起来的。这种空间表征法被相关研究者认为是一些伟大作家能塑造出个性鲜明、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的秘诀。{11}同样,老孙头也并不是唐小兵所说的噱头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在周立波笔下的出现,乃至这个类型的人物开始稳固地出现于周立波的小说中,应当是周立波从《暴风骤雨》开始给自己的写作寻找到的且相当成熟的人物设置经验。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线索往后可以在《山乡巨变》里看到亭面糊,往前在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中却难觅踪迹。小说于东北书店发行后不久,1948年5月,东北文委召开了《暴风骤风》上部的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上老孙头的形象并未引起太多的讨论,只是偶有提及,“关于人物,我听到许多人说都喜欢老孙头,我自己也如此”{12}。但是到了1950年,《东北文艺》刊出的评论文章就关注到了设置这类人物的意义,“第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赶大车的老孙头,……老孙头这种人是农村里贫雇农阶级中的中间分子,是群众思想动态的代表人物”{13}。尽管作者曾坦言,“写场面比写人物容易对付些,这是因为场面的材料还容易收集,而各阶层的人物的行动,心思情感和生活习惯,往往难捉摸”{14}。但是,周立波仍然敏锐地抓住了老孙头这一类型的人物,将其塑造成反映地方社会和土改空间中各阶层思想认识、情感心理和行为动态的一面镜子。
二、小学校和“龙王庙”:由外而内与内部空间构造法
对《暴风骤雨》开篇和结尾处的叙事回顾说明了需要把注意力从土改小说的时间形式转移到空间形式问题上。实际上,不同的空间叙述形式也确实影响到了土改小说的展开路径和生成面貌。相较于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空间形式构造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两者是从乡村社会阶层构造的内部空间入手,先写明李家庄的人与宗族社会关系,再交代出暖水屯各社会阶级与村内的空间格局,而后出现工作员和工作小组。《暴风骤雨》不是这样,看似其全知全能的叙事掌握着土改运动的全过程,可从一开始,叙事者和工作队对元茂屯这个工作地的内部空间就是未知的,对其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其旧有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网络空间是不了解,也是不清楚的。
这个发现来源于小说第一章将近结束时的一个情节所带来的疑问。“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萧队长从榆树障子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就住在这行不行?’大伙都同意,一个个跳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15}这个疑问可以被简单总结为:为什么是小学校,不是龙王庙?工作队来到了元茂屯,面临了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住的问题。在小说中,萧队长是如此轻易地选择了小学校,但为什么是小学校?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个住的问题,让我们想起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里的龙王庙和《三里湾》中的“旗杆院”。龙王庙和“旗杆院”是工作队员和土改后农会的住所,但在此之前它们就已然不单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龙王庙被神像、戏台、村公所、公道团、自卫队等旧势力占据,{16}而壮地主阶级威风的“旗杆院”更是个象征着旧的封建权贵势力的空间,它们表征出了一个乡村权力结构的政治文化空间。这即是杜赞奇论述华北农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它们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是“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17}。这个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乡村社会的内部空间,在赵树理笔下是先交代出来的。那么,元茂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龙王庙”,或者说其旧有的权力结构的内部空间是怎样的?工作队对此是未知的,甚至连这个突然被选择出来的小学校也显得十分突兀。
因为未知,所以无法提前交代出来。也因为这个未知,在第一章的进入叙事上,萧队长曾三次向老孙头打探屯内的情况。第一次是霸蛮的韩家车子把泥浆溅到老孙头身上,萧队长问:“那是谁的车?”“到底是谁的车呢?”{18}第二次是由日本开拓团谈到韩老六拉起大排,萧队长问:“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这人咋样?”{19}第三次是打听胡子的情况,除了刘作非:“还有谁?”{20}面对萧队长的询问,老孙头都是支支吾吾唠起别的闲嗑或是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屯里的情形究竟怎样?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与血缘、宗派、姻亲等形成什么样复杂勾连的社会网络,贫雇农遭受到了什么样的盘剥与压力,他们的思想行动如何?只有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大会,工作队才见识到了屯子里的事情不简单,于是全体动员访贫问苦,收集材料,去探明元茂屯的内部空间。
反过来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在开篇之前就先有一个主要人物列表,这就交代出了暖水屯内各色人等的阶级身份和村内的阶级构成。而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交错在一起的,姻亲、血缘也网罗其中。比如村治安员张正典是地主钱文贵的女婿,被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和钱文贵是亲家,而贫农钱文富竟是钱文贵之兄。在人物出场顺序上,丁玲也有特定的安排:先写村内的人物,顾涌、钱文贵、黑妮、任国忠、董桂花等,而后才让老董、文采、杨亮、章品等干部和工作小组出场。小说第四章“出侦”,交代了暖水屯的空间格局。村子的中心是小学校,它是从前的龙王庙。学校对面有一个四方大平台,原是戏台。台后边有合作社和豆腐坊。豆腐坊墙上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大字标语。“中间是条向南的大路,路两旁全是砖房,村子里的有钱的人住在这里。往西去是许多小巷巷,都是土房子。这里住得又拥挤,又脏。”{21}这种居住格局的差异和分化以及大字标语的出现,表明了暖水屯的空间政治:既是过往历史的产物,也将是一个新的革命政治空间。{22}丁玲对暖水屯内部空间的交代,更是放到了村内各种人的各种思想动态上,比如钱文贵和任国忠的密谋,董桂花的怅闷空虚,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第八章“盼望”,既有盼望土改到来,想要再来一次清算的,也有带着恐惧,盼望不要闹得太厉害的。直到第十章“小册子”,才引出土改到来的正题。张裕民、程仁和李昌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李昌认为本村的土改轻而易举,有十足的把握。程仁觉得分配土地是不容易的,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张裕民考虑的是他们究竟能掌握多少力量,能否把旧势力彻底打垮。他觉得老百姓糊涂,常常动摇,有一点不满足就骂干部。他对即将到来的土改,有热忱,也有很多顾虑,希望区上早点派人来,派一个得力的人来。
这种优先着眼于工作地内部的空间叙述形式,可谓内部空间构造法。丁玲首先做出的是村内各阶级对即将到来的土改不同的心理分析,她下笔之处是放在暖水屯内部的,她的焦点也优先是暖水屯人,而不首先是土改工作小组。这种内部空间构造法传达出了暖水屯的土改斗争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内爆”{23},且爆出了斗争的复杂性、必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急迫性,“张裕民更去向区上催促,要他们快派人来”{24}。也正是这种内部空间构造法所表现出的村内问题的具体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引导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展开了暖水屯土改斗争的密谋、分歧、徘徊、争论、光明还只是远景、决定、醒悟、自私和翻身乐。《暴风骤雨》与之不同,不是由内而外的因为事情的急迫与难办而期盼工作队到来,完全是扣着工作队的视角由外而内,在对内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打开式运动。正是这个由外而内的空间叙述形式,决定了工作队要处理未知的“暗处”,也决定了革命的开展不得不依赖于工作队不断地向内发动,这就导致了“三斗韩老六”的叙事进程。
因为由外而内以及对内部的未知,就有了明暗格局,也因此《暴风骤雨》必须要处理这个“暗”并向内探明。这就很有必要分析一下那个失败的大会。工作队到元茂屯的当天,刘胜先召集大会的意见获得多数人赞成,老孙头吆喝人来开会。“从屯子的各个角落,里里拉拉的,有一些人来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在星星的微光里,三三五五站着的,尽是老头和小孩。”{25}会场上,白胡子和黑毡帽搅了局。白胡子说这屯里没有大肚子,黑毡帽说得先走一步,人群开始退散,最后连老孙头也溜走了。刘胜想不到的是在他们到来的当天,地主韩老六就暗地里安排了富农李振江,“跟他悄声悄气说了一会话,……只听见李振江的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六爷的事,就是姓李的我个人的事,大小我都尽力办’”{26}。这意味着,工作队进入元茂屯后,村内产生了敌暗我明的空间格局。而正是在这个暗处,地主有了耍花招使诡计的空间。从会议的结果看,李振江至少使了两重力量来搞破坏。第一重是人数,经过李振江的尽力办,来开会的人是里里拉拉、三三五五,且都是老头和小孩。第二重是搅局,“李振江嘁嘁喳喳在他背后说些啥”{27},可见白胡子和黑毡帽是受李振江唆使的。李振江是韩老六的狗腿,白胡子和黑毡帽又是李振江的狗腿。这个暗中破坏经过了两层力量的传导。在大会召开的同时,元茂屯的三家大粮户也在韩家大院的暗夜里密谋。三个人直唠到深夜,杜善人和唐抓子走时点的灯也经三人合计吹熄放回。韩家大院里更有行动,“洋镐和铁锨挖掘石头和沙土的响声,直闹到鸡叫”{28}。就此可见,《暴风骤雨》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去处理了“暗”。第一个层面是随着工作队的到来,屯内形成了敌暗我明的格局,且未经调查研究,以韩家大院为代表的内部空间是“暗”的;第二个层面是地主暗地里的破坏与种种对付的花招和诡计。这也是周立波在回复霜野来信时作的两点说明,韩老六的阴谋操纵是第二个层面的暗,工作人员的主观主义是第一个层面的暗。
尽管周立波阐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但他实际上并未明了霜野来信的真正挑战:“这个会不可能开得这个样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开辟工作的地区,初次召集一个群众会,他(群众)决不敢说,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而一个一个地都溜了。”{29}群众不敢走掉,这并不是孤证。在座谈会记录摘要中,李一黎也说:“因为那时群众不了解我们,所以也怕我们,叫他开会来,他是不敢溜掉的。”{30}也就是说写开会时群众的走掉,看上去是处理了“暗”并写出了土改进程的曲折,“但这种曲折的内里恰恰没有写出在北满土改时所处历史情境中社会现实和人心复杂的内涵”{31}。同样,小说开始就营造的韩家大院的黑大门楼、灰砖高墙、柳树障子、黑洞洞的枪眼,这是由事物色彩的明亮程度隐喻了“暗”。在小说里,仿佛“暗处”只属于韩家大院,工作队的障碍也就这一个,而屯子里真正存在的复杂纠葛,其内在晦暗不明、犹疑不安的群众心理以及有待发现和争夺的空间并没有被完全表现出来。土改是一场微妙复杂的博弈,地富、贫雇农、党的干部都在这个局里。除了地富阶级对贫雇农、干部的拉拢和麻痹,贫雇农会犹豫和耍两面派,也会过火和冒进。部分干部会脱离群众,积极分子也很复杂。在酝酿不成熟的情况下,“真正好的劳苦农民,是不容易以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来参加斗争的,而常常表现为中间分子(当然因为要出气报仇而很积极的也不少)流氓、兵痞、警察、特务则容易混入”{32}。小说看似以失败的大会处理了“暗”,但这种写法又确实没有深入“暗”,表现出“暗”,反倒是着急想触碰那个“暗”,抓住那个“暗”,破解那个“暗”。但工作队并不是“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小说所呈现的“暗处”以及对“暗”的处理只是作者按照既定的思路和给定的空间构造方式所展开的一个已经被提前透明化了的“暗”。周立波知道“暗”并向“暗处”进军,却未处理好“暗”,没能写出“暗处”的复杂纠葛与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反而有种透明感。这种透明感,在陈涌的评论文章中是“单纯”。除了人物和情节,它直指《暴风骤雨》未能写出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地主的阴谋破坏,看来都是毫无例外迅速地而顺利地被克服,我们很难想象现实生活正是这样的”{33}。
由于这种由外而内的空间叙述形式无法像赵树理和丁玲的土改小说那样呈现出乡村社会“内爆”的革命路径,元茂屯的土改斗争就不得不依赖于工作队不断地向内发动。这体现在小说对发动群众的刻意掌握上。初次积极分子会后,赵玉林引导大伙去找韩老六算账,却被韩老六打了伏击,主动变成了被动。而小说安排的是萧队长在此之前就意识到:“在群众的酝酿准备还不够成熟、动员还不够彻底和广泛的情形之下,也许赵玉林跑得太快了,脱离了广大的觉悟慢些的群众。”{34}初斗韩老六的会场上,萧队长看到了人们不关切、不热心的脸色,因此韩老六在献了地、拿了牲口衣裳后,就被释放了,这引起了工作队员的不满。萧队长为此解释道:“如果我们不耐心地好好把群众发动起来,由群众来把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地摧毁,封建势力决不会垮的,杀掉这个韩老六,还有别的韩老六。”{35}要想冲破封建势力的堡垒,就需要更深地向内发动群众,也就需要对韩老六抓了又放,“三斗韩老六”就是不断向内发动的结果。
三、从元宝屯到元茂屯:错位的空间形式与土改的区域性特征
为何《暴风骤雨》会与赵树理、丁玲土改小说中的空间叙述形式如此不同,又为何是这种由外而内的推进方式?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得从北满{36}土改的历史经验说起。而一旦对北满土改的历史经验与《暴风骤雨》的建构经验做出对比说明,便能进一步阐明空间形式问题之于土改小说的重要性。其实,土改小说最大的空间形式就是它的区域性特征。
“东北土改直接因于我军的军事失利,是希望通过发动农民挽回败势(建立基层政权,继而征兵、征粮)。”{37}这是指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东北局从长春撤到了松花江以北。早在1945年年底,毛泽东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中就指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也面临着对地理民情不熟的主观困难。{38}1946年5月,中央下发了土改的“五四指示”{39}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从事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把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置于工作的第一位”{40}。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七七决议”,决议要求“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使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迅速普遍执行”{41}。从7月到9月,东北局共发动了一万两千多名干部下乡,以至于松江省“机关里只留下两个看门的干部”{42}。在干部下乡的热潮中,周立波到松江省珠河县报到,被任命为元宝区区委委员,后改任区委副书记、土改工作队副队长。10月25日,周立波来到元宝镇,住在元宝镇小学。{43}小说中那个被萧队长突然选择出来的小学校就是以此为原型。
东北土改对于挽回东北局势是极重要且相当急迫的,“在六个月到八个月内,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东北群众工作搞起来”{44},但又是在“环境全然陌生、工作毫无基础、干部严重不足、土匪骚扰频仍的条件下进行的,恶劣而复杂的现实状态使‘深入生活’很难以按部就班的方式展开”{45}。客观上,东北的干部下乡与发动群众在形式上就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有时还要在部队剿匪的掩护下进村。在工作方法上,东北土改确是疾风骤雨的。工作团下乡,就是下到一个个“空白地区”并推动更多的“空白地区”:“搞根据地要由点到面,每一个工作团下乡,由一主村作起,突破一点,推动全面。”{46}“根据工作的经验,作出扼要的总结,并使各地经验迅速交流。”{47}这种运动的形态也直接影响到了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和深度。扣着工作队的视角由外而内进入不熟悉的村屯成为不言自明和无需多虑的形式被下乡的文艺工作者接受了下来。宋之的就说“在空白地区开辟工作”{48},韩进也讲“写到空白地区”{49}。这当然是错位的空间认识,东北农村并不是空白地区。在陈云的报告中,“北满所有股匪都是政治土匪”,“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北满多是山东、河北来的开荒农民,大佃农及经营地主很多,雇工、零工、伙种雇工占农民百分之六十”{50}。又由于日伪的统治,一般民众认为“国民党是正统,牌子正,有美国援助,力量大”{51}。
周立波选择了他1930年代形成的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疏离于对象和环境的介入现实的方式。{52}小说首先入笔的是不具北满时代特征的田园风景,首个感知中心也是那个与北满的时代环境没有情状关联的牛倌。周立波用自己的感知方式构造了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元宝屯的,也不是土改发生地元茂屯应有的空间。随着叙事视角的全景切换,这个风景化了的空间转到了革命政治的规范叙事上来,工作队驶入了,“时间开始了”。很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断裂,但这个断裂不只是关于叙事的,也是关于对土改空间形式的把握的。它反映了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乃至下乡的工作队与北满地方社会的隔膜。工作队要快速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但做不到像肖洛霍夫对哥萨克农民的了解那样深入。知晓村屯的来龙去脉,每个家庭的迁徙与生活,个人的经历、性格与行为{53},这在短期内都是困难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在土改中完全做到,否则就不会有夹生。韩进就指出小说“未能多方表现丰富的农村生活,……一个长篇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如《静静的顿河》就写得很好”。{54}《暴风骤雨》开篇在空间形式上所呈现出来的断裂和错位,也在无意中表达出了北满土改在运动铺开时的急促与艰难。
除了初步把握土改空间时所存在的错位,《暴风骤雨》在呈现元茂屯作为根据地空间被开辟出来的过程与形式时,也存在另一个层面的错位。这一错位或许可以用黄宗智分析中国革命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一致与偏离{55}给总结出来。无疑,《暴风骤雨》是作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56}被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他的诉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57}。在写作时更是借助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把东北的土地改革的几个主要阶段的主要特征压缩在里面”{58}。经过周立波的创作与改写,《暴风骤雨》几乎算是可资借鉴和参考的土改运动的工作大纲和经验手册。事实也正是如此:“上卷刚刚问世,就在东北文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甚至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作为工作队的参考书。”{59}
可错位也正在这里,北满被开辟为根据地空间的形式和过程与小说存在着偏离。小说上部的故事时间是1946年7月至9月,也即反奸清算的阶段;下部是“砍挖运动”和平分土地时期。反奸清算阶段,“当时到处点火,到处燃起斗争,刮了一阵风。斗争不彻底……未能贯彻群众路线,于是发生包办代替……群众本身存在着思想顾虑,好人不敢出头,狗腿子钻空子,变成了夹生饭。这夹生饭是带着普遍性的,也很严重”{60}。所以,当时推广的经验是“介绍马斌式的人物,提倡马斌式的作风”{61},也就产生了“经济—武装—再经济”{62}的办法。在元宝屯,“1946年7月,‘萧队长’萧文达到后,仅用了两个月就建立了农会”{63}。北满土改的客观现实是时间短、任务急、又普遍夹生,但“作为开辟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来看,这个村子的成绩是过于好的”{64}。更大的错位还在于小说将北满土改一波三折的运动过程做了部分简化。“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地捎了几笔,没有着重地描写。”{65}回避运动发生的偏向,抽掉某些阶段和环节,将开辟北满根据地的过程叙述为没有较大波澜的空间运动形式,这确实给小说带来了一定的批评。蔡天心就指出小说“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66}。北满的土改运动整体上经历了先右、后左、再纠偏的过程。从前期的犹疑动摇,照顾地富阶级到地主、富农不分,侵犯中农利益,也在打杀人上有过左的行为,最后由领导进行普遍的纠偏。{67}也因此,座谈会上有另一种声音:“作为工作经验来介绍,拿到新地区去,这点也是值得考虑的。”{68} 实际上,这种错位的空间叙述形式,也提醒我们不管是具体的土改实践还是土改小说都是有区域性特征,也是有区域性限制的。
总的来看,从空间叙事开始的《暴风骤雨》,在叙述元茂屯被开辟为革命根据地的空间形式时,是扣着工作队的视角由外而内进入未知的工作地空间的。小说试图向内探明未知的“暗处”并写出土改运动的曲折,可惜略显透明和“单纯”。通过对错位的空间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暴风骤雨》恰恰反映了北满土改的急促性和区域性特征。
在此过程中,这个工作地空间被开辟出来的历史经验并不透明地敞开在那里,可以让作家一览无余,更因作家们不同的观察视角和感知方式,经其文学创作转译后的土改小说的地理空间和叙述形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注释:
{1}⑥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参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第120页。
②③④⑤⑨⑩{15}{18}{19}{20}{25}{26}{27}{28}{34}{35}周立波:《暴风骤雨》,摘自《周立波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第5页、第5页、第5页、第243—244页、第6—7页、第13页、第7页、第10页、第11页、 第28页、第20页、第29页、第25页、第62页、第86页。
⑦[苏]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⑧马加:《江山村十日》,东北书店1949年版,第5页。其实赵树理的土改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也是从空间叙事开始的。小说开头第一句是“李家庄有个龙王庙”。这个龙王庙是铁锁和春喜争夺桑树的“茅厕事件”必须依存的审判空间,也是整个小说想要打破并改造的乡里空间。空间是超越于故事和人物的总体性视野。
{11}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2页。
{12}{13}{14}{29}{30}{48}{49}{54}{57}{58}{60}{61}{64}{65}{66}{68}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第265—266页、第246页、第242页、第259页、第254页、第263页、第263页、第250页、第249页、第258页、第262页、第255页、第250页、第269页、第257页。
{16}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
{17}[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21}{24}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第44页。
{22}[法]列斐伏尔著,陈志梧译:《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23}所谓“内爆”,贺桂梅曾以“赵树理将农民的革命思想表现为乡村内部的引爆”,以区分从外向内输入革命的方式。参见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31}{52}何浩:《“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32}{42}《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全省群众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土地改革运动·上》(内部发行),黑龙江省档案馆1983年,第144—145页、第134页。
{33}陈涌:《暴风骤雨》,《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合刊。
{36}{38}北满根据地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等地区,东满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相关地区,西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以西的相关地区,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相关地区。1945年9月18日,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1946年6月,以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的新的东北局成立)。北满分局于1945年11月16日成立,1946年6月与东北局合并。北满下属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绥宁五个省。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张闻天为合江省委书记,张秀山为松江省委书记。参见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2—1183页、第1180—1181页。
{37}张均:《〈暴风骤雨〉 的史实考释》,《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39}{67}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纠偏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纠正土地改革打击面过大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
{40}{46}魏燕茹编:《张闻天在合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第14—15页。
{41}{44}{47}{50}{51}{62} 陈云:《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5页、第238页、第233页、第225—226页、第236页、第226页。
{43}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9页。小说的原型地在当时叫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屯,即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改名后,通用元宝镇。本文依托于北满土改的基本史实,故本节标题仍用元宝屯。
{45}梁帆:《重审“红色经典”的生成过程——解读〈暴风骤雨〉的一种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53}关于东北农村的移民社会,元宝屯的建村史,小说人物原型的迁徙史,参见程娟娟:《从地域性视野重新审视土改文学——以〈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0年第2期。
{55}[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摘自《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56}阎浩岗:《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接受与传播的内外机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59}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在东北》,《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63}张鹭:《〈暴风骤雨〉内外的“元茂屯”》,《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8月18日。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康富强 蔡翔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