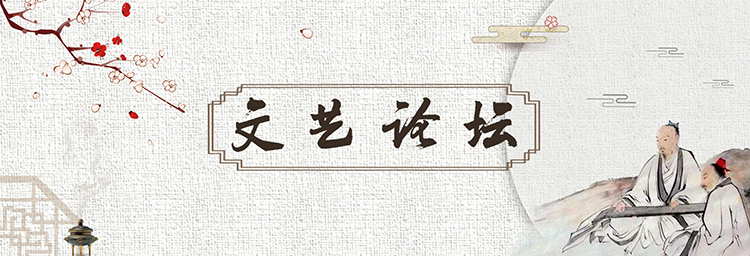

经典昆剧《十五贯》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清官”之名下的十七年“清官戏”写作研究
文/唐蕾
摘 要:“十七年”文学中“清官戏”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占据的位置却很醒目。从《十五贯》到一系列“海瑞戏”,此时期的“清官戏”在写作重心上完成了从清官智断向忠奸斗争的转化,在民间趣味与政治诉求间摇摆。无论是对“清官之恶”的暴露批判,还是“清官之死”的悲剧写作,在况钟、海瑞等一系列清官名义下的写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清官戏”本身。
关键词:清官戏;《十五贯》;海瑞戏;《团圆之后》;《谢瑶环》
一、“清官戏”的演变:从清官智断到忠奸斗争
“清官”意识、“清官”情结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存在。“清官”一词早在《三国志》卷57《虞翻传》中就出现了,指清贵简要之官职,与“浊官”相对;而后世表达官员清廉公正、勤政爱民之意的“清官”概念则出现于宋元时代。①“一般而言,政治上的清官,主要是指能稳定国家的法制和政局,与不法之臣乃至皇帝的随意变更国家政体、法制的行为作斗争,擅长于处理与皇帝的关系以及在绝对效忠皇权的前提下尊重民意、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②作为封建官僚的一员,清官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但有时也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因而在民间受到推崇。“清官戏”这种艺术形式寄寓了人民的政治理想,其中所传达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等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民间更是长期受到欢迎。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官戏”和大部分旧戏一样,徘徊在“人民性”的边缘,面临着被遴选、被改造的命运。1956年,《十五贯》进京演出大获全胜,在政治界与文艺界的大力宣传下,作为其显性外壳的“清官戏”似乎被证实可以为当代戏曲吸收、改编。然而,伴随着“人民性”“封建伦理道德”问题讨论的深入,“清官戏”仍不断接受着审验,发展相对缓慢。“十七年”文学时期,“清官戏”数量并不多,但是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到《海瑞罢官》《谢瑶环》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清官戏”显然又占据了醒目的位置。
1.《十五贯》:“清官戏”在创作与解读中的错位
20世纪50年代初,不少“清官戏”因为阶级性问题难以上演,但是文艺界一直在努力。1956年张庚在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上为“清官戏”正名,指出统治阶级中也有同情劳动人民甚至愿为他们服务的人,比如“清官”和为民请命的人物。③而《十五贯》的成功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让“清官戏”重回人们视野。在《十五贯》的发展轨迹上,各级领导的关注、推荐、指示格外醒目。浙江省文化局局长黄源敏锐地在这部戏中发掘了况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特质,因而成立工作组专门改戏。在上海公演期间,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当时在上海视察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都曾观看演出,评价颇高。上海组织区委以上干部观摩,并向全市公安人员做了推荐。1956年进京演出后,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向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做了推荐,罗瑞卿看完后,认为这个戏提倡对人民负责,大兴调查之风,很能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在短期内看了两次,并作出指示:“这个戏全国都要看,特别是公安部门要看。”随后,周恩来参加了《十五贯》座谈会,肯定了这个戏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讽刺意义。④在这种情势下,文艺界大力宣传推广,作为显性外衣的“清官戏”似乎也被证实为可推广。
《十五贯》改编自清初传奇《双熊梦》,故事最早取自宋代话本《错斩崔宁》。《错斩崔宁》中还没有“清官”拯救无辜百姓的情节,冤案发生后,由凶手自己说出真相,原判官受到惩处。《双熊梦》将这个“戏言成巧祸”的传奇故事发展得更为离奇,熊氏兄弟遇祸皆因十五贯钱而起,弟弟遭遇冤情后,哥哥为了救弟弟,路上遭遇了“错斩崔宁”中的祸事,兄弟二人都由常州府过于执判定为死刑,经苏州巡抚周忱定案,交由苏州知府况钟监斩。况钟梦中得到启示,觉察冤情,请求重新审理,经过调查破案,熊氏兄弟沉冤昭雪。虽然况钟破案缘自梦中神示,但是比起《错斩崔宁》中草菅人命的酷吏,他能够以自己的仕途为代价为民请命,实地探访找出真凶,已经将原先的传奇故事转变为一个具有说教意义的“清官戏”。最后,况钟解救了熊氏兄弟,昏官过于执也幡然悔悟,一变而为清官,促成了熊氏兄弟“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大团圆结尾。
昆剧《十五贯》在《双熊梦》基础上改编,删掉了弟弟熊友蕙一线,是一个典型的“清官戏”,剧中几位官员也不断强调自己的“清官”身份。过于执上场念白道:“上自巡抚,下至黎民,哪个不知我过某人英明果断。”周忱也自认“清官”,当况钟拿冤案激将他,意指其为昏官时,周忱马上回复“无锡县与常州府都是朝廷命官,国家良臣,见闻多,阅历多,审理此案,决不会有什么差错的”。而况钟更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清官”意识,出场时自称“体民苦,察民情,平生愿,效包拯”。行刑前,熊友兰与苏戌娟纷纷用“清官”激将况钟,一个说:“人人都说你是爱民如子,包公再世,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小人含冤而死吗?”另一个说:“你要是屈斩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呢?”况钟立刻决定为二人翻案,想到翻案必定困难重重,可是“错杀人,怎算得为官清”,“清官”意识成为况钟翻案的重要心理支撑。连罪犯娄阿鼠听到况钟查案都慌了手脚,因为他知道况钟才是真清官。
作为一部“清官戏”,《十五贯》将主题设定为“清官判”与“忠奸斗”两部分。“清官”意识两次在情节与戏剧结构上形成逆转,第一次是熊友兰、苏戌娟用“清官”意识激将况钟,第二次是况钟用“清官”意识激将周忱。两次“激将”分别是“清官判”与“忠奸斗”的转捩点,第一次激将,“冤民”与“清官”的矛盾化解,况钟接下来采取了勘察、暗访、套口供、抓捕罪犯等一系列行动,从发现冤情到冤案解除,整个“清官判”一气呵成。第二次激将,上演了一场“忠奸斗”。“见都”一场,况钟连夜去见周忱,遭遇“胆小如鼠,却也可笑”的夜巡官与“狐假虎威,可恶得很”的中军的阻拦和一番刁难后才见到周忱,二人相争不下,逼得况钟只能以官印为押,请求宽限数月查案。周忱无奈同意,却将时间缩短为半月,“倘半月之内,不能查得水落石出,本院当奏明圣上,哼哼,题参未便”,一个盛气凌人又阴险狠毒的昏官形象被烘托出来。除了与周忱的较量,剧中况钟与过于执的“忠奸斗”,对二人性格刻画也颇为传神。从创作来看,这部剧较多保留了民间趣味,主要围绕“清官判”一线展开,“智断”部分最为精彩。但是从当时的解读文献来看,重心却落在了斗争上。
《十五贯》对斗争的淡化处理,在当时遭到质疑,批评家认为看完“访鼠”,高潮已过,最后一场“审鼠”有草率结尾之感,要翻案还得和周忱、过于执等人作斗争,改编本没有写出来。⑤正如巴人在《况钟的笔》中指出的,况钟要用笔除掉坏人保护好人必须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6},对“主观主义者”与“官僚主义分子”的斗争才是这部戏得以大力推广的原因。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7}《十五贯》的推广正是要在对比中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与态度。甚至可以说,警示、改造现实生活中的“过于执”们是《十五贯》推演中更为重要的一环。
此时期对“过于执”的解读是颇为用心的。与况钟相反,过于执代表着粗暴的工作作风、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但是和《双熊梦》类似的是,解读中,过于执并未被视为一个彻底的昏官,而是认为其有向清官转化的可能性。相比周忱这样“一个僵死的灵魂”,“过于执不是有心为恶,只是思想上有很大缺点:主观主义。他如果能把这缺点克服,还是可以做些好事的”{8}。认为过于执本意是讲求清廉公正的,在主观意图上也是愿意“为民做主”的。只是在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上出现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因而,过于执被视为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人,他不是存心要做坏事,而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无心办了坏事。在我们中间,过于执这样的“好”人是有的。{9}
尽管《十五贯》在创作中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但仍具有典型的“清官戏”要素,其精彩之处在清官查勘、智断、辨明冤案一系列过程,随着冤案的解除,忠奸斗争一线也就结束了。但是在解读过程中,《十五贯》更多被视为一个政治文本,解读重心落在了斗争上。剧本中,过于执明显是一个刚愎自用、“清官尤可恨”的酷吏形象;但在解读中,为了配合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批评,而肯定其动机与道德本性,将过于执与况钟的矛盾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认为他的错误是“好心办坏事”。在创作与批评的错位中,“清官戏”的创作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暗含龃龉。
2.“海瑞戏”:以清官之名的模式化写作
《十五贯》成功了,“清官戏”创作得到了肯定,但“清官”的阶级性问题仍令改编者顾虑重重,较长一段时间内,改编寥寥{10},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海瑞热”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现象。传统戏曲、小说中有不少以海瑞为原型的作品,一方面展现出海瑞善断案、富有审讯才能的特点;一方面以忠奸斗争为核心,如流传于嘉庆年间的《海公大红袍全传》和道光年间的《海公小红袍全传》。{11}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史学界对于海瑞的研究热潮,文艺界也不断推出“海瑞戏”。据统计,自明末至今,有关海瑞的剧目约43出,“海瑞戏”集中出现在1958年以后,多达27出,数目是有清一代“海瑞戏”的三倍。{12}此时期比较著名的“海瑞戏”有《生死牌》《海瑞背纤》《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等。湘剧《生死牌》中“海瑞”作为配角,仅在结尾部分出现,但这部戏开启了“海瑞热”。毛泽东曾四次观看,当看到三女力争死牌时,曾欣然对随同观看的马少波表示:“舍己从人,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嘛!不必说我说的。你可以写文章。”{13}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次观看这部戏,开始对海瑞产生兴趣,让秘书田家英把《明史·海瑞传》找给他看。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讲到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时,向与会者谈起了海瑞的故事,表示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14}
湘剧《生死牌》对旧本改动较大。传统戏曲里没有所谓的贺总兵之子,而是一个假冒的巡按调戏民女王玉环,反被王玉环打死。知县黄伯贤听信谗言,判了玉环死罪,黄伯贤的女儿、丫环和女塾师向其说明真相,但是黄伯贤不愿改正。于是三个女子争相替玉环去死,并在刑场上揭露真相,黄伯贤终于醒悟;此时,海瑞也来到刑场,解救了几位女子。旧本中黄伯贤和《双熊梦》中的过于执类似,展现了一个武断偏执的酷吏如何转化为清官的故事。结尾海瑞的出现,更是将全剧推至情感高潮。湘剧《生死牌》则设定了明确的忠奸斗争模式,黄伯贤直接被设定为清官,他查明真相,不肯滥杀无辜。后来发现王玉环竟是自己救命恩人王志坚的女儿,黄伯贤的女儿黄秀兰为了保护父亲和王玉环,抢着赴死。黄伯贤不忍判斩,竟至晕厥,而为了不被前来监斩的贺总兵发现掉包计,又不得不立刻将女儿斩首。面对恩人王志坚的喊冤,黄伯贤佯装不理,坚持要斩女儿假扮的“王玉环”。
这个戏里涉及很多传统伦理因素,黄伯贤不杀王玉环是“为民做主”,但其中又夹杂着“报恩”的因素。王志坚是抗倭将士,救他的女儿便和民族大义结合起来。黄秀兰抢着赴死,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尽“孝”。在“孝”“义”等民间情感与民族大义的绞缠中,这个“清官戏”有些不那么纯粹。然而清官黄伯贤在这场忠奸斗争中完全处于下风,一开始就受到贺总兵“丢乌纱帽”“丢脑袋”的威胁,毫无招架之力。假设没有海瑞的出现,发现掉包的贺总兵将把三位女子统统处死,“孝”“义”等民间情感都将不保。因此,这部戏的忠奸斗争是从戏剧的尾声——海瑞登场才开始的。和《十五贯》极力塑造的实地取证、明察暗访的清官况钟不同,《生死牌》里的海瑞是作为“清官”的象征符号出现的。在平冤狱的过程中采取了“道听途说”——听王志坚和王玉环姨母的对话了解案情;“刑讯逼供”——要对贺总兵家奴用刑,迫使他说出真相;“偏听偏信”——仅听取黄伯贤的解释就简单破案。而对于贺总兵的申辩,海瑞反驳其父子在此地“横行霸道,欺官害民”,轻易就扭转了斗争局势。难怪当时有评论说,这部戏就应该以悲剧告终,让贺总兵把三个女子一起杀掉,这样更显真实。{15}《生死牌》中的“海瑞”形象无心插柳地引发了“清官戏”的热潮。然而其中混杂的“忠孝节义”等人伦情感问题,在日后的讨论中也逐渐暴露出来。
“海瑞热”兴起后,陆续出现了《海瑞背纤》《海瑞上疏》《海瑞罢官》等较有影响的几部作品。其实这几部作品中,海瑞都未取得绝对的胜利,都有失败与妥协,但是却被塑造为刚直果敢的革命斗士形象。《海瑞背纤》中面对位高权重、气势汹汹的张国公,海瑞当面将其贪赃枉法的罪行和盘道出。《海瑞上疏》中则性格更为火暴,面对整日求仙荒政的嘉靖,海瑞想依靠首辅徐阶进谏劝告,没想到徐阶却是撰写青词贺表的“甘草”,不为所动。海瑞慨然决定自己写谏书骂醒明世宗,并令仆人把棺材搭在午门。海瑞骂皇帝的过程被描写得极富喜剧性,海瑞先是“不认君”,不肯跪穿着道袍的皇帝,气得皇帝咬牙切齿骂他“畜生”。海瑞问皇帝,疏本好是不好?皇帝恨极,切齿回答:“好哇!”海瑞马上对大臣们说,我的疏本,万岁也说是好的呀!一来一回,海瑞全都占据上风,驳得嘉靖哑口无言,完全处于劣势,在海瑞的戏谑声中显得滑稽又可怜。皇帝想杀海瑞又因其“清官”名声在外,不敢残害忠良,气得直接吐血,及至最后一命呜呼。海瑞不仅把皇帝痛骂一顿,甚至还直接要了他的命,这场向最高统治者发起的斗争,海瑞大获全胜。
剧本最初的创作中刻意淡化了海瑞上疏“忠君”的本质,后来在中宣部领导同志的建议下,增补了海瑞在狱中得知嘉靖晏驾的消息时号啕大哭、酒饭呕吐一地的情节。{16}原剧把海瑞塑造成统治阶级的坚定挑战者,为民请命,也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百姓们“跪香请命”,恳求释放海瑞,后来修改为给海瑞送牢饭。虽然修改本中,海瑞为嘉靖痛哭流涕,但是阴霾很快一扫而去,随即转到出狱的“海青天”被百姓们簇拥着。突然“变天”了,百姓们都躲在海瑞的雨伞下。海瑞说,可惜我这把伞太小了!百姓们说,有这样一把,也就难得了哇!无论是《海瑞背纤》中廉洁奉公、体恤民情的形象,还是《海瑞上疏》中脾气火暴、机智应变的挑战者和为百姓“遮风避雨”的形象,“海瑞”都表现得相对醇化而扁平,跳出了阶级身份局限。
《海瑞罢官》则围绕海瑞为洪阿兰一家平反冤案展开,冤案皆因王明友、李平度的贪赃枉法所致,其背后靠山正是对海瑞有恩的徐阶,因此引出了海瑞与王明友、李平度的斗争以及与以徐阶为代表的乡官集团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断案”“求情”“反攻”与“罢官”四场。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在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处理得很细致,从不同阶层对“清官”的认识展开。写出了不同官员对待海瑞的态度,贪官王明友得知海瑞上任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而官声尚好的郑愉对海瑞则是颇为敬仰的,讲述了当年海瑞冒死上疏一事。徐阶对待海瑞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他是个沽名钓誉的伪清官,既注意名声,又要保护切实利益。海瑞向他请教为官之道,他一面说出自己对“吴下刁民”的看法,暗示海瑞要保护好官的利益;一面又冠冕堂皇地指出如果乡官不法,鱼肉良民,自然“豺狼当道要驱散,尚方宝剑莫投闲”。海瑞刚走,便立刻找来儿子徐瑛,一面告诉他对付海瑞的办法;一面想着海瑞对自己当是知恩图报,不至于翻脸。同时,吴晗也很注意在“清官”与“民”间建立联系。海瑞的母亲谢氏深明大义,回忆抚孤往事,讲述了儿子与人民的血脉深情;妻子王氏和忠心耿耿的仆人海朋虽为海瑞的刚直清正而担忧,却都完全理解和支持海瑞为民请命。而暗访中,乡民对“海青天”定能为民做主的信心,也坚定了海瑞的信念。通过不同阶级对待海瑞的态度,实际让清官海瑞跨阶级地具有了“人民性”的本质。
尽管在《海瑞罢官》中,史学家吴晗践行了他对于“历史真实”的表达,但仍然在“文学真实”上做出了很多让步。《海瑞罢官》前后改了七版,前四版中,吴晗以“退田”为主线,“除霸”为辅线;后听取多方意见,改“除霸”为主题,“退田”作为陪衬。剧中最后一场原先设为“送别”,海瑞离任,百姓依依惜别。穿插海瑞与新任巡抚戴凤翔交接场面,在百姓的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就此离去。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把这场戏改为公堂判斩,劲头会大一些。对此,吴晗是很有顾虑的,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充军,并未处死,这样处理,是否妥当?改了好几次,才下决心,处死徐瑛,改写成现在的“罢官”。{17}
无论是写作中“退田”到“除霸”主题的转变,还是解读中姚文元将“退田”“平冤狱”主题与“单干风”“翻案风”关联起来,“海瑞”这个清官形象都承载了太多政治因素,这当然与毛泽东对“海瑞”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推崇《生死牌》中的海瑞,是希望干部们学习海瑞敢说真话的精神。而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谈到《生死牌》,说海瑞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自己喜欢和支持的是“左”派海瑞。胡乔木曾经说过,毛泽东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18}。直到针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展开海瑞批判,“海瑞”虽然是一个大传统和小传统都认可的“清官”形象,但是从讨论伊始就成为政治符号,承载的一切超出了“清官”概念本身,甚至可以说和“清官”关联性并不大,尽管其引发的“清官戏”批判轰轰烈烈,但是在政治的设定中,“海瑞”的角色定位从来就不是一位“清官”。
从《十五贯》到《海瑞罢官》,“清官戏”由暗场走向明场,在写作中也由早期民间趣味的表达,自觉地向着政治诉求转化。早期写作中精细地描画清官巧谋善断、平反冤狱的过程,缺乏实权的清官唯有依靠智慧,方能获胜。此时期“清官戏”的合法性仍有待证明,因此创作重心常落在“为民做主”的清官意识上,以此达到跨阶级的“人民性”的表达。相比况钟,海瑞的受关注,使其从一开始就显得毋庸置疑。此时期的“海瑞戏”尽管也是“清官判”与“忠奸斗”的结合,但前者显然已让位于后者。海瑞成了权力的象征,他不再需要依靠智力取胜,在骂皇帝、斗权贵的斗争中,他所表现出的勇敢、自信,都说明了权力在无形中的转移,这种权力源自一种政治保障。而这位“背纤”“上疏”“罢官”的海瑞表现出的一系列特征在历史逻辑与文学逻辑上都失去了真实性。
二、反“大团圆”的“清官戏”悲剧模式探析
传统“清官戏”往往采用“大团圆”结尾,因为清官的明察秋毫、为民作主,无辜的百姓不仅能洗清冤屈,还常常获得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补偿,所以绝大多数“清官戏”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此时期改编的“清官戏”尽管在政治性和教育意义上作了修正与拔高,但基本上仍循用喜剧结尾,即便是一些正剧,也往往克制悲剧性因素的处理,这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密切相关,剧本既要暴露历史斗争残酷黑暗的一面,又要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展现光明的前景,避免过分凄凉与压抑。在“十七年”几个著名的“海瑞戏”中,除了《生死牌》这个非典型“海瑞戏”悲剧性因素较为明显,《海瑞背纤》《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等基本都是采用喜剧性的光明结尾。但实际上,清官戏中常常具有悲剧的情调,无辜的生命被毁灭,含冤受屈的又常是良善的,犯人却得以逍遥法外,再加上贪官污吏的独断专横,清官戏的前半部分往往是既悲且愤的;即便清官出现,化解冤情,然而美好的人或事已经被毁灭,补偿或许能够出恶气,但是悲伤的情绪仍难以消散。此时期有两部“清官戏”就采用了悲剧形态,一部是莆仙戏《团圆之后》,另一部是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但是两部悲剧却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1.《团圆之后》:“清官之恶”的反清官戏模式
被称为“继《十五贯》以后戏曲剧目改编整理的又一胜利”{19}的《团圆之后》{20}是一个展现“清官之恶”的反清官戏,据传统莆仙戏《施天文》改编而成。原剧写秀才施天文母亲叶氏与郑司成通奸。后施天文娶柳氏为妻,柳氏无意中发现婆婆通奸之事,叶氏羞愧自尽。柳氏为保婆婆名节,不肯说出实情,被舅父叶庆丁诬为逼死婆婆而告到衙门。县官判罚柳家巨款,因为与叶庆丁分赃不清,而将案件送到按司洪如海处审理,审案时,在座的知县杜国忠察觉柳氏有冤情,经洪如海同意后,将柳氏带回复审,后了解到实情。案情大白,郑司成被斩决,柳氏释放,施天文夫妻拜杜国忠夫妇为父母,施天文得“赐进士”,与柳氏大团圆结局。原剧是个彻头彻尾的“清官戏”,杜国忠抓住“真凶”,还柳氏清白,并且代替施天文不贞的母亲,成就大团圆的完美结局。1956年响应国家扩大上演剧目的号召,仙游县对这部戏进行了改编。最初未脱窠臼,仍保留杜国忠“清官”身份。剧中施佾生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柳氏,于是杜国忠就和洪如海与施佾生双双展开斗争,最后施佾生服毒自杀,柳氏得以不死,清官杜国忠取得了胜利。改编后出现了不少问题,既然是暴露封建阶级的罪恶,为何还要维持杜国忠的清官形象,经过三年修改,终于把杜国忠改成一个“坚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效忠皇上的官”{21}。
传统戏曲往往以“大团圆”作结,《团圆之后》反其道而行,从“大团圆”写起,开场就是“三喜临门”:儿子施佾生“鳌头独占又成婚”,寡母叶氏苦尽甘来,被赐贞节牌坊。然而,喜庆中却隐藏着不安的因素,叶氏得知儿子为自己请旨旌表,表现不悦;而来拜访的杜国忠得知施佾生“身世”——八个月即出生,颇为注意。叶氏为保护儿子,决定和情人郑司成分手。二人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本来真心相爱,叶氏被父兄逼迫嫁到施家时已经怀孕,不久丈夫就死了。可是婆母不准改嫁,她只得生下儿子独自抚养。郑司成对叶氏真心不改,帮助她抚养儿子。然而二人私会场景被儿媳柳氏撞见,叶氏羞愧自杀。柳氏为保婆婆名节不肯说出真相,叶氏的哥哥叶庆丁诬陷柳氏逼死了婆婆,跑去报官。柳氏将实情告诉丈夫后,施佾生求柳氏“三保”——替母亲保名节、替祖上保家风,替为夫保性命,劝柳氏先伏法认罪,自己想办法保护她。
之后,叶庆丁告到按司洪如海处,抱怨知县杜国忠“太不明”,“徇私不断案”。于是“执法无私”的清官洪如海立刻将柳氏提来,亲自审问。他断案的方式就是严刑逼供,还把柳氏的父兄都叫来问罪,柳氏见父兄受株连很痛苦,但仍信守诺言,不肯说出实情。整个审讯的过程可谓最集中展现矛盾与痛苦的过程。从1959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以下简称“上海文艺”版)与1959年11月号《剧本》上发表的版本(以下简称《剧本》版)来看,施佾生的形象变化较大。“上海文艺”版中施佾生没有如和柳氏说好的那样搭救她,为了躲避嫌疑,眼睁睁看妻子受刑,还两次暗示柳氏承认罪行。舅舅叶庆丁劝他不必念这“三日夫妻”的恩情,施佾生立刻对柳氏“变脸”,痛骂妻子一通后,也只是悄悄补一句:“吾妻真可怜!”“上海文艺”版中施佾生表现得过于冷漠、懦弱,不仅不令人同情,反而让人感到灵魂卑琐、自私可恨。在稍后发表的《剧本》版中,施佾生在人格、性格上被塑造得更善良真实,写出其在“救与不救”间的挣扎痛苦,一变而为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整场审案戏中,虽然施佾生和柳氏“保”与“不保”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但是“清官”洪如海在审讯中表现出的暴戾武断,让人们将矛盾逐渐转嫁到了洪如海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清官”杜国忠再次登场。施佾生想到杜国忠没有判妻子死刑,或许有意替自己排难,于是求杜国忠帮忙。原来,这个杜国忠并不是真的昏聩,他早就看出柳氏有隐情,认为这是个冤案,现在更觉怀疑。在他和施佾生的对话中,一个打探隐情,一个害怕泄露,一问一防,杜国忠已经表现出“清官”足智多谋的特点,他决定为柳氏“翻案”。要翻案就必须上演一场“忠奸斗”,杜国忠坚持重审,于是洪如海也如周忱对待况钟那样,要求以仕途为抵押。审案过程中,杜国忠表现出高超的手段,终于查清真相。绝望的施佾生带着毒酒来到母亲灵前准备自尽,恰逢郑司成也来悼念叶氏。郑司成得知施佾生已知实情,饮下毒酒后与施佾生父子相认,说出当年不能与叶氏结合的痛苦。施佾生跪地认父,也绝望地饮下毒酒。此时,杜国忠、洪如海上场。真相大白,含冤的柳氏被放出。杜国忠和洪如海要为柳氏请旨建造节孝楼,面对家庭变故而心灰意冷的柳氏撞死在了旌表牌坊前。
《团圆之后》以团圆喜庆为开端,但这不过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在短暂的“乐景”中一步步走向“哀境”。这部戏将《十五贯》中况钟与过于执、周忱的对抗移植到杜国忠与洪如海身上,只是这位“平冤狱”的“清官”杜国忠却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完美诠释了“清官”概念中与“人民性”相对立的一面——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者,残害人民的刽子手。作者表示自己在改编时曾受到《十五贯》的影响,最初把剧本设定为如况钟那样精明的清官,来揭开疑案。作品寄到剧本杂志社,编辑提出杜国忠这个人物的性格以及对事物的态度和全剧风格、人物性格很不统一,“在这个剧中是否适合出现这样面貌的县官是值得研究的”。之后又听取各方意见,作者索性砍去“清官判”主题,将戏集中在“反封建”上,“清官”杜国忠也就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22}
如果说洪如海是传统清官戏中“酷吏”形象,擅长严刑拷打、屈打成招;那么杜国忠显示出的刨根究底、查明冤案则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一早便觉察施家的秘密,不杀柳氏并不是怜惜生命,而是要一网打尽。杜国忠在查案过程中使用了一系列的计谋:刑场上的察言观色,从心理上击破防线,对柳氏和施佾生两边离间,躲在暗处偷听,派人盯梢……这完全是传统“清官戏”中足智多谋的清官形象,然而他越努力探知真相就越让人感到可怕。《团圆之后》让观众置身于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中,如果杜国忠查明真相,那么善良的柳氏就可以免于一死,可是施佾生就犯了欺君之罪,必须去死,重情义的柳氏恐怕也活不下去;如果无法查明真相,柳氏就得去死,而施佾生表示自己也要追随妻子,无论如何都难逃悲剧命运,这就让观众将怨怼情绪全部转嫁到这场悲剧的制造者——洪如海与杜国忠身上:没有酷吏洪如海,柳氏不会被处以极刑;而没有杜国忠,真相不会被查出,施佾生也不会死。从人伦情感角度来看,洪如海与杜国忠逼着施佾生家破人亡,查明真相便不具备正义性。如果说况钟的查案是出于拯救,那么杜国忠则是为了毁灭,他就像法海一样,穿着封建卫道士的“袈裟”破坏人间真情。为了让杜国忠的反面形象更明确、不让主题堕入“好人办坏事”的窠臼,1958年后的改编刻意强调其阴鸷狠毒的性格,由他亲口在向洪如海请求翻案时说出“阴谋”;杜国忠查明真相后,柳氏曾求他放过施佾生,自己愿意顶罪去死,大人又何必多事?杜国忠回答:“本县执法如山,岂容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番秉公执法的话实在是讽刺至极。最后手上沾满鲜血的杜国忠竟然还若无其事地提出要为柳氏请贞节牌坊,足可见其残酷冷血。由对于“为民请命”的“清官”之“清”的颂扬一转而为对于“清官”之“官”的揭露与控诉,从改编目的来看,《团圆之后》与《十五贯》、“海瑞戏”等走了性质不同的两条路。由杜国忠、洪如海的“清”揭示了“清官”之封建卫道、戕害人民的本质,从而达到“反封建”主题的需要。
这个剧并不将矛盾冲突简单设定在官与民之间,而是让成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施佾生及妻子柳氏走上被告席,接受封建制度的审判,这就将矛头指向封建伦理道德对于人的戕害。施佾生、柳氏都深陷人伦道德的冲突中,选择夫妻之爱,就要放弃对母亲尽“孝”;为了保住母亲的“贞节”,就必须指控妻子的“忤逆”;一旦证明母亲的不贞,就造成对皇帝的“不忠”;如果选择为夫家“三保”,就要毁坏自己父亲、家族的名誉……种种道德选择的纠缠中,达成一种就必然损害另一种,并且这种损害是以生命的消逝为代价的。无论是柳氏、施佾生,还是叶氏、郑司成,他们都不是坏人,却要承受悲惨的命运。作为悲剧中心的施佾生至死都没有作出有力的抗争,临终还是执迷不悟,告诉妻子“我是堂堂郑家子,墓碑切勿刻姓施”,要通过“认父”的行为完成对父亲的“孝”。身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施佾生也逃脱不了制度的惩罚,自杀也不能令其真正解脱,无力地发出一点苍白的质疑,然后继续做封建道德的“孝子”,这就将封建制度对人戕害之沉重完全道出。施佾生表现得越无力、越痛苦,人们就会对他所深陷与维护的制度越痛恨,戏曲终了,这个悲剧已经从“清官之恶”的揭露上升到了“制度之恶”的鞭挞。“清官之恶”恶在表层,而“制度之恶”深入骨髓。如果将杜国忠换成《三勘蝴蝶梦》中珍惜生命、通情达理的包待制,悲剧是否就不会发生了?戏中的人物依旧陷于道德选择无法自拔,柳氏只要不说出真相,那么在她的父兄眼中,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她就仍是逼死婆婆的恶妇,其悲剧命运仍然无法获得解脱,她所极力维护的一切终将造成她的陨灭。《团圆之后》站在“清官戏”的反面,投向“反封建”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此时期关于封建伦理道德是否具有“人民性”的讨论。
“反封建”主题的表达,使得《团圆之后》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戏曲曾一度以施佾生自杀作结,不交代柳氏结局,意图“给观众有一个思索的走廊”,然而观众通不过,只好改为仍由柳氏上场,慷慨激昂控诉一番,撞坊而死,忽然来了大雷雨,贞节坊震倒,现出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思索的走廊’和‘光明的尾巴’,观众都不要”。最后只能改为在郑司成、施佾生死后,洪如海、杜国忠要为柳氏建节孝楼,柳氏一头撞死在贞节坊上。{23}从一开始逃避结局,到“化蝶”式的浪漫尾巴,再到白毛女式的控诉结尾,这条反“大团圆”的悲剧之路并不怎么顺畅。如何能够在表现凄凉的同时不失革命浪漫精神,在“社会主义新喜剧”时代,对于悲剧结尾的剧作该如何解释;即便是悲剧,又能否写一群妥协者的悲剧;如何顺应“清官戏”发展,在剧作主题鲜明的同时,得到观众的认可,这些难题都在《团圆之后》的结尾改编过程中暴露出来。从无论悲喜,到控诉后新生,再到彻底的悲剧,这其间作者在民间趣味与主流意识形态间不断权衡、协调。当时有研究者出于保护,指出《团圆之后》的悲剧中蕴藏着讽刺、滑稽的力量,封建势力并不如它所表现的那样强大,相反是虚弱的、可笑的。{24}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结果,1963年在“清官戏”被打为“毒草”后,《团圆之后》被指为“开倒车”,全剧压抑得让观众透不过气来,感受不到一线光明。“恨”是缺乏力量的,缺乏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作为现实主义的悲剧,不仅要给观众无限的回味,还应当或多或少给观众一点鼓舞的力量。更有讨论者指出这个剧表面是反封建的,实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者有意追求西欧文学中那种突兀的情节和悲剧的气氛。{25}
2.《谢瑶环》:“清官之死”的爱情悲剧
此时期另一部著名的“清官戏”悲剧是田汉的《谢瑶环》。20世纪60年代初,田汉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参与了郭沫若话剧《武则天》的修改工作。1961年田汉访谒了昭陵和乾陵,由“载舟之水可覆舟”产生了一些想法,还观看了碗碗腔《女巡按》。这个剧基本保持了清代戏曲家李十三《万福莲》的样貌,以谢瑶环奉旨私访开场,与袁义士造反作结,充满喜剧色彩。田汉看完后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国家这几年有困难,少演造反的戏,剧本不要以反入太湖结束,应让谢瑶环与武三思等斗争不屈;对武则天的态度应该基本肯定,但也要有所批评。把谢瑶环作为坚持均田制的斗士,她的死是有悲壮性的。{26}由此,田汉选择了此时期“清官戏”的主流模式——忠奸斗争模式,不同之处在于“清官之死”的悲剧结局。
从一开始,谢瑶环就清楚这场斗争九死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奠定了悲壮的基调。但是这部戏和《团圆之后》的阴郁压抑不同,它有浪漫舒缓的一面,即谢瑶环与袁行健的爱情部分。伍员庙中,谢瑶环对器宇轩昂的袁行健一见钟情;留袁行健在府中,要与他八拜订交,类似《梁祝》中的“草桥结拜”;袁行健在花园里不小心撞破谢瑶环男扮女装的秘密,二人相爱,男女私会于后花园;谢瑶环的贴身侍女苏鸾仙则是为二人穿针引线的“红娘”;而结局“托梦”一章颇有杜丽娘幽魂入梦之感,传统才子佳人相知相爱的情感模式,给这个原本一开场对立双方就剑拔弩张的“清官戏”,增添了古典韵味,节奏也变得舒缓起来。
然而私订终身于后花园的男女是怎么表达真情的?苏鸾仙劝谢瑶环,快点对袁郎表白心迹。谢瑶环却有诸多顾虑,和传统戏曲中小姐受制于封建礼法而娇羞扭捏不同,她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为政治理想而自我牺牲的准备,爱情固然美好,终究只是政治理想的附丽,这也奠定了爱情悲剧的基调。在听了谢瑶环的“表白”后,袁行健被感动了,从假山后走出,称:“贤弟!愚兄与你情同骨肉,死生与共,祸福同当。”“金兰之好”迅速转化为“儿女私情”,源自共同的政治理想。袁行健与统治阶级关系游移,他原本出身于统治阶级,朝廷于他有杀父之仇,只能远离避祸,在这个过程中与“民”靠近,和农民起义军将领李得才结为好友,后来也是靠私人情谊化解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尽管靠近“民”,袁行健与统治阶级仍有血肉关联,仍不失用世之心,谢瑶环对朝廷的“忠爱之心”令他感动,脱口而出“怀靖怎能不为贤弟效死”,并且告诉谢瑶环,因“自幼慕李药师为人”而取名“怀靖”。从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行健”到仰慕开国名将而得名的“怀靖”,正是行走民间到归顺庙堂的转变,谢瑶环激发了他的用世之心,因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促使爱情迅速萌生直至热烈。这种将爱情拔高的笔法正与孟超让李慧娘看见裴生的瞬间,脱口而出“壮哉少年”而非旧本“美哉少年”异曲同工,谢瑶环与袁行健的爱情也向着“壮”而非“美”的路上走去了。
剧中的爱情线索与忠奸斗争是合而为一的,然而清官谢瑶环在这场忠奸斗争中并不出彩,甚至略显尴尬。她虽手握特权,武则天又赐她尚方宝剑,却救不了自己。身为钦差,武则天并不完全信任她,甚至起念要杀她。谢瑶环来到江南是要解决太湖起义军的问题,缓解朝廷与民间的矛盾,然而她实际上只是斩杀了蔡少炳,杖责武宏。斗争的高潮部分谢瑶环并未参与,而是一方面由龙象乾喊冤,递上血表,解除误会,到武则天、徐有功亲赴现场,苏鸾仙传递遗折完成;另一方面由袁行健去往太湖,化解危机。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谢瑶环》的主题就是对于“载舟之水可覆舟”思想的言说,武则天是“舟”的代表者,袁行健是“水”的象征者;武三思、来俊臣等是水舟关系的破坏者;谢瑶环则是一个努力想让舟稳水静、国泰民安的局面出现的水舟关系协调者,她与另三者发生联系。{27}“清官”谢瑶环在这部剧中只起到调节性作用,甚至缺席斗争。
谢瑶环的死虽是对她所忠诚的事业的献祭,但她的死亡对于斗争影响并不大。“十七年”戏剧中对于“死亡”的描写是非常抽象的,极力淡化肉体消亡所承受的痛苦,着意强调精神的连贯性。英雄的死亡往往发生在类似《拉奥孔》中所描述的在顶点到来前“最富孕育性的顷刻”,在这“顷刻”之后,价值的肯定、理想的弘扬将被推至顶点,一切高尚、激昂、明朗的情感,将跨越死亡的痛苦直达新生。而谢瑶环的死亡时间却并不发生在这样“最富孕育性的顷刻”,甚至她的死亡与斗争的结果间并未建立直接的联系。在最初的手稿里,田汉只是让谢瑶环在酷刑中昏死过去,后来在武则天怀中复活。田汉说:“我每次写戏,总是不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主人公死去,虽则是悲剧,总想让它喜剧结尾。”但是过了半个月,田汉作了修改,“戏剧的悲剧性是由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和她的性格决定的。我还是无法把谢瑶环救活过来,就如武则天无法救活她一样”{28}。“清官之死”在“忠奸斗”线索上匆匆画上句号,清官在其中的调节性功能业已结束,斗争由武则天亲自解决。但是,“清官之死”的悲剧效果自此才真正展开,剧末谢瑶环亡魂入梦,对袁行健倾诉生离死别的痛苦。谢瑶环生前作为巡按,牺牲了女性的私人情感,她与袁行健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之上的;如今亡魂入梦,才与丈夫真正建立起了爱情的联系。只是阴阳两隔,袁行健“拜别亡妻把路赶,五湖烟水且盘桓”,曾经的理想与爱情如梦幻泡影,从此他将继续飘零湖海,其间的旷达、悲悯与超脱,真正将“清官之死”的悲剧性节奏持续下去,被评论家指为“神来之笔”,余音袅袅,给人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受。{29}
而“清官之死”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隐喻性,伴随清官在剧中功能的弱化,此时期,对“清官戏”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清官戏”趋于终结。而对于田汉本人来说,“清官之死”也别有意味。新中国“清官戏”的发展历程中,少不了田汉的投入。当初《十五贯》的成功,除了政治因素外,与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的不断奔走,邀请戏曲界知名人士看戏、写文章推荐有直接关系。{30}而田汉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关汉卿》中就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清官意识的、“为民请命”的关汉卿形象,到《谢瑶环》中“清官之死”,“清官戏”这种艺术形式终于宣告终结,这与田汉的行为恰恰是呼应起来的。
《团圆之后》与《谢瑶环》相对旧剧来说,都经历了从喜剧到悲剧的转变,但是主题与思路迥然不同。《团圆之后》在多次修改后,反转“清官戏”传统模式,达到了对于“官”之本质的暴露与批判,这也是“清官戏”写作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阶级性问题。反映制度之恶,同时借助人伦情感的复杂纠葛,控诉邪恶对善良的戕害。像杜国忠这种破坏人伦亲情的官员,在人们眼中是不会被视为“清官”的,实际上这个“反清官戏”已经转变为善恶较量,以此激起人们对于打着“清官”名义的无耻之徒的痛恨。从创作思路来说,“反封建”主题并不新鲜,其主要创新在于对传统“清官戏”思路的转变,从结果和情绪来看,都是悲剧的,但是这个剧同时又让人感到诗性的匮乏。《谢瑶环》写了“清官之死”的悲剧,但是清官的“死”却割裂了她生前艰难进行的忠奸斗争,死亡并未导向“崇高”,悲伤的余韵在爱情的破灭中得以延续,可以说爱情的幻灭为忠奸斗争主题披上一层浪漫感伤的轻纱,在意想不到之处增添了悲剧的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清官戏”本身。在“悲剧消亡论”的20世纪60年代,这两部悲剧作品最终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整体来看,“清官戏”在“十七年”文学中并不发达,但是影响力却不容小觑。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阶级论角度看,“清官”作为封建官僚之一种,被抽象地排除在新中国文艺之外。但“清官”意识在此时期的戏剧创作中一直都存在。田汉的《关汉卿》就有“清官”的影子,关汉卿和朱廉秀聊天时,说到自己曾写过《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期待着现实中能有一个包待制那样的青天出现。自嘲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专会开薄荷、甘草的大夫”,表达了“羞为甘草剂”的想法。而王著的“为万民除害”,以及百姓共同签名为关汉卿求情的“万民禀”,都是典型的“清官”元素。丁西林《孟丽君》后半部分的忠奸斗争也有“清官戏”特质。传统“清官”在大、小传统中有不同的想象与构造方式,大传统强调“忠君”,小传统更切近“人情”,二者实则基于同样的伦理道德基础,因而那些广为流传的“清官戏”在二者间可以做到轻松转化。循着这样的模式,改编戏中也利用“情”的因素,特别是基于民间立场的“情”的表述来强调清官之动人。如《生死牌》中黄伯贤父女对于王志坚父女基于道义、恩情之上的为民做主与舍生取义;《谢瑶环》中谢瑶环与袁行健基于政治理想之上的爱情的吟咏;《团圆之后》则反其道而行,清官毁灭了夫妻、父子等人伦情感,而引发人们的反思与愤怒。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民间性情感的表达,掩盖了“清官”本身的阶级性问题,但随着“清官戏”的推广与规范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仍卷土重来,在后来的批判中被指为“阶级融合论”。
作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清官戏”被施以当代政治性的改编与解读。封建社会里,清官形象作为儒家传统“仁政”思想的人格化,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作为王权主义的内在调节机制发挥作用。{31}之所以选择“清官戏”的表现形式,或许正因为“清官”思想、“清官”情结早已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决定着人们的选择。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将政治与道德绞缠在一起,人们习惯以善恶之辨代替政治立场的判断,而“清官戏”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代表着对于正义、公理的自觉追求,受到观众的喜爱。然而,此时期,“清官戏”的推行,主要是文学对于政治的借力,而非民间兴趣的承载。从《十五贯》到《谢瑶环》,“清官戏”的写作是传统戏曲重新进入当代文化建设方式之一种。《十五贯》开启了“清官戏”的写作,也说明了“清官戏”写作对于政治的依赖性及这种关联建立的偶然性。在《十五贯》写作与解读的错位中,已经隐现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此时期的“清官戏”既是典型的“清官戏”,同时又不断消解着“清官戏”本身,直至“清官之死”的出现,这颇富隐喻性的结局,为“十七年”“清官戏”的写作画上了一个句号。
注释:
{1}陈旭:《清官:研究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魏琼:《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③张庚:《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在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13号。
④蒋星煜:《〈十五贯〉改编演出的深远影响》,选自蒋星煜:《蒋星煜文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张庚:《向〈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学习——谈〈十五贯〉的剧本整理》,《剧本》1956年6月号。
⑥巴人:《况钟的笔》,《人民日报》1956年5月6日。
⑦逄先知、金冲及:《〈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百年潮》2003年第12期。
⑧张真:《谈〈十五贯〉的三个人物》,《文艺报》1956年第11号“笔谈昆剧《十五贯》”。
⑨王斐然:《〈十五贯〉给我们的启发》,《文艺报》1956年第11号“笔谈昆剧《十五贯》”。
⑩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十五贯》引起轰动后,擅演“清官戏”的周信芳也想编一出新戏。他以前演过一些“海瑞戏”,但是征求了各方意见后,发现都不适合,只得作罢。直到1959年“海瑞”被大力宣扬后,周信芳才上演了《海瑞上疏》。
{11}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12}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考辨》,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13}马少波:《毛泽东与中国戏曲》,选自马少波:《马少波文集》(第8卷),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14}张占斌、孙建军:《“三家村”沉冤》,三环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5}湖南省戏曲工作室编,刘回春执笔:《生死牌》,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页。
{16}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海瑞上疏》,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17}吴晗:《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1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9}田汉:《读〈团圆之后〉》,《剧本》1959年第11月号。
{20}《团圆之后》经过多次修改,存在好几个版本,除特别指出外,本文皆以发表在《剧本》1959年11月号上的版本进行考察。
{21}{23} 仙游县编剧小组改编:《团圆之后·前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第6页。
{22}陈仁鉴:《关于“团圆之后”的写作与修改问题》,《热风》1962年第4期。
{24}郭汉城:《〈团圆之后〉的出色成就》,《剧本》1959年11月号。
{25}《关于〈团圆之后〉的争论》,《戏剧报》1963年第12期。
{26}田汉:《田汉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27}田本相、吴卫民、宋宝珍:《田汉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4页。
{28}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
{29}伊兵:《漫话〈谢瑶环〉》,《戏剧报》1962年第3期。
{30}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00—601页。
{3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基地项目“江南文化和江苏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JD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唐蕾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