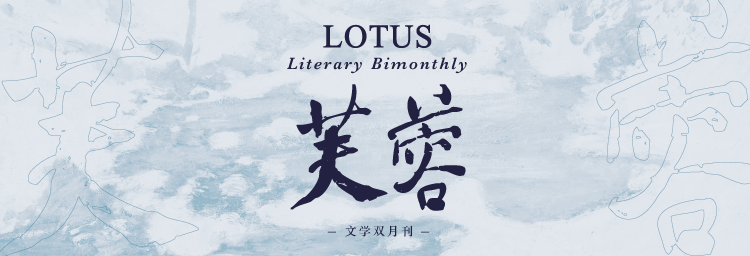

伯祖父一家(短篇小说)
文/王平
我的伯祖父,是我祖父同父异母的哥哥。小时候见过(六七岁吧),印象不深了,只记得那时候他已经中了风,整天躺在床上,由伯奶奶跟三伯奶奶轮流侍候着。
这样一说,谁都便可推测我的伯祖父可能有三个老婆。
没错,他是有过三个老婆。但“伯奶奶”这个称谓有些语焉不详。她究竟是大伯奶奶,还是二伯奶奶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伯奶奶就是二伯奶奶。大伯奶奶我们从没见过,她去世得早,二伯奶奶便俨然成了正房。她不乐意别人再叫她二伯奶奶。但改叫她大伯奶奶,毕竟也不合适。因此,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谁的意思,我们都叫她伯奶奶了。
但三伯奶奶并未顺理成章成为二伯奶奶,我们一直叫她作三伯奶奶。至于为什么,从没问过。我们对此没有兴趣,小孩子才不管这些事呢。
我只见过大伯奶奶唯一的女儿。一个高度近视眼,毕业于周南女中,我们叫她作表姑妈。那时恐怕有四十好几了,后来在倒脱靴也住过几年。
伯祖父不太喜欢表姑妈。因为他想先有个儿子。结果大伯奶奶来不及再生个儿子,自己却先死了。慢慢地,表姑妈长大了。她喜欢读书,还会作诗填词,却有个败象。与人说话,还没开口,鼻子却先一“吭”一“吭”的,眼睛还一眨一眨。伯祖父尤其不喜欢。哪怕《唐诗三百首》可以背出来两百首也不算数。
所以伯奶奶也跟着有些嫌弃表姑妈。
伯祖父那时住在长沙北门外潮宗街的当铺巷子里,自己有一栋陈年老屋。在“文夕大火”中居然幸免于难,可算个奇迹。事后有人分析,乃风火墙砌得高的缘故,似乎有几分道理。至于当铺巷子里有没有当铺,我已毫无印象,但这栋老屋子的大致格局还记得清楚,因为父母带我们去的次数较多。房间都是木板壁,呈烟褐色。大门不宽,进去要上几级台阶,又下几级台阶。然后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有环形走廊将四周连接起来。天井两厢的左首有三间房,一间是伯祖父的书房,另一间是伯祖父的卧室,还有一间做什么用的,不知道。右首是堂屋,堂屋两侧各有一明一暗两间正房。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各占一边。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分庭抗礼的意思。堂屋正面右侧有张小门,通厨房,厨房后面还有个小天井,且里面果真有一口井。伯奶奶后面的那间房也有张门可以通厨房和天井。
最有特点的是那口大水缸,嵌在厨房朝天井的那堵墙中间,一半在屋外一半在屋内。这样从井里扯上来的水,转身便可直接倒进水缸,不必费力提进厨房里去。
三伯奶奶后面那间房却不能通天井,没有门,只开了扇小窗户。
这多少显现了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地位的差异吧。
忘了说了,堂屋挨正面墙壁还有一个既宽且高的神龛,分好几层。中间有个慈眉善目的大菩萨。除此外,每层都有一排小门,每个里头都装了一尊小菩萨,样子却很凶恶,雕得活灵活现。
有一回,我搭张板凳偷偷爬上去,拿出来两尊小菩萨在地上玩,遭伯奶奶发现,逼着我对神龛磕了两个响头。
伯祖父的名字叫王时润,祖父的名字叫王时泽。合起来则是“润泽”二字,看来我的曾祖父还会起名字。但曾祖父本人叫什么名字,我哪里还记得。只见过祖父晚年在他的一份简历里提及过,曾祖父去过四川打箭炉(现今康定)游幕多年,从湖南走着去的,“脚都走肿”。以至只好走走停停,中间还在哪里教了大半年蒙馆,赚了些许盘缠。这样想来,曾祖父先前恐怕也是个不得志的穷秀才吧。
打箭炉,这个地名无端引起我好多遐想。
但伯祖父读书总算是读出来了。他真的很会读书,记性尤其好。他与祖父都在日本留过学。祖父先后在东京商船学校、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学海军,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同盟会,意图推翻清朝,还跟秋瑾结为姐弟。伯祖父与其弟不同,他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学,有书呆子气。只顾埋头做学问,不关心时政。我听说过当年伯祖父的一桩轶事。说他们兄弟俩同在日本留学时,有次祖父硬拖着哥哥去参加一次留学生聚会,主持者乃梁启超。梁氏听人说过伯祖父博闻强识,便提了几个法学方面生僻且刁钻的问题,说是请教,其实是想叫他难堪。不料伯祖父镇定自若,引经据典,将答案倒背如流,令梁启超大为折服。
伯祖父回国后做过不少事情。当过检察官和法官什么的,在南京民国法政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清华大学教过法律,最后做了湖南大学的法学系教授,与中文系主任杨树达交情颇深。1949年后,杨树达任湖南省文史馆馆长,伯祖父是首批文史馆馆员。他的专业虽为法学,但对于古代典籍的校勘、注疏等亦颇有研究。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到了他的一本著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叫《周秦名家三子校诠》,当然属于冷门得不能再冷门的书。不过其中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还是听说过的。
我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八五品,原价三角四,现价二十元。翻了几页,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
既然留过东洋,还学的法学,伯祖父应该算个新派人物吧,可是未见得。他非得想生个儿子(这恐怕也是他先后找了三个老婆的主要原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他眼里,所谓“后”,必定得是儿子,女儿算不得数的。他对自己唯一的女儿不无冷漠,便可佐证。以致后来,伯祖父竟然与伯奶奶达成默契,做出一桩颇为不堪的荒唐事来。这件事是多年后三伯奶奶当作私房话告诉我姑妈(我父亲的姐姐)的,姑妈管不住嘴,于是我母亲又知道了。但幸而就此止步,仅家里少数几个人知晓,并未扩散到外头去。
先得说说伯奶奶。虽说伯祖父宠她,却有一个无法释怀的心病。与大伯奶奶比,伯奶奶连女儿也生不出。她索性没有生育能力。但这种事,谁又预先能够料想得到呢。伯祖父当时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伯奶奶既年轻,又漂亮。可惜年轻漂亮当不得饭吃,没有生就是没有生。伯祖父徒唤奈何。幸亏伯奶奶自有手段,虽说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将伯祖父及大伯奶奶侍候得一是一二是二。伯祖父原本在家里是个除了应酬就是看书,其他百事不管的人,加之耳朵根子又软,伯奶奶更将他哄得团团转。待大伯奶奶一死,这个家,实际上就由她操弄了。
那么三伯奶奶呢?三伯奶奶先前并不是三伯奶奶,只是伯祖父家里的一个未曾裹过脚的大脚丫头。人老实,做事不太麻利,加之一双大脚,也屡遭伯奶奶嫌弃,因为她自己拥有一双地道的三寸金莲。但三伯奶奶很会做鞋,鞋底尤其纳得好。且能纳出不少图案与花样,如二龙戏珠、丹凤朝阳之类。伯祖父只穿她做的鞋,说同升和的鞋都没有她做的鞋舒服。这个我相信,因为小时候去当铺巷子,还见过三伯奶奶纳鞋底。坐在一张竹靠背椅上,膝间卡一个两尺余高的A形木夹,将鞋底紧紧夹住,先用锥子钻一个眼,再将穿了麻线的针引进去,咝啦咝啦地扯,最后将麻线在锥柄上绕两圈,使劲勒紧。鞋底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纳出来的,既细密又均匀。
但三伯奶奶从来不做裹脚女人穿的小鞋。伯奶奶曾经想要她做两双,她说不会做,其实未必。伯奶奶心里应当明白这不过是托词,却拿她没有办法。谁叫你嫌她那双大脚哩。
不过三伯奶奶除了那双大脚之外,竟慢慢出落至姑娘模样了。且与伯奶奶莲步轻移,弱不禁风之风格迥然不同,三伯奶奶的体态自然且健康。乃至年逾五十的伯祖父暗地里动了心思,想娶这个丫头,并不在意她那双大脚。只是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这好理解。《红楼梦》里头,大老爷贾赦想打丫头鸳鸯的主意尚且未遂,何况伯祖父呢。
但精明的伯奶奶哪里看不出来?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伯奶奶索性打算成全此事。一则可以讨好伯祖父,二则自信有能力掌控三伯奶奶。于是某日,伯奶奶跟伯祖父挑明说了,当然正中伯祖父的下怀。便又去跟三伯奶奶说。不料好说歹说,这个三伯奶奶竟不肯从,还说想要回宁乡老家。伯奶奶倒有点急了。平时家里一应杂事加气力活,皆可支使三伯奶奶,如果真说走便走了,劳累的还是自己。
于是伯奶奶使了个计谋。她择个日子做了几样好吃的菜,先将伯祖父劝了个半醉,又将三伯奶奶赚进屋里(先前的三伯奶奶只能在厨房里吃饭),顺手将房门反锁了。这个暗示太过显然,伯祖父何尝不知。其时正是夏天傍晚,两个人都穿得少,加之酒能乱性,伯祖父二话不说,将“酒杯一搁,蒲扇一扔”(这是三伯奶奶的原话),竟然将三伯奶奶摁在了床上。谁知她还有几分气力,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起来。伯奶奶在门外听见,有些慌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开房门,径直奔到床前,死死摁住三伯奶奶的两条腿。伯祖父这才将她如此这般了。
固然,酒醒之后的伯祖父为自己的行径懊悔不已,却覆水难收,只能听之任之了。当然更不能责怪伯奶奶,要怪只能怪自己。
幸而三伯奶奶哭了一通,想想便就算了。原先说要回去,也就说说而已。十二岁从乡下到当铺巷子做丫头,已然习惯了这种谈不上好,也未见得坏的日子。且既然失了身,人就索性只好给他了。何况伯祖父是主人,先前待她毕竟不薄,从未给她过脸色。更没有什么老爷派头,得空还教她认几个字。
三伯奶奶原本是个文盲,后来识得几个字了,还是得感激伯祖父。我还听她神神道道背过《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什么的。这《千字文》,当然也是伯祖父教她的。
生米就这样煮成了熟饭。一个比伯祖父小三十多岁的丫头便正式成了三伯奶奶。且伯奶奶还俨然以大房自居,为之操办了一番,当然场合谈不上有多么热闹。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祖父与伯祖父亦有类似之处。祖父也娶了个二房,原本是老世伯郭先生家里的丫头,也是个大脚。这丫头身世很惨,三四岁时乡下发大水,家人全被冲散,生死不明。万幸自己坐在一只脚盆里逃过一劫(应该是父母情急之下将她放进去的吧),被人辗转卖了几次,最后被郭先生收养了,连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直到成人,个子仍又矮又小,于是郭家人索性唤她叫“矮子”。但矮子做事却很伶俐,人也规矩,从不多嘴,也有几分姿色,倒惹人喜欢。后来郭先生将她送给了祖父。祖父得知身世,不忍将她再当作丫头,便收她做了妾。且以“矮子”的谐音替她取了个名,叫“蔼慈”,加上王姓,叫王蔼慈。“矮子”从此才有名有姓了,晚辈们管她叫作蔼婆。蔼婆跟祖父生了个女儿,即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的细姑妈。但祖父与伯祖父不同,思想开明得很,儿子女儿都喜欢,甚至更喜欢女儿。我的大姑妈年轻时找了个登徒子,很早便离了婚。祖父甚为怜惜,让大姑妈伴随他生活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
这个蔼婆,我们晚辈都喜欢她,且觉得祖父的名字取得真好,她确实是一位既和蔼又慈祥的老人,小时候我们跟她比跟祖母还亲近。祖母去世得也早,是个大家闺秀,印象中却不苟言笑,家里人都有些怕她。多年后祖父去世,蔼婆便被细姑妈接走了,先居唐山,后居北京。晚年很幸福,女儿女婿孙子孙女都孝顺她,高龄九十五岁无疾而终。
所以虽说伯祖父与祖父都娶了个丫头做小的,但我觉得性质还是有所不同。且这两位丫头后来的命运,也截然不同。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命吧。
再说三伯奶奶,居然很快就跟伯祖父生了个儿子出来。伯奶奶掐指一算,竟然就是那天晚上做的“好事”,便不无醋意地说,真是一只碰不得的鸡婆!但伯祖父不免大喜过望。虽然谈不上老年得子,毕竟也五十出头了啊。
伯祖父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王仲通。伯祖父算是有学问的人,起名“仲通”,肯定有讲究,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就不必提它。但王仲通从小性格不好,很敏感,听不得一句重话。且不喜欢读书。伯祖父要他背古书,他死活不背。伯祖父很生气,举起戒尺要打。其实只是做样子,哪里舍得打?他竟然把书撕了。伯祖父终究奈他不何,只得顿足,说,孺子不可教也,孺子不可教也!
为什么会这样呢,没人说得出所以然。要知道,王仲通在家里可是备受宠爱的呀。伯祖父宠,生母三伯奶奶当然宠,伯奶奶呢,尽管看三伯奶奶不顺眼,可她宠王仲通,确乎也是真的,甚至比伯祖父、三伯奶奶更宠。有时伯祖父刚举起戒尺,她便一把夺走。有时三伯奶奶刚开口骂(当然是假骂),她必定将王仲通揽至身后,厉声制止,且说,莫以为你生了他就了不起!
所以人世间,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王仲通也慢慢长大了,性格仍无什么变化。虽说不再像小时候那么任性,但仍然内向,沉默寡言。倒是喜欢看书了。却不是看古书,而是看新书。伯祖父也只能由他去。伯祖父这点倒开明。一屋子书,随他去看。
伯祖父家里的书确实多,而且门类杂。一屋子的书架重重叠叠摆满了,还有十几个篾箱笼子,也装得满满的。线装书多,铅印书也多。善本、珍本或许有,但不会多。伯祖父并无藏书癖好,买得来主要是读。
王仲通跟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即我的表姑妈,也不太讲话。尽管表姑妈经常让着他。表姑妈比他大十几岁,比三伯奶奶却小不了多少。二十岁时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子弟,姓朱,叫朱春江,据说是赫赫有名的朱家花园里的人。朱春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喜欢读表姑妈作的诗。
至于朱镕基亦是朱家花园里的后人,这是数十年后外人才知晓的事情。
朱春江这里那里做了些事,后来做了山东东阿县的县长。此县盛产驴胶,表姑妈还寄回过长沙不少,且叮嘱伯祖父及三伯奶奶分些给众亲戚,却只字不提伯奶奶。多年后母亲忆及过此事,竟然在柜子深处还翻出一包,牛皮纸上头贴着一张已然发暗的红纸,赫然印着“东阿阿胶”几个老宋体字。母亲说这阿胶越存越好。我当时则想,再存也不能像这样存上几十年吧,谁还会吃它呢?
有人说表姑妈嫁得好,结果后来很糟糕。县长太太没当两年,县长大人却犯了桩命案。一日,朱县长正在蹲茅坑,外头忽然有个人影一闪。朱县长疑是“共匪”搞暗杀,鬼使神差,撅起屁股抬手一枪。旋即出去一看,地上躺着一个人,却是他的勤务兵,遭他一枪击中脑门。人命关天,这事态便严重了,且找不到可以推责的理由。不过我这位朱姑爹倒痛快,说事已至此,无力回天,任凭上司发落,并赔偿给家属一大笔钱。态度既然如此之好,又毕竟属于误杀,加之还有点人脉,上头并未严办,仅打算记大过一次,降职留用。但朱姑爹自己却引咎辞职了。
夫妇俩卷铺盖离开了东阿县衙,县长大人转眼之间成了一介布衣。幸而稍有家底,在聊城还置了处房产。便借此开了一家茶叶店,得过且过地过小日子,哪里晓得未过几年,朱姑爹因有一笔血债,被人民政府押解回了东阿,判处了死刑。
表姑妈在山东再无任何亲人,家产也遭全部籍没。仅有的儿子刚去天津读大学(后来见过两次,我们叫他小铁哥),她只得孑然一身回到长沙。结婚十几年,表姑妈如一只苍蝇满世界转了一圈,又原复回到潮宗街当铺巷子,跟伯祖父住在一起了。
其时应该是1951年吧。回到家里,表姑妈才听三伯奶奶说起,她的弟弟王仲通,四年前竟然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了。走之前压了张纸条在伯祖父的书桌上,上面写着:
我不喜欢这个家,你们不要找我。
名都未留。
后来伯祖父多方托人打听,仅仅知道王仲通可能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但也不知具体下落。何况当时内战频仍,哪里找得到他的踪迹?
三伯奶奶边说边哭,还说,你父亲不肯让我告诉你。表姑妈听了,也哭了。她这才明白,这几年父亲为什么苍老得这般快。
我想,后来伯祖父中风,与此事也不无关系吧。所幸中风以后,伯奶奶跟三伯奶奶侍候得很不错。伯祖父个子高大,在床上瘫了五六年,翻个身还得靠两个人帮忙。但伯祖父病得干干净净,大小便一次也不曾拉在床上,更未生过褥疮,委实不容易。
大约是个1958年还是1959年,伯祖父去世了,活了八十二岁。
操办丧事时,伯奶奶几乎把三伯奶奶撇在了一边。她打算尽可能办得热闹些,祖父也随她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亦有凄凉之处,伯祖父灵前无孝子。唯一的儿子王仲通出走多年杳无音信,乃至连披麻戴孝、捧灵牌子的人都没有一个。想到此处,伯奶奶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大哭起来。我母亲只好边劝边说,表姑妈可以代替呀。未料伯奶奶立马将眼泪一收,仿佛刚才从未哭过,厉声说道,那怎么可以?她是女儿,嫁过人的,绝不能代替。甚至连表姑妈在天津千里迢迢赶回来吊孝的儿子,嫌他是外孙,不姓王姓朱,也不能代替的。最后伯奶奶做出一副情急智生的样子,跟我父母说,要将我的二哥过继给她做孙子,没有孝子也有孝孙,披麻戴孝举灵牌子便名正言顺了,这样方能告慰伯祖父的在天之灵。弄了半天,伯奶奶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不过这又何尝不可呢,父母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伯奶奶立马像煞有介事地抬眼望天,泪眼婆娑边哭边笑地告诉“先生”,要他放心(她从来称伯祖父叫“先生”,三伯奶奶也跟她这么叫),王家还是有后了诸如此类一堆话。而当时我最纳闷的是,伯奶奶的眼泪怎么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灵堂设在堂屋里,四周挂满了祭幛、花圈和挽联。天井里,鞭炮屑子足有几寸厚。出殡时,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又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偏不去擦。两个人一人跪一边,抚棺号啕。感觉她们在一个劲地比赛,看哪个哭得更厉害。鼻涕悬至两三寸长,却任凭它们惊心动魄地悠悠晃晃,都不去擦。但依小时候的我来看,三伯奶奶还是哭不过伯奶奶,何况她的鼻涕,无论如何没有伯奶奶的鼻涕长哩。
出丧时,我又做了件惹伯奶奶生气的事。我二哥非常听话,叫他跪就跪,叫他拜就拜。披麻也好戴孝也好,听凭大人摆布。我呢,却死活不愿穿那身白色的孝服,腰间还要扎根麻绳,更不愿下跪,觉得很丢面子。伯奶奶生气,母亲只好揍了我几下,我便大哭。最后双方只好达成妥协,我仅仅戴了顶白帽子,未穿孝服。
那一年二哥十岁,我八岁。
丧事办完之后,伯奶奶生怕母亲变卦,钉钉子还要敷脚,催着我母亲去办过继手续,且将二哥的户口从城南路派出所迁到了北正街派出所。这样,二哥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伯奶奶的孙子。
伯祖父去世后,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必然会分家。好像伯祖父生前只有口头遗嘱,并不正式,也不详细。这样一来,祖父便必得出面了。伯奶奶跟三伯奶奶从来对祖父颇为忌惮,祖父在她们面前不怒自威。但祖父还是将一碗水基本上端平了,两个人至少在表面上没表示异议。其时祖父自己年事已高,她们分家后,也不便再去当铺巷子了。
那么表姑妈呢,她刚好在一所民办中学谋了一份教职,教语文。薪水刚刚够用,但学校给她安排了一间小房子,一个人住着。晚上批批作业,看看书,偶尔写两首旧体诗抒抒胸臆,还算安心。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天津铁路局当技术员,也常有信来。表姑妈执意不肯要他负担生活费,要他存些钱准备成家。每个星期回当铺巷子一次,看看父亲,待个把钟头,饭都无意吃一餐。父亲去世后,仅搬了自己喜欢的一堆书走了,其他一概不要,干干脆脆。她不愿为这些可怜的遗产劳神。
祖父沉吟半晌,说,也好,也好。
分家最重要的是分房子。但事实上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已各占两间,不宜再动,只是将伯祖父那边的三间房分别租给了两户人家,此外每户含一间杂屋做厨房。每月房租由伯奶奶与三伯奶奶平分,轮流收取。至于所谓细软,本来就所剩无几,伯祖父早担心他死后两个老婆会生龃龉,多年来已陆陆续续分给她们了,谁多谁少,外人一概不知。然而还是有不少日常用品及一应杂物,当时哪里可能分得那么细,便留下了一堆潜在的纷争。
只是可惜了剩下满屋子的古旧书籍(表姑妈挑走的不及百分之一),以及一些字画。祖父原本想设法处理一下,却无精力。晚辈亦无一人关心,乃至后来全部散佚,不知所终。
祖父仍叮嘱父母得空要去当铺巷子看看。祖父从来不说去伯祖父家,只说去当铺巷子。每次去,我们都是在伯奶奶屋里吃饭,只是去三伯奶奶屋坐坐。若我到她房间里去玩玩,她还是高兴。经常给我一块扯麻糖吃,或者几根灯芯糕。
伯奶奶却不许二哥到三伯奶奶屋里去。
两三年后,祖父突发脑出血,在倒脱靴去世了。伯奶奶闻讯,颠一双小脚从当铺巷子赶来。长沙俗语云: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伯奶奶从北门赶到南门,距离当然一样。她未及喘息,刚进大门,扑通一声跪地便叩,然后居然双膝跪行,跪过院子,跪上麻石台阶,跪进堂屋,就这样跪行至祖父床前,放声大哭。搞得一众亲戚手足无措,费好大力气才将她扶起来。
这个印象委实太深刻,乃至三伯奶奶来没来,我都毫无印象了。
在祖父的葬礼上,我再次被大人要求披麻戴孝,终于不得不从。但只是苦着一副脸,实在哭不出来。这便又让伯奶奶不高兴了。指责我没心没肺,祖父去世一滴眼泪不流,先前死了一只鸡崽子倒哭得伤心伤意。她这样一说我觉得很委屈,反而哭了。因为那只小鸡崽子是我精心喂养的,还指望它长大了下蛋呢。不料有次被邻居不小心一脚踩死了,肠子都流了出来。我把它捧在手心,觉得太可怜,遂大哭了一场。还在院子里的玉兰花树下挖了个坑,将它埋了。然而,祖父的去世对一个懵懂孩子而言,固然有些许难过,但实在难得产生过分的悲伤吧。可是那时候,大人哪里有什么闲心,对小孩子的这些心思予以理解跟同情呢?
那时正值1962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二哥作为过继给伯奶奶的孙子,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当铺巷子看她。这倒是二哥非常乐意的一件事,且每次都带着我去。我当然也高兴。因为在伯奶奶那里可以玩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有饱饭吃,有好菜吃。话说回来,伯奶奶还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见到我,总要摸摸我的脑壳说,造孽啊 ,就是一根豆芽菜,长得!
再叹口气。
伯奶奶每次给我和二哥一人蒸一大钵硬饭,也给自己蒸一小钵。平时,她每天只以稀饭度日。菜为一荤一素一汤。当铺巷子离通泰街菜市场很近,伯奶奶每次必定要称二两肉,买两片泰字香干(长沙的香干,南有德茂隆,号称“德”字香干,香干正反有个“德”字;北有吴恒泰,号称“泰”字香干,香干正反面有个“泰”字)。泰字香干炒肉,炒白菜薹子或红菜薹子,再加一碗酸菜豆腐脑汤,撒少许葱花。真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美味啊。
伯奶奶给二哥夹菜,也给我夹菜。但总少不了要唠叨一句,你哥哥带得亲,你带不亲!
我听了虽然不高兴,但菜照样吃。
还有不爽的便是,日子苦到那般田地,在伯奶奶家里吃饭竟然还要用公筷,不能用勺子舀汤直接朝嘴里送,要另外用只小碗盛上,嚼东西不许吧唧嘴,更不能用筷子指着人说话(我有这个毛病),总而言之名堂多。
伯奶奶多少还有些私房钱。三伯奶奶也应该有。若无意外,两个人细水长流,加上房租,各过各的日子,总归还是过得下去的吧。但自从祖父去世后,她们两人的矛盾日趋公开,最终竟然发展到彼此动手的地步。且三伯奶奶也越来越占上风。原因无他,既然双方都没了忌惮,便但凭实力说话了。毫无疑问,伯奶奶年长,且一双小脚,动嘴巴可能难分伯仲,若动手,显然不敌比她小十几岁的大脚三伯奶奶。且到后来,三伯奶奶越来越会审时度势了。每回吵架,只要有人围观,她的口头禅必定是:你怕这还是旧社会,还让你骑在我头上屙屎!
这样一来,三伯奶奶便获得了街坊邻舍道义上的同情甚或支持。伯奶奶被空前孤立了。我们两兄弟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唯一的期盼,便是每个星期天二哥与我去当铺巷子看她。
二哥的确也比我懂事。有次看见伯奶奶眼角有一块瘀青,便问怎么了。伯奶奶说,还不是你们三伯奶奶搞的!二哥再细问。伯奶奶说,本来每人分两根晒衣竹篙,一根粗的一根细的。她的放堂屋她那边,我的放堂屋我这边。可是趁我不注意,她把我那根粗的换成了细的。我问她怎么换我的竹篙,她说本来就是这样分的。我要去换回来,她竟然将我一推,被神龛子角碰了个包。二哥当时亦有十三四岁了,起身便要去找三伯奶奶换竹篙,却被伯奶奶拖了回来。伯奶奶说算了算了,你也搞她不赢。只指望你长大,替我争口气。我死了,你替我披麻戴孝,气死这个有崽冇得人送终的!
这个崽,当然指的是王仲通。王仲通,你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记起来,我小时候,三伯奶奶给我看过一张王仲通小时候的照片。大约正在上初中吧,穿着一套咔叽军装,头戴船形帽,皮鞋短裤长筒袜,系一条领巾(那领巾跟红领巾的系法不同),腰间皮带处还悬挂着一捆卷得紧紧的绳子。三伯奶奶告诉我,这是你仲通表叔参加童子军时拍的照片。
挺胸凹肚,成丁字步站着。好神气的样子。
而我小时候,早没有什么童子军,变成少年先锋队了。
没过几年,父亲被单位隔离反省。一家人全都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当铺巷子看伯奶奶跟三伯奶奶?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伯奶奶突然自杀了。
消息是潮宗街街道革委会派人来通知的。母亲大吃一惊,连忙带着二哥和我赶了过去。但见伯奶奶躺在一张门板上,放在堂屋中间,身上盖了张白床单。三伯奶奶缩着身子站在旁边,不作一句声,脸色苍白得跟那张床单差不多 。一个革委会的女的指着门板对母亲说,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另一个革委会的男的说,天气热,赶紧找人拖到火葬场去,不然会臭啊!
母亲麻起胆子问那个女的,伯奶奶犯了什么罪?革委会的女的将嘴巴朝三伯奶奶一努,你去问她。母亲不解,便也看了三伯奶奶一眼,却见三伯奶奶惊恐地朝后一退,嘴唇发抖,说不出一个字来。
真相很快大白。
就在头天上午,街道革委会要伯奶奶跟三伯奶奶交代历史问题。结果高压之下,三伯奶奶为了“反戈一击有功”,竟然一五一十,当场揭发了三十多年前的那桩隐私,说她本来只是个丫头,是伯奶奶配合“人面兽心”的伯祖父强暴了她,并胁迫她做了小老婆,还生了一个崽。这确乎是铁的事实,伯奶奶一下子瘫软在地,哪里还有脸面见人?
尸体是租户丘嫂子最先发现的,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来绘声绘色,很夸张的样子。说先天半夜里醒来,迷迷糊糊听到小天井那边扑通一声,却未介意。隔天早上她去井边扯水洗衣,却见一双三寸绣花鞋整整齐齐搁在井台边上,便觉得有些不对劲。继而发现井里有一具尸体,半浮在水面上,吓得不要命地叫起来,连吊桶子都掉到井里去了。
母亲费了好大力气才联系上火葬场,让火葬场派来了一辆汽车。却因当铺巷子太窄开不进来,只得停在潮宗街上。进来了两个人,将伯奶奶装进一只铁匣子里,抬了便走。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二哥,突然间大哭起来。
他哪里还有机会替伯奶奶披麻戴孝?
而在我们闻讯去当铺巷子之前,三伯奶奶已将伯奶奶屋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母亲打开那个雕花大衣柜里头的小抽屉,两只蟑螂忽地蹿出,吓了她一跳。
此后好多年,我们便再也不曾去过当铺巷子。
直到二哥当了十年知青后顶职回城,有回几个少时好友邀他去坡子街的爱群茶馆喝茶,吃包子。有个人忽然说,你三伯奶奶这两年不见人了啊。先前经常在茶馆里碰见她,挽只破篮子,这张桌子底下那张桌子底下捡烟蒂子,卷喇叭筒抽。这话触动了二哥,便一个人去了一趟当铺巷子。
这才知道,三伯奶奶死去好几年了。有两年还找了个伴,是个在潮宗街菜场门口摆摊子,修锁配钥匙的老乡。这个老乡骗光了她残余的一点钱财,一去不返。三伯奶奶从此沦为低保户,精神也有点失常了。
母亲听说后,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怔了大半天。饭都烧煳了。
再后来我也去过一次当铺巷子。时间记得很清楚,即举办奥运会的那年,2008年。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定居深圳多年的长沙人,听说搞房地产开发,将一些古老街巷拆去不少,便抽空回来了一趟,要我专门陪她两天,拍些照片留作资料,还说“不然会来不及了”。既然如此,我只得奉陪。她不愧是搞专业的,扛了两架尼康单反,长枪短炮,还背了个大摄影包。我难免怜香惜玉,便将摄影包替她背上,还真有蛮沉。
第一天去的哪里不必提,第二天去的哪里也不必提,第三天去的潮宗街。因为这是一条古老的、保存尚且完整的麻石街道。东起北正街,西止沿江大道,即原来的潮宗门,老长沙城西边的城门之一。我们左穿右插,还走完了梓园、九如里、连升街、楠木厅、三贵街等老街巷。
最后带她去了当铺巷子。
巷子几无变化,只是更显破旧了。两边石灰剥落的墙壁上,隔不了几步,便红通通刷了好大一个“拆”字。伯祖父的老屋在巷子的最里头,十七号。摄影师朋友在门口替我照了张相。上了几级麻石台阶,又下了几级麻石台阶,便站到了天井里。那天天气极好。阳光斜射下来,照在天井里满竹篙满竹篙飘扬的衣服上,五颜六色。我忽然想,这几根竹篙,还是多年前伯奶奶跟三伯奶奶争夺过的那几根竹篙吗?
堂屋里,那个既宽且高、分好几层的神龛子,包括里头大大细细的菩萨,当然没有了。
整个大屋显得杂乱不堪,恐怕住了六七户人家。忽然听见有张门吱呀一响,回头,从原来伯奶奶住的那间屋里走出一位中年妇人,用狐疑的眼光打量我们,问我们找哪个。我连忙说不找哪个,只是看看。那妇人说,一栋破屋子,有什么看头,要拆了。我说晓得晓得。这栋屋子小时候我经常来。那妇人说这就怪了,早几年也有个老头子找了进来,说他小时候住在这里。
我一愣,说,真的?那妇人乜我一眼,这也骗你?那老头子又瘦又高,西装革履。一脑壳白头发,朝后背梳得整整齐齐,油抹泠光,像个归国华侨。也没讲什么话,这里看一下那里觑一下,待了几分钟就走了。
不必说了。这个人,肯定是王仲通。

王平,长沙人。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编审,《书屋》杂志创始人之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雨打风吹去》《王平小说》(甲种本/乙种本)。
来源:《芙蓉》
作者:王平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