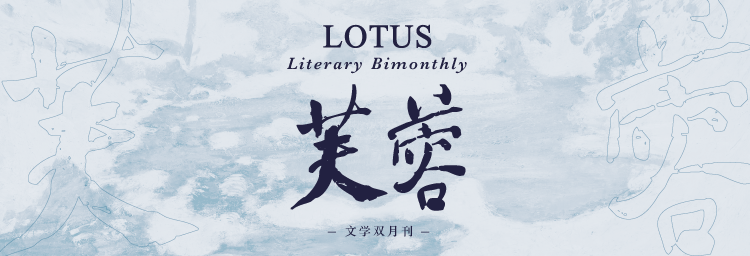

芳草长堤(短篇小说)
文/盛可以
回乡必须横穿小镇。沿大米加工厂林立,建筑树木蒙灰的无名公路东行,在酒厂高耸的烟囱下拐弯入镇,立刻跌进城乡接合部的嘈杂旋涡。过去的牛车变成了汽车摩托,车忙人乱,而街道依旧狭窄,要从这片混乱无序的路况中脱身并不轻松,堵死是常有的事。她庆幸自己早就离开了这里,托一次失败爱情的福,或者说,感激那个抛弃她的人,要不然她就是此刻混乱市井中的某一个中年妇女,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对身后的喇叭声充耳不闻。
仿如泥潭中跋涉,车终于从古桥上盲眼算命先生和他们的信徒中挤出来,驶入两排低层建筑剪裁出来的麻石街。这条街上有旅社、杂货铺、理发店、五香米粉加工、梧桐掩映下红漆剥落的老戏院,一个屋顶十字架,门口香炉青烟袅袅,像教堂也像寺庙的宗教场所,全程两三分钟便到了小镇的尽头,迎面是豁然开朗的乡村景色,芳草长堤,岸边杨柳飘拂,河水波光粼粼。她黯然远走,对镇上这些自童年便熟悉的事物不再正眼打量,心底的秘密被多年的人生经验深裹,连她自己都触摸不到了。
麻石街上竖起一道又一道“沉痛悼念”的充气拱门,一望就知是桩有排场的丧事,离世的无疑是个有福之人。她瞥了一眼死者的名字,目光如夜驰的车灯从路牌上一晃而过,没留下任何印象。车在戏院那一段堵住了。灵堂和花圈占了半边街,看唱孝歌的人填满了剩下的空地。
戏曲衰落,戏院荒废,唱戏的人改为在丧葬活动中唱孝歌谋生。红漆剥落的戏院大门提醒她关于时间和历史,多年前在戏院那只被攥握过的手似乎还留着他的余温,梧桐树下的初吻带着薄荷的清香,驳接乡镇的芳草长堤充满恋爱的欢愉。
一个男人出来疏散人群,引导她开车跟进。人潮如水在车尾后重新弥合。她放下车窗,向这位热心肠道谢,这人忽然满脸波纹荡漾地叫出了她的学名,这个看起来挺老的人说他们是初中同学,她顿时沧海桑田。他接着提到另一个人,顺着他的手指,她的目光落在充气拱门上那个被沉痛悼念的名字——季羡军。她也不是立刻想起此人是谁,就像乒乓球落到地板上,蹦跳几下,滚了一段之后停下来,她才猛然一惊。
她后来也感到奇怪,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却连主角的名字都模糊了。也许她铭记的不是爱,而是事。一个老土的故事,城乡差别之下的爱情夭折,对刚出社会的她迎头一击,失败的凛凛寒意伴随,使她时刻清醒。
她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轻雾如烟的早晨,在故事与杂草同生的芳草长堤,面对一艘停泊江心的挖沙船——他曾经带她在这船上过了一夜。他弟弟季慕军在挖沙厂当监工,一手安排的,弟弟始终和哥哥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抵抗父母对乡下姑娘的偏见,为他和她的爱情赢得了生存空间。平心而论,那是她人生中最为浪漫深情的夜晚,十八岁,朗月当头,江水幽幽,她成为他的女人。
分手十分突然。此前她还一起照顾他住院的弟弟,弟弟的脑袋上划了条口子,身上多处是伤,因怕父母担心隐瞒了病情。她从家里带来适合病人吃的食物,喂汤喂药,晚上睡折叠床,他则挤在病床上。他们的爱情在这里更深更稳。如果那天一大早他向她求婚,她绝不会感到惊讶。
但情况正好相反。他似乎通宵没睡,神情异常严肃。他没有解释那只吊在脖子下打了石膏缠满纱布的手是怎么回事,那五根专职撰写政府文件报告的手指,裹得像襁褓中的婴儿只露出五个脸蛋尖。他是个文弱书生。她知道它们的温柔和美。但它们完全没有触摸她的想法。他本人也没拐弯抹角,开门见山且神色哀伤地说,他准备和城里的一个大学生结婚了。
后面来车按喇叭,她往边上挪车,错挂了倒挡,差点撞到后车。急促的敲锣打鼓声鞭炮声,以及震耳欲聋的铳响掩护了她的尴尬。她虽没想起眼前这个人的名字,但记得他和季慕军都是被镇学校刷掉的差生,降级转到乡中学重读,他们都不爱学习,带着街上男孩的痞气整蛊闯祸。她和他们只同学一年,几乎没什么交流。
“季慕军可真是舍得为他哥哥花钱。这不,戏院包场连演三天呢。”他意犹未尽,移步到车窗前继续聊这桩非凡的丧事,好像他和她之间没有相隔三十年,好像她是专门来采访这件事的。
与初恋情人在三十年以后的街头偶遇,却是阴阳两隔。她不想了解一桩丧事办得如何热闹铺张,一身寿衣如何价值不菲,棺材是什么名贵木材,她想的是他五十出头,因何早死,有无孝顺的子女,此生过得是否如意?在他后来的婚姻生活里,他是否偶尔会想起她,有没有试过打听她的下落,有没有愧疚当年的残酷无情?
她脑海里又浮现那时的芳草长堤,河水蜿蜒直到天际,本应是良辰美景。当他说要和一个出身城市的女大学生结婚时,黑鸟从树林中惊叫飞起。此后静寂。轻雾比之前浓了几分。他强调身份和教育,这两样珍贵的事物,都是她缺少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权力阻碍别人获得更好的,任何性质的胁迫都是不道德的,自尊心拒绝她表达爱意。这时候说什么都已无足轻重。他神色凄然,伸出一只手,想要一个分手的拥抱。她拒绝了这种充满怜悯与伪善的温情,在泪水涌出眼眶前,迅速转身离开了他。
“季慕军组织了一个同学群,但谁也联系不上你,这次回来了,一定要聚一聚。跟你说吧,慕军发了大财,自己就有好几艘挖沙船,手下工人一大堆。咱们聚会吃喝玩乐他全管。所以啊,过上好生活并不见得要上大学,好多上了大学的也并不怎么样……”
她从不曾和故人联络叙旧,各有各的生存哲学,没有共同语言,价值观又相差太远,没有辩论的基础,此刻她也没有想到反驳。也许是为了吸引她加入群组,展示留在故土的人,如何用不着走南闯北照样过得有滋有味,老同学始终在聊季慕军如何发迹,以及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如何热气腾腾,完全不知道她心的某部分已被迅速冻僵。
不应该是这样的场景。她无数次想象和他在这条街上偶遇,他必定听说过她读了博士,有了大城市的户口,他也必然知道他在她命运中的作用,他会笑说他功不可没。他可能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变成平庸虚胖的中年男人,生活安稳无风无浪。当他们像老朋友似的坐下来,他不可避免地说起自己的儿孙,这也是大多数人这辈子最拿得出手的东西。她也不会问起那个城里的女大学生,虽说当年她很想知道这个女程咬金的来龙去脉。
孝歌声哀恸哽咽。高音唢呐刺穿悲伤的氛围,多种乐器奏响,仿佛风雨大作。
他要和她结婚。当他收拾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时,她是这么想的。那座房子在长堤边,白墙青瓦,有一个由四根木柱撑起的气派堂屋,门口一眼塘,水面开满睡莲,蜻蜓飞舞。水边有芦苇、白茅,遍地鸭跖草、茼麻、莎草、苍耳、蓟,含羞果、辣蓼草……似乎所有乡间的花朵都来了,带着喜庆。知了像监工在树上声声催促。金银花藤顺着老槐树爬到半空中落下清香。他们像夫妻一样打扫庭院,除尘拔草。她感到大自然以及沉稳静默的祖屋都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祝福他们,期待它们的新主人。
她喜欢祖屋的样子,还说要是镇上都是这种白墙青瓦的风格,一定会很好看。他笑着说,以前屋里头住的可都是些走路不利索的小脚女人,像他奶奶那样。不过他也承认旧建筑的美,好的东西应该有传承。
收拾完祖屋,他们满身尘土,翻过长堤跳进河里游泳。她潜水。他看她很久没浮上来,急得大喊她的名字。夕阳沉落时,他们像两条鱼在水中交尾。河水涌动。潮涨潮退。多年后山河依旧,它们会证明他是爱过她的,像她爱他一样纯粹。
也就是在他们打扫完祖屋的第二天,他弟弟受伤住院,他们在医院陪伴病人,放下了祖屋的事。他弟弟长相跟他相反,皮肤黝黑,身材偏矮,像个壮实的乡下人,好武爱斗,受时下流行的香港武打片影响,时不时惹点麻烦事,但都靠他的关系摆平了。他对弟弟近乎宠溺。有人说这是他为了弥补弟弟在父母那里受到的冷落。不过应是无稽之谈,季羡军是那种温柔敦厚、心地良善的人,兄弟俩深厚的感情是打小建立起来的。
她心中最柔美的时刻是和他的相识。那年冬天特别冷,降下了五十年来最猛烈的雪,积雪高堆,只看得见长堤上行走的半截人影。那一年全乡开始办理身份证,作为村里少有的高中生,她被选中做身份信息搜集登记工作,最后又被安排到乡政府誊抄身份资料。将近一个月时间每天早出晚归,顶着刺骨河风沿长堤往返,时而风雪交加,大雪如飞蝶乱扑,不论天气如何恶劣,她心里始终流淌着温暖黏稠的蜜——去的路上想到有他在,回时想到明天又能见到他——他负责全乡身份信息采集工作,他们就这么认识的。她在他的办公室誊抄资料,这些手写体将作为永久的存档与依据。他教她很多,嘱咐她认真仔细,尤其是出生日期,千万不能出错。他也给她泡茶,往炉子里添炭。不知不觉,他这些简单的日常行为渐渐蕴藏了别的含义。一天下班时分,北风咆哮癫狂,天色漆黑,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他留下她,将她安置在办公室,从食堂打来晚饭,两个人一起吃。讨论工作,烤火说闲话。火苗舞动。偶尔迸散火星。夜渐渐滑向深海。心跳声覆盖了外面的喧嚣。呼吸如雪静静地下。下半夜风平浪静。她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没回宿舍休息,为她守着炉火。天就那么亮了。
“我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老同学摆出了长谈的架势,“就拿慕军他哥哥来说吧,读了大学,有公职,朝九晚五,都没干出点眉目来,人就进了监狱……一待二十年,出来没享几年福,人就没了。书不是白念了吗?”
这短短几分钟是她生命中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关于他这几十年的空白,被一个个惊人的消息填补,漫长的光阴在讲述者嘴边飞逝。她没有像舞台剧中的女主角那样闻言惊愕,反倒表情麻木,两眼呆直。头几年她曾经等待他的消息,盼他千方百计找到她,联络她,关心她的情绪和生活,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做出某种解释。要找到她并不难,她的父母绝对不会对他隐瞒她的电话号码。但他从不曾寻找她,他将她忘得很彻底,他的无情使她更加发愤图强。
“为什么进了监狱?”就像对陌生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她让老同学坐到副座,关上车窗开足冷气,与其说是为了让他在舒适的环境中讲得更加精彩,不如说她是掩饰内心的波澜起伏。他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犯罪?犯的什么罪?原来他多年来杳无音信是因为身陷囹圄?二十年牢狱,她一次也没去探望过他,她才是那个真正无情的人啊。她甚至都没问他的手如何受的伤,扭头就走,且拒绝了他最后的拥抱——他单臂所环抱的虚空刺痛了此刻的她——如果不是只顾着骄傲的自尊心,她一定能察觉到那天的分手隐藏着某种蹊跷,他眼神里异样的忧伤,他欲言又止的凝重……往事忽然清晰如镜,她开始自责起来。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啊!我也是过了好一阵才知道的。”老同学从兜里摸出烟盒,手指敲击烟盒底部,一根烟像命运之签冒出头来。她不抽烟,本是摆手谢绝,却又仿佛要查看命签般,伸手接过这支烟。老同学替她点火,她像是怕他忘了似的,又问了一遍那个人犯的什么罪。
此时街上一阵骚动。车窗被急迫地敲响,来者催促老同学处理事情,那边都乱套了。作为本次丧葬委员会的主任,老同学负责所有的调度安排,他对完成一桩圆满的丧事满怀热情。但他仿佛卖关子似的没有立即回答她,反倒说起即将到来的同学聚会,相当认真地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起身离开,在车门外转过身俯下头来低声说道:
“他啊,杀了一个人。”
她在车里默默地抽那支不知其味的烟。老同学带来的消息像一颗颗石子,绞磨着她的脏腑。爱过一个杀人犯——她顿觉毛骨悚然。他为什么杀人?被杀的是谁?他是怎么下手的,割喉,砍颈,刺心脏,钝器锤击?她仿佛看到他脸上溅满鲜血,跨过死者的尸体离开现场,径直走到她的面前。
她有点慌神,手误碰到什么地方,雨刮器忽然快速工作,发出吱吱的摩擦声。她扔掉烟,启动汽车缓缓离开,从反光镜看到忙乱喧哗的葬礼现场渐渐后退,风吹动充气拱门,他的名字轻轻摇晃,仿佛在挥手道别。
她感觉方向盘变得沉重,车轮也似乎陷入泥泞。
车驶出小镇,进入芳草长堤。河水已经混浊。一艘挖沙船在河心工作。她看到了多年前的那对年轻恋人,听见江水在船底呢喃。女孩早已面目全非,而那个年轻的文弱书生,此刻正躺在一个上等的楠木棺材中,长长的白皙的杀过人的双手温柔相叠,搁在恋人深深嵌埋过的胸膛,那颗因为爱情而怦怦跳动的心脏停止了运动。
曾经像教徒进入教堂那样虔诚热爱过的人,是个杀人犯。不,这不是真的,那双温柔的手只拿得起一支笔、一张纸,只捏得起她的头发、她的外套,它们绝不会去碰任何凶器,没有哪双手比它们更加温和理性。
车仿佛是自己停下来的,正好是他们打扫完祖屋后下河游泳的地方。她记得这个河湾的弧度。他们的脚印已被野草覆盖。歪脖子柳树被虫蚁蛀空了心,一半枯死,一半鲜活。她放下车窗,河风灌涌进来,肺叶舒展。她望着水波层层推进的河面,听到他叫她的名字,她潜水的时间太久,他的呼唤饱含着深情和急切。
“他啊,杀了一个人。”
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她推迟返城,参加她并不感兴趣的初中同学聚会。她的加盟,使聚会提高了规格,季慕军包下了河边最美的小酒楼。一窗美景,河水橘黄。情景大致和她预想的一样,三十多年前的同学,尽是些陌生的面孔,眼皮浮肿,身体变形,他们情绪热烈,大声谈笑,质朴到近乎粗野。她进来使气氛有短暂拘谨,甚至警惕,最终很快熟络起来。她总算认出了几个原先关系稍近的,同时感觉时间的残忍。同学们早都离开了乡村,在镇里做小生意,在市里和省里有着或好或坏的工作,也有几个因病离世或意外身亡的,过去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也都作古了。
这些事刚说了个开头,季慕军到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和他哥哥那么神似。她眼圈顿时红了。
他扎扎实实地拥抱她,她感觉到这里头的千言万语。
他身体不太利索,稍晚她会知道,这与三十多年前那次受伤住院有关。
聚会没什么主题。聚的次数多了,旧早叙完,只剩下吃吃喝喝,男的拼酒,女的助兴。因为有新人加入,大家又重新回顾当年,谁偷窥了谁的情书,谁暗恋皮肤白净的学习委员,谁考试作弊被老师逮住……季慕军始终在抽烟,失去兄长的伤感在脸上隐约闪现。在街上遇到的那位老同学负责聚会的气氛与热度,稍有冷场,他就提议谁干杯酒,谁唱支山歌,谁来段花鼓戏,掀起一轮轮小高潮。这样闹腾一阵,在座的自动分成小团体,有的聊儿孙,有的谈生意,有的已经醉态毕露。这表示聚会成功,酒足饭饱,散场后关系比较亲密的几个,会去足浴中心泡脚醒酒,聚会到这里才算真正结束。
季慕军引她来到露台,这是她不曾领略的小镇风貌,河边的迷人景致让她颇为惊讶,河水倒映着青白建筑,显出异样的美好与繁华。那条重点保护的文化古街,其建筑均变成了白墙青瓦木格窗,风格像她和他哥哥一起打扫过的祖屋。季慕军将哥哥加为股东,兄弟俩各占公司一半的股份,他刑满释放时,都不知道自己已是家财万贯。出来后一直独自住在祖屋里,镇上这些建筑风格,也是他捐钱改造的。
“他是因为我出的事,”季慕军说道,“他不是杀人犯。”
季慕军那天的讲述掺杂了眼泪与悲伤,过多的沉默与停顿,激动时语无伦次,之后仍不断在给她的短信中补充疏漏。他后悔年轻气盛惹下的祸。当年他工作的船与另一艘挖沙船产生纠纷,他是个监工,地盘争夺本不关他的事,但他为老板打抱不平。那时社会有打斗的风气,年轻人为姑娘,为面子,或争一时之气,头破血流并不稀奇。他在打架方面有点名气,谁赢他就能威望升级,因此对方下手狠毒,用板砖和西瓜刀将他打趴了,且公安局里有人,连医药费都不用支付。
“我每次惹事,都是他帮我摆平的。身上裂几道口子,断几根肋骨,像个死人一样在医院躺个把月,他比我更痛心。他要尽哥哥的责任。”季慕军当时是这么说的,“他一个文弱书生,根本不是打架的料,一上场自己先受了伤,后来骨头没接好,手臂一直是弯的,手指头也不那么灵活了。”
她眼前晃动他负伤的形象,那只缠满纱布的坏手吊在脖子下,另一只好手要拥抱她,她一点也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是个杀人犯。
“他没杀人。”季慕军好像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个人自己跌倒了,后脑勺撞在石头上。”
案子背后的社会关系比本案复杂。面对审判,他们无能为力。整个家庭因此崩塌,父亲首先被击垮,半年后积郁离世;母亲努力活着,但也没有撑到儿子出狱的那一天。
说到这些,季慕军有一阵长久的沉默。
他说他欠他们的。他哥哥是如何欢天喜地地收拾祖屋,如何秘密地选定了日子,准备去她家求婚。她几乎马上要成为他的嫂嫂。
“所以,他编出一个女大学生来。他了解你的性格,既刚烈,又柔软。他知道只有这么做,你才会掉头就走……他说,这样对你更好,你面对和承受的,就会简单得多。”
河水将沉默绵延至很远的地方。她感觉到命运的惊涛骇浪。
她不知道什么是简单。车在芳草长堤上低速行驶,她第一次缓慢仔细地观察沿路的一切。坟墓、菜畦和违章民居,分割和破坏了芳草长堤的统一。垂杨老柳所剩无几。她忽然意识到,芳草长堤的秀美,连同她卡在她生命中的那根刺,都已不复存在。她与故乡之间形成了新的秘密关系,这里头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和谐与默契。人还未离乡,她已经开始思念它了。

盛可以,女,20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北妹》《死亡赋格》《道德颂》《水乳》《息壤》《福地》,中短篇小说集《可以书》《取暖运动》《在告别式上》《缺乏经验的世界》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等十余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来源:《芙蓉》
作者:盛可以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