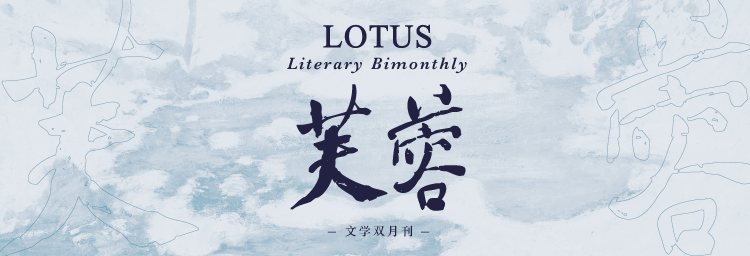

托着小提琴飞起来(短篇小说)
文/罗令源
有人在敲门。不快不慢,不轻不重,比较斯文。我睁开一只眼睛。强烈的光线使我马上又把眼睛闭上了。这是上午还是已经中午了?我怎么还睡在沙发椅上?我浑身汗津津的,嘴唇干裂,口渴得厉害。我拿起手边的威士忌瓶子,把它凑到嘴边。但瓶子已经空了,只有两三滴残酒滴到我嘴里,让我觉得更渴。我放下瓶子,瓶子掉到地上的声音特别响亮,刺激着我的耳膜,好像我把耳朵贴到了地上。我摇了摇脑袋,想把不适感摇掉。
敲门声又响了,也许是听见了瓶子掉地上的声音,所以敲得更坚决了。我把眼睁开一条缝。真要命。怎么看不清墙上的挂钟了?酒精烧坏了我的脑子,现在也要烧坏我的眼睛了?我把戴着手表的手腕举到眼前,这才看见时针指到三了。但我同时也看见,我的手臂有点浮肿,手表带勒进了肉里。我预感到,再喝下去,我会把自己给毁了。我恨自己消沉颓丧,但我就像置身于黑暗的隧道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隧道的尽头。
眼睛渐渐能全部睁开了。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直到模糊的吊灯清晰了一些。敲门人一敲再敲,不肯离去。我只好认输,仰起头,大声问:“谁?”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的声音怎么沙哑得像个风中的破渔网?
“我。”一个文雅的男声。这声音我从来没听过,但很悦耳。
“您是谁?”
“我认识您,您还不认识我。”
我扶着沙发扶手站起来,头重脚轻地朝门口走去。一个穿着灰色西服的漂亮男子出现在我面前。这人很年轻,看上去才十八九岁,蜷曲的头发拢着额头,大大的蓝眼睛好像在远眺,在遐想,看上去有点儿诗人的浪漫气质,身上那笔挺的西服却又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位保险推销员。我想不起来这么一个模特儿似的美男子是怎么认识了我这个三十三岁的平凡女人的。不过,在这样一个注重外表的男子面前,我为自己邋遢的睡相和皱巴巴的连衣裙感到难为情。我侧着头,让披肩发垂下来,半遮住脸部。
“您好。”男子把手伸出来,要跟我握手。他的手像钢琴演奏者的手一样白皙修长。
我装作没看见。“我不认识您。这里没您要找的人。”我边说边关门。
他把手举起来,挡住了正要关上的门。“尊贵的女士,我奉命来见您。”
经过拉小提琴的常年训练,我对声音很敏感。光听他的声音,我觉得他该二十七八岁了,跟我的年龄应该不相上下。可他看上去怎么这么年轻?我困惑地扫了他一眼。“什么事儿?”
“我叫罗兰德·皮雅诺,我奉命……”
“奉谁的命?”
“这个我不能告诉您。但请您放心,我是带着好意来的。春天过去了,夏天降临了阿尔斯特湖。汉堡现在到处都是享受新鲜空气和湖畔美景的人……”
这人果然喜欢像诗人一样借题发挥。但我没力气陪着他站下去了。“您要找的人在隔壁。您往前走吧。”我用肩膀顶门,心想这回一定要把门关上。但对方也在用力,门怎么也关不上。我气呼呼地问:“您到底有什么事?”
“我的任务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复杂,就是陪伴您,一直陪伴到晚上九点。您要不嫌弃,我可以说多种语言给您听,也可以为您唱支歌解解闷。”
这样一个漂亮的男孩要来为我这样一个颓废的女子消愁解闷?这一定是有人在搞恶作剧。那我何不反击一下?我猛地把门大大拉开。陌生男子像没了堤坝的水一样猛冲进来,哐当一声倾泻到地上,发出了金属撞击声。我恍然大悟,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你是个机器人。怪不得你漂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可声音又跟容貌不般配。”迄今为止,我只听说人们在试验让机器人接电话,当的士司机或家庭清洁工,没想到机器人已经开始人模人样地满街跑了。我好奇地盯着他的蓝眼睛,这才发现他果然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他不怎么眨眼,大大的眼睛有点像洋娃娃的眼睛,很容易打动人的心。
“哎哟,哎哟。谢谢您迎接美好使者的热情方式。我对您表示钦佩。”他把自己撞歪了的腿扭正了,佝偻着腰站起来,瘸着腿走了两步,才又站直了,脸上又摆出了迷人的微笑。
嗬,这个机器人还挺幽默。但我还是不想见他。自从我经营了好几年的三人小乐队解体后,我就不想见任何人。我想用酒来湮灭我对乐队的记忆,但我做不到。我只要看着家中的空沙发空椅子,就会想起尼娜和卡斯滕坐在上面和我说说笑笑或拉琴唱歌的情景。
那是六年前,尼娜、卡斯滕和我,我们三人音乐学院毕业后,组建了一个古典音乐小乐队。这个主意是尼娜提出来的。我们读书时就很合得来,毕业后也都跃跃欲试,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有独特风格的音乐表演家。反正大家都还在找工作,找演出机会,于是我们就边做些零碎的小工作,边合伙干起来了。奶奶留给我的房子就在阿尔斯特湖边,带花园,风景优美,所以大家都喜欢到我这里来排练。毕竟我们在音乐学院里接受了多年训练,拉出来的琴声不错,所以没人来抗议我们打扰了宁静。渐渐地,附近的邻居都认识我们了,他们有时还会敲门进来夸奖我们一番,或者打听我们的下一场演出在哪里。我们三人排练完了,就一起做饭,然后端到花园里,一边欣赏阿尔斯特湖,一边吃饭聊天。如果我们刚举办的一场音乐会很成功,我们就会绕着阿尔斯特湖散步,然后在湖滨饭店庆祝一番。不知不觉,尼娜和卡斯滕就跟我的姐姐和弟弟差不多,乐队成了我们三个人的家。我们培育着我们的冒险精神,对艺术的憧憬和热爱、梦想和希望,活得潇洒、快乐、无忧无虑。我们每年都能得到一些演出邀请,时不时还会出国演出,有一家音像出版公司还发行了我们的两张光盘。我们的梦想因此像发面馒头一样蒸发得越来越大。只是我们赚的钱并不多。但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把金钱摆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也许与奶奶给我存了一笔钱有关。
可潇洒了几年后,尼娜想生孩子,想过稳定的生活了。去年年底,她男朋友在柏林找到一份工作。她于是也告别艺术家的流浪生涯,今年年初去柏林安联保险公司当职员了。一份尝试用音乐来解决职员纠纷的时髦工作,听上去像音乐心理疗法。尼娜跟很多人都谈得来,这工作适合她。可她这么甩手一走,我们三人小乐队就解体了。尼娜去柏林前,曾来和我告别。那时她的肚子已经有点鼓起来了。她一脸幸福地想着要做妈妈的日子,谈音乐不像以前那么眉飞色舞了。
接着,卡斯滕找到了在一家音乐学校全职教课的工作,也不怎么跟我联系了。我突然间孤身一人,好不难受。我有时怀疑,我是不是只是半个女人,太缺少魅力,大家才这么弃我而去。但我知道我不该这么想。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但这不意味着我永远找不到。只是伴侣可遇不可求,就像写着我名字的一朵白云,只能等待他有一天会忽然飘进我的天空,然后我就必须赶紧飞上去抱住他,留住他。职业则是永远的爱人,永远等着你的清晨,让你天天去追求,去拥抱,去和它消磨时光,和它一起前行。我鞭策自己去拥抱职业,去寻求一个新的艺术之家。我去看了一些演出,寄出了好几份申请书,也跟几个乐队试了试。可要么音乐风格不般配,要么跟乐手们不是很融洽,到最后总是找不到家的感觉。我渐渐有点灰心。我想我是不是该自己挑大梁,组建自己的团队?但我不像尼娜那样善于组织,而且组织这类事情跟音乐关系不大,让我提不起精神。天空辽阔,路在何方?有一天,我寻了一天,一无所获地回到家,于是给自己倒了杯酒,以便不失眠,不痛苦。后来越喝越多,不知不觉间,把白天黑夜都喝颠倒了。
“我可以帮您把窗帘拉开,屋子里会更舒适些,而且您就能看到阿尔斯特湖。”陌生人的话语把我拉回到现实中。但他没有鲁莽地朝遮住了大半个窗户的深绿色天鹅绒窗帘走去,而是期待地看着我。
我不想要这一堆用人造皮肤包裹起来的铁片来同情我帮助我。但怎样才能把他赶走?他的力气不小,用蛮力是行不通的。可我的脑子被酒精泡酥了,转不过来。我得先跟他说说话,争取时间。
“你说你是专为我而来,而且知道我是谁?”
“知道,”对方胸有成竹地说道,“您叫凯琳·卡佩兰,是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手。去年,这一带的人还经常能听到您的琴声。可惜今年您沉默了。”
我想起所有电信设备供应商都会收集用户数据的报道。“你是不是来收集我的数据的?”
“不是。”
“那你是不是哪个实验室里派来的试验品?”
“也不是。您不觉得我更像一个忠于职守的普通人吗?”
“那你是来变相要钱的吧?先佯说是有人派你来服务,过后就寄账单给我,要求我付款?”
“请放心。我不会给您增加财政负担的。”
真的什么猫腻也没有?那是谁会突然想到要让机器人来陪伴我呢?记得上星期有个医生邻居来看过我,说愿意介绍我去看一位心理医生。我坚辞不要,他才有点尴尬地走了。机器人会不会是他派来的?不太可能。我跟这位邻居一直保持距离,虽然有音乐会的话,他都会来捧场,但他不会不打招呼就派机器人过来的。那是卡斯滕的主意?卡斯滕一向节俭,不会花钱去租赁机器人的。那该是尼娜的主意?尼娜快要临盆,哪有时间顾及我。哎,不想了吧,想多了头疼。我说:“那好吧。既然你是来服务的,那就把我嗜酒的坏习惯接过去吧。”
“嗯——?”罗兰德迟疑着,有点为难的样子,“您想必知道,不管我喝什么,液体又都会从我体内的塑料管里干干净净地流出来。一杯酒可以一喝再喝,而且不会喝醉。这对您没帮助吧。”
“那就没你的事。你下班走人吧。”我朝门口看了一眼,示意他可以出去了。
他站在我的客厅里,纹丝不动:“等一等,也许我可以学学。您知道,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不断进步,而且我可以飞速进步,快得像火箭一样。”
“别逞能,你走吧。再说,我也不喜欢家里有个机器人到处晃悠。”
“那电冰箱您总有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吹开落到眼前的一绺褐发,不解地看着他。
“冰箱说穿了也就是个机器人,只不过没头没脚,只有个大肚子而已。但您也没有把它扔出去呀。您不觉得您相互矛盾吗?”
一听他说到大肚子,我立即就想起了尼娜,想起了我被抛弃后的孤独和失落。哼,这个机器人不就是来显示他的优越性的吗?肯定是我的两个老队友合伙派来了这个机器人,名义上是叫他来陪陪我,实际上是让他来奚落我的落伍,或者让他来游说我,以便我像他们一样,也去做个每天上班拿工薪的职员。我扶着门,口里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我快要站不住了。去地窖帮我拿瓶香槟酒上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您应该接着喝。”他看我脸有愠色,马上满脸堆笑说,“但您说得对,香槟很适合我们俩的初次会晤。”他果然朝门外走去。
我跟着他来到外面。罗兰德像个熟悉我房子的人,径直朝设在房子侧面的地窖门走去。可就这么八九步路,太阳就把我晒得抬不起头来。今天该有二十八九摄氏度吧。我出汗,心慌,怕晕倒,放慢了脚步。我抱怨太阳太毒辣,好不容易来到地窖门前,手有点哆嗦地掏出钥匙给他开了门,看着他顺着楼梯往下走去。不一会儿,他拿着一瓶法国波茉莉香槟酒回来了。我接过沉甸甸的酒瓶,说:“干得不错,再去拿一瓶汝纳特香槟吧。”
他看着我,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点点头,转身又消失在光线暗淡的梯道里。我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我拉上门,立即轻轻锁上。两分钟后,他来到门边,发现门锁上了,开始打门:“开门,卡佩兰女士。”
“你就待在里面吧。这就是我派给你的任务。你帮我看好地窖,别让人偷了我的酒,也别放我进去拿酒。你该下班的时候,我就放你出来,让你回去。”我故意晃荡钥匙,弄出一片毫不让步的响声。罗兰德不再说话。
我回到房里,坐到我舒适的沙发椅上,休息片刻。机器人来打扰前,我就睡在沙发椅上。但这么一折腾,现在是肯定睡不着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好像一只发怒的斗牛犬,让我心慌气短。我热了一碗两天前做的土豆粥,配着刚从地窖里取来的波茉莉香槟,一起灌到肚子里去了,这才感觉好了不少。
我竖起耳朵倾听,周围一片寂静。原来这个机器人也是个懒虫,并不真的想工作。估计他正坐在台阶上靠着门打盹呢。我这么想着,就感觉到睡觉的美妙,身不由己地就在沙发上斜躺下来,慵懒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已经快六点了。天空不像先前亮得像金黄的火焰。但我头痛欲裂,身体好像被人肢解过了一回。费了好大力气,我才站起来,把用过的汤盆端到厨房里。厨房的窗户开着,窗户下面就是地窖门。我的鼻子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酒香,好像有人用我喜欢的酒调制了鸡尾酒。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轻微的哼唱声,好像有个男子蒙在被子底下唱歌。歌声有点沙哑,但很抒情,唱的是意大利歌曲《纤小又脆弱》。我忍不住侧耳倾听。
“纤小又脆弱,你看上去就像我,但我做错了更多。你在我身边,这么纤小,不管脆弱与否,但最终你比我强很多。……”
歌声像一只温润的手,抚摸着我孤寂的心,让我感动。我走出房门,轻轻打开地窖门,蹑手蹑脚顺着台阶往下走。歌声现在更清晰更动听了。我发现,罗兰德比较成熟的嗓音唱这首歌还挺合适。是喝酒使他的声音也带上了一点沙哑,还是他在模仿唱响这首歌的意大利歌手Drupi?正是这一丝沙哑,让歌词好像在叙说自己的故事,给人回味无穷的感觉。我思索着来到酒窖前,可眼前的一幕把我气得几乎昏倒。我的脚无意中碰倒了地上的一个空瓶子,这个瓶子又碰倒了旁边的空瓶子,弄得地上瓶子乱滚,发出一片叮叮当当的响声。歌声戛然而止。
“天哪,我的酒窖!你把我的收藏全毁了。你是不是疯了?”我扶着空空如也的放酒的木架子,尖叫起来。
“真的吗?我只是按照您的指示,尝试着把您的酒瘾接收过来。我相信已经接收了百分之六十了。”罗兰德的声音好像在梦游,忽高忽低地飘浮在空中。一股浓郁的酒香也洋溢在空中。就在离我两三步的地方,罗兰德脱光了衣服,挤坐在一个老旧的红色婴儿塑料澡盆里,眼神迷离恍惚。他的身材修长雅致,人造皮肤在微弱的光线中显得柔软且富有弹性,人斜躺在澡盆里,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慵懒地把酒香四溢的暗红色液体浇到胸脯上,给自己洗澡。他的头往后仰着,眼睛半闭着,好像一会儿就要开始吟诗。他高雅的姿态让我想起青年时代的歌德。可他的两腿间只有光滑的皮肤,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怜的机器人,只有超级大脑,但却没有性生活,也不知道性是何物。我对他的愤怒一瞬间烟消云散。
“你不是说,喝多喝少都没问题,只是一根管子里流上流下而已。怎么喝成这副模样了?”
“所以我才坐在澡盆里,让皮肤来吸收嘛。”他又哼唱起来。
我叹了口气,打断他:“希望你是买了保险的。你倒到澡盆里的液体,大概值2000欧元。你要没买保险,就得自己赔偿了。”
他睁大眼睛,惶恐地看着我。“您怎么这么说呢?是您把我关起来了,是您剥夺了我的自由,强迫我替您喝酒的。”他想站起来,但被澡盆夹住了,出不来。
这机器人还挺会辩嘴。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帮他摁住澡盆,他两手撑在盆沿上,提胸收腹,这才把自己拔出来了。各种酒的混合物跟着泼了一地,我的身上手上也泼到了一些。
这个超级大脑看着澡盆里所剩不多的液体说:“我可以把沐浴露又灌回瓶子里去。但如果这些瓶子还是放在地窖里,那您很容易又喝上瘾。”他的臀部摇来晃去,显然站不稳。我伸手去扶他,但他还是撑不住,一屁股跌坐到地上。他打着哈欠,迷迷糊糊地说:“我浸在澡盆里的部位好像喝醉了。您的酒瘾百分之六十转移到了我身上,我的功劳还是挺大的吧。您看,您现在比我清醒多了。”
我感到一丝内疚,沉思片刻后,说:“不用担心,我会让你又清醒过来,摆脱你所说的百分之六十的醉意。”我从角落里取来一个拖把,把罗兰德扶起来,把拖把的一端顶在他腋窝里,给他做拐杖用。我在另一边撑扶着他,慢慢走出地窖,来到房子里。我在浴室里给他冲了个澡,把酒液都冲洗掉了,然后把他擦干,用一条新的干净的浴巾把他曾浸泡在澡盆里的部位包裹起来,以便浴巾能把慢慢渗透出来的酒液吸收掉。我忽然觉得我是在照料一个少不更事,喜欢做梦的大男孩或大女孩,不,甚至可以说是在照料一个婴儿,把他包裹起来,让他得到温暖和安全感。我把他带到尼娜和卡斯滕都曾用过的客房里,让他睡一会儿。他乖乖地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我给他盖上被子,看着他下巴上隐约可见的黑点,发了一会儿呆。罗兰德的创造者把他设计得惟妙惟肖,好像那下巴就快要长出胡子来了。我明明知道我面前躺着的是一部机器,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同时也是个很迷人的艺术品。
但我这是怎么了?干吗在一个机器人身上费这么多脑筋?记得日本人生产的电子宠物曾风靡亚洲,让有母性本能的女生们忘了学业和家务,后来被学校禁止,不许学生把电子宠物带到学校去。我现在是不是也中了某家机器人生产商的圈套?我警告自己不要沉溺于幻想中,等罗兰德醒了,就送他出门。我轻手轻脚走出来,关上了客房的门。
但我好久没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动作和话语。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脑子也不迟钝了。我又回到地窖,把地上的酒液擦掉,空瓶子扔掉,把地窖打扫干净。好久没做打扫卫生的活,我出了一身大汗。回到房子里,客房还是静悄悄的。我把房子里的空酒瓶也都收拾掉,把窗帘拉开,窗户打开,让新鲜空气驱散屋子里甜腻的酒味。然后,我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脏衣服和罗兰德沾到酒液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洗涤。忙完了这些后,我给自己泡了一壶绿茶,做了盆沙拉。沙拉才刚吃到一半,罗兰德揉着眼睛从客房里出来了,腰间还裹着我给他包扎好的浴巾。我明知他不需要吃喝,但我还是不想把他当机器。
“好些了吗?要不要吃点喝点什么?”
“好多了。谢谢。我喝杯茶吧。”
这机器人还挺能入乡随俗。我起身去厨房给他拿了个茶杯,倒了杯茶给他。他伸着懒腰,坐到桌边。“您这件裙子特别好看。”他说。
我微微笑了笑,再次暗暗佩服罗兰德的创造者的能力。罗兰德的交际能力是无可挑剔的。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喃喃道:“时间过得真快,快八点半了。”
我宽厚地说:“你先喝茶。我去把你的衣服拿来。等你穿好衣服,就可以下班了。”我来到卫生间,把洗好的衣服放到烘干机里烘干。不一会儿,罗兰德就恢复了刚来时的模样。
他感激地看着我,说:“我还没给您唱歌呢。我本来想给您唱歌来着。”
“还有二十来分钟。你想唱,现在还可以唱。”我坐到桌边,继续吃沙拉。
罗兰德抿了一口茶,说:“那我就唱了,您就像坐在放着轻音乐的饭馆里,接着吃。”
他站起来,走到客厅中央大吊灯下,拉平了衣服,先看了我一眼,然后望着窗外的阿尔斯特湖,哼唱起来。他先唱了一首意大利歌《啊,我的太阳》,随后唱了一首德语歌《英俊少年》,接着还唱了一首旋律优美的外文歌。这首歌我曾在哪里听过,可能是在音乐学院读书时,同学唱过。罗兰德告诉我,最后这首歌是中国歌曲《茉莉花》。
“你的语言能力够强的。在语言方面,机器大脑还是比人的大脑厉害。”
“好听吗?”
“好听。”我已把沙拉吃完,半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让他的歌声在我脑子里继续回荡。“你平常都干些什么?”
“完成各种特殊任务。跟今天差不多吧。”
“那你经常给人唱歌解闷?”
“不经常。我只是自己喜欢唱歌。听别人唱一首歌或听到一支好曲子,我就能过耳不忘。”
一个喜欢音乐的机器人?而且还跟我一样,听到一段旋律就能熟记在心?他要是个真人,我们俩就可以合伙组建一个乐队了。我惆怅地低下了头。屋子里静默了一会儿。罗兰德轻声说:“我该走了。”
我忽然十分难受,脖子上开始出汗。天色还早,阿尔斯特湖还亮得扎眼。我不希望他这么早就走,我害怕又一个人面对寂寞和无奈。“请你走前帮我泡一壶茶吧。我喝着你泡的茶,会觉得你还没有走远。”
罗兰德默不作声地朝厨房走去。我像泥雕一样呆坐了几秒,然后迅速站起来,朝卧室走去,把锁在箱子里的小提琴拿了出来。不一会儿,我站在客厅里平常和友人排练时习惯站立的地方,拉起了小提琴。一开始,我的手有点哆嗦,拉出来的声音跳跃不定。但我接着拉。我闭上眼睛,让音乐像云朵一样把我托起来,引向另一个世界。慢慢地,我的手平稳了,拉出来的声音流畅了。舒伯特,门德尔松,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我拉着一首又一首心爱的曲子。我看到罗兰德拿着茶叶罐,来到客厅和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侧耳倾听。我得意地想,我成功了。他会记住我的曲子,下次就可以哼唱更多曲子了。他是个出色的音乐机器人。我要让他更出色,让他拥有更多的音乐细胞。我继续拉,我要把我能拉出来的最美的声音拉给他听,让他像我一样在音乐的世界里忘却时间,待到天黑才走。但慢慢地,我自己也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甚至忘掉了罗兰德。我感觉到自己好像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像飞鹰一样在十万八千里远的上空遨游。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每个音符都贯穿我的身体,好像人与神合成了一体,在美妙的音符间旅行。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我一生的至爱永远是音乐。我为音乐而生,也将为音乐而死。当我拉完最后一曲,满足地垂下疲累的右臂时,我没有马上睁开眼睛,而是让余音继续回旋,让它像螺旋梯一样,把我从十万八千里外的世界里,载回到现实中……
厨房门口传来了孤零零的掌声。接着,窗外也传来了掌声,先只是一两个人,但接着掌声越来越大,好像突然下起了冰雹。我惊奇地睁开眼,看着站在昏暗的厨房门口对着我微笑鼓掌的罗兰德,快步来到窗前。在银灰色的暮色和淡淡的月光中,我看见我的后花园里坐着、站着许多人。隔壁花园里也站着一些人。他们大约有三十个人,全都高举双手,朝我这边鼓掌。有些面孔是我熟悉的邻居,有些我没看见过,可能是正好路过时听见琴声留步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处,阿尔斯特湖平静的湖面在凝重的暮色中像一面大镜子,发出幽幽的,难以捕捉的光芒。我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
有人喊道:“凯琳,非常高兴你又开始拉琴了。我们早就想念你的琴声了。”是我熟悉的一位邻居的声音。我不是在做梦。我面前站着坐着的都是真人。
邻居花园里有人接着说:“我们知道你没有乐队了,但你不会没有听众的。”
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心田,使我眼睛潮湿了。我品尝到了生活的美好。邻居们把我的窗口变成了舞台,把我重又拉回到了舞台上。我的心在欢快地跳舞。没有乐队,不意味着没有舞台,没有出路。没有乐队,我应该也能活下去。我立即进入角色,摆出谢幕时惯用的优美站姿,张开双臂,端庄地微笑着朝观众鞠了一躬:“衷心感谢各位的扶持!”
有人呼喊:“拉得好棒。下周再来一场,好不好?”
马上就有人附和:“对。凯琳,我们都是你的粉丝,渴望你的琴声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天气炎热,你的琴声可以帮助我们抗暑。”
我感动得想大声呼喊,但我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很久没练琴了,今天拉得肯定不够好。感谢大家,把我的练习变成了一场即兴音乐会。为了酬谢各位,我将举办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就像现在这样傍晚时分站在窗口给大家拉琴。我们就叫它后花园音乐会吧。我会像以往一样,在我的大门前及时贴出演出海报,欢迎各位到时光临我的后花园。”
大家用力鼓掌。有人呼喊:“来个加演节目!”接着,呼声和掌声此起彼伏。
我走向始终站在厨房门口阴影中的罗兰德,轻声说:“你来唱《纤小又脆弱》,我用小提琴给你伴奏。”
罗兰德立即摆手往后退。我说:“那好,我问你,你是打算还我擅自洗豪华香槟酒浴花掉的2000欧元,还是想唱一首动听的歌把欠账了结了?”
罗兰德看着我,一脸委屈:“还是唱歌吧。”
“我知道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我朝他赞许地笑了笑,看他有点局促地咬嘴唇,就安慰说,“我们不开灯。你唱得不好,也没人能看清你的面孔。唱砸了也没关系。”我走回到窗口,大声说:“今天有个歌手意外地来访问我。是他用一首歌打动了我,使我重又拉起了小提琴。我为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这首歌也能打动在场的各位。但这位歌手很年轻,有点害羞,请大家不要开灯,不要打手电筒。下面,有请歌手罗兰德为我们演唱意大利歌曲《纤小又脆弱》!”我和观众用掌声把罗兰德请到了窗口。我退到他身后,拉起了小提琴。罗兰德的声音开始时有点紧张,但很快就随着旋律变得舒缓并充满感情:
“你永远找不到你自己的那份真诚。也许你想要,但你说不……你小巧而脆弱……你用充满情感的声音,使我醉入爱河……”
一曲终了,屋里屋外鸦雀无声。接着,窗外涌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和罗兰德手握手,高举手臂向观众致谢。有些人想看看罗兰德,手电筒的光束射过来,罗兰德马上跑到屋里躲起来了。我再次保证本月就会举行一场新的后花园音乐会,而且会和罗兰德联袂表演后,余兴未了的观众才喧哗着慢慢散去。
站得离窗口最近的是住在我斜对面的邻居。他是个中国人,大约四十岁,长着一张饱满的鹅蛋脸。我只知道他姓赵,出门喜欢戴着墨镜。两年前,他买下了我斜对面的一套大房子,搬到了我们这里。邻居们说,他很有钱,是个大公司的老板。他经常以车代步,我难得看见他。但有时他也会在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我们正好碰上的话,就会相互打个招呼,说两句客套话。他的德语带点中国人的口音,但我都能听懂。不过,这也就是我跟他的全部交往了。我有点惊讶他为什么一直站着不走,而且还一直朝我这边看,好像想看到屋里的情景。这跟他平常保持距离的风格迥然不同。
我客气地说:“赵先生,谢谢您也来听我拉琴。我站在屋子里练习,没看见大家来到了花园里。还好大家都喜欢。”
这位神秘的中国富翁走近两步,冲我笑了笑。我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么笑,笑得有点调皮,但更多的是骄傲,好像他刚刚打了个大胜仗,忙着要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我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对我这么亲密过。他说:“何止是喜欢,有人是为之倾倒,把自己都给忘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得我的心怦然一跳,脸上涌起一片红晕。幸好暮色已浓,罗兰德也没有开灯。
我忽然想起来,去年冬天,有一次练琴时,我走到窗口休息一会儿,无意间看见他的窗户大大地开着,好像整幢房子张着耳朵在倾听。平常他的窗户顶多是往上斜开一点点。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窗户开得这么大。我们在圣诞节前后有多个演出,所以那天我练习了很长时间。外面寒风飕飕,但他的窗户始终没有关上。但我练完后不一会儿,窗户就关上了。于是我猜测,房子的主人当时站在房子里默默听我练琴来着。“您今天是凑巧路过我这里,还是因为喜欢欧洲古典音乐,专门过来的?”我问。
“我经常听音乐,喜欢多种多样的音乐。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他跟我聊了起来。
在我身后,罗兰德从厨房里端来一壶茶,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客厅的桌子上,然后又去厨房拿了个茶杯,放到茶壶边。我很高兴他没有开灯。夏夜比冬夜明亮一些,我喜欢夏日影影绰绰的夜景,喜欢眺望暮色中的阿尔斯特湖,幻想连篇。
罗兰德放好茶杯茶壶后,转身来到窗前,轻声对我说:“你要的茶泡好了。”然后,他对着窗外鞠了一躬,说:“对不起,大师,我没有及时回家。任务很艰巨,但我终于完成了所有任务,现在可以跟您一起回去了。”
什么?罗兰德称这个中国人为大师?我打量着窗外一脸诡笑的中国人,然后又打量着毕恭毕敬的罗兰德。忽然,我豁然开朗地大笑起来,朝窗外说:“谢谢您送给我这么美好的一天!”我把手指轻轻贴到嘴唇上,然后把手平伸出窗口,送给窗外的人一个飞吻:“赵先生,我正要品尝优秀生罗兰德给我泡的茶。罗兰德唱了一曲,肯定想喝点茶,润润嗓子。您也想来一杯吗?”

罗令源,20世纪60年代年出生于中国江西,80年代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学士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1990年随丈夫移居柏林,在中国大陆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在德国发表《中国代表团》《向往上海》等6部德文原创长篇小说和《夜游莱茵河》《黄丝绸》等短篇小说集。
来源:《芙蓉》
作者:罗令源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