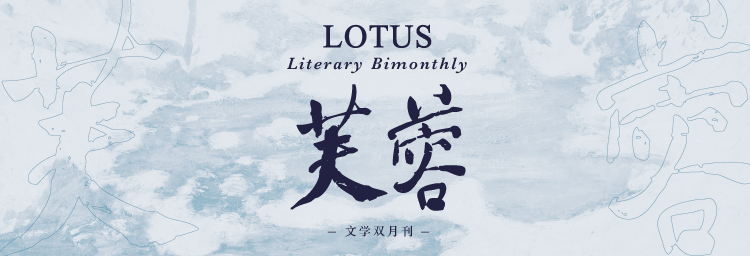

小事端(中篇小说)
文/杨少衡
医生下令:“侧身。翻过去。”
柳宗源遵命,翻身,背对医生,面对墙壁。
“松皮带。脱。”
这是要脱裤子。无须全脱,把皮带松开,裤头纽扣解开,裤头往下褪,后边露半个屁股,前头脱到小腹根部即可,不必再往下暴露,下身物件肢体无论多么隐私,不在该医生及其助手关注之列。
医生很年轻,男性。身边助手却是年轻女子,该女对柳宗源的部分裸露表现出职业性无感,柳宗源也努力无感,毕竟这两位就年齿论只属小辈,女孩不见得比柳宗源的女儿大。此刻医生及其助手面对工作台并排而坐,工作台上有电脑等设备,有一张铁床紧挨工作台靠墙摆着,铺有白床单,供柳宗源躺卧。上这张床除了需要半脱裤子,还需要掀衣服露肚皮,柳宗源自嘲为“半祼”。年轻医生性子急,手脚麻利,柳宗源刚把内衣掀起,裤头褪下,肚皮右侧就感觉一阵凉,是医生给他抹一种液体。据说那玩意儿叫“耦合剂”,水性高分子凝胶,其作用是排出探头与皮肤之间的空气,让探头直接与皮肤接触以完成检查。
这时电话铃响。是座机,摆放于工作台上。
女助手接电话。应了两声,即把电话听筒交给男医生。
“院长。”她说。
年轻医生话不多,似乎懒于言辞,亦像不太情愿,不高兴。他听了好一会儿电话,中间有三次发言,各讲一句:第一句是“是我”,第二句是“正做呢”,第三句是“知道了”。
然后他放了电话,回过身,伸手哗啦哗啦从桌旁纸卷上抽出几圈卫生纸,做一团一把按在柳宗源肚皮上。
“擦掉。”他说。
柳宗源吃了一惊:“完了?”
“有那么快吗?”医生反问,“出去吧。”
“怎么啦?”
一旁女助手说:“大叔,是临时调整。”
这女子比较和气,略有礼貌。她说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只能先暂停,请柳宗源谅解。“不要在这张床上躺了,起来出去吧,在外边等,一会儿叫名字再进来。”她说。
“看我裤子都脱了。”柳宗源说。
“不好意思。”
柳宗源躺在铁床上一动不动,第一个念头就是打个电话。手机就在他的裤口袋里,尽管褪了半个屁股,掏手机也不困难。他知道一个电话可以解决问题,无论天大的事情,这两个年轻人必须让他继续半祼,给他继续涂那种液体,把该他的那些事做完,无论礼貌与否,情愿不情愿。问题是有必要吗?此刻毕竟是他找医生,不是医生找他,支配权在人家手里。在这张床上赖着有什么意思?调侃而言,人家本来就不高兴,再勉为其难,有事给你查没,没事也给你查有,一声都不用吭。
柳宗源决定听命。他从床上坐起来,拿医生按在他肚子上的那团卫生纸擦去刚涂上身的“耦合剂”,感觉该液体稍有点黏,类似某种办公用品,或可戏称为胶水。然后柳宗源把脏纸团扔在床头边垃圾桶里,放下衣服,拉起裤子,下床穿鞋,离开那房间。整个操作期间,房间里静悄悄的,一声没有,两个医生一个看电脑,一个看手机,对柳宗源视而不见,似乎此人就是一张纸片剪出来的。
柳宗源到了门外,门外等候区铁长椅上坐着一二十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基本上人手一机,都低着头各自欣赏,旁若无人。这些人当然不是无所事事跑到这里看手机玩,无一例外都是来做彩超的,柳宗源刚刚离开的房间便是彩超室。彩超很费时间,以柳宗源亲身体验,如今各大医院,无论是省里的还是市里的,彩超室门外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等候者特别多。柳宗源自己今天起个大早,七点半到达,那时医生还未上班,彩超室外已经坐着几长椅排队人员。柳宗源把自己的单子放在护士站排队,在彩超室外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听到广播喊他名字。兴冲冲进门上床,岂料刚把裤子脱下又给“临时调整”,悻悻然回到外头等候,说来挺沮丧。
这时候还能怎么样?等着二进宫吧,耐心点,调整好心态。问题在于感觉不舒服。肚皮上的胶水已经擦掉,那种黏糊糊感还是挥之不去。这类耦合剂据称无毒、无味、对皮肤无刺激且易擦除,只是擦它的卫生纸已经扔进垃圾桶,感觉却还在,可能因为还得再抹一次。
根据常识,一个已经被涂上胶水者又被要求穿上裤子,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于当事医生也属“不可抗力”。会是什么事情呢?很简单:有人要插队。时下各种排队场合插队现象并不罕见,医院在所难免,但是通常不会太过分,哪怕是医生自己的岳父大人需要临时紧急照顾一下,情理上也会让已经躺上床的那位先做完,然后再插入岳父大人,不至于硬生生把人家从床上赶下来。柳宗源有幸享受特殊待遇,一定是不凑巧碰上了一位超岳父大人,特别特别重要的人物插队,立刻就要,不容拖延。从刚才医生接电话的三段发言判断,似乎是医院院长亲自下令,让柳宗源立刻让位,即便已经抹了胶水。一般情况下,彩超室跟急诊手术室略有区别,急诊室常有急难险重,弄不好一场车祸,救护车拉来几个重伤员,其他病号可能得先让手术床,救命优先。彩超室这边有那么急吗?莫非插队进入的该重要人物就要死了?
柳宗源决定“关注”一下,这是个谁?有多重要?重如航母,或者高及珠峰?活蹦乱跳,或者半死不活?碰上这种事,一般人都会感觉气恼,在不得不服从、隐忍之际,难免有所发泄。柳宗源未能免俗,除了在心里骂,情不自禁就“关注”上了。他自忖这一心态还是有点问题,别说弄清楚有多费心,即便认出个张三李四又怎么啦?难道把对方从床上也拉下来?
柳宗源所在的等候区侧向彩超室大门,只要不是专注于手机,让眼光保持观察,谁从那个门进去,然后怎么出来,可谓尽收眼底。柳宗源坐的位置是倒数第二排,前面几排人员个个低着头,柳宗源的视线未受任何阻挡,观察很方便。但他很快便意识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从他走出彩超室大门起,那扇门始终紧闭,没有人从里边出来,也没有谁从大门进去。里边那张床有可能空置这么长时间吗?不可能。否则医生尽可从容为柳宗源做完彩超,无须急急忙忙把他请出房间。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彩超室另有通道,为内部使用,概不对外,里边人来人往,外头无从得见。
柳宗源站起身离开座位,往走廊另一侧走。他久坐不适,起来活动筋骨状,同时深入进行考察。那天他戴口罩,还有一副遮阳眼镜,足以掩盖真容,不易让人认出,可以临时充当福尔摩斯。柳宗源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通道无论多么“内部”,它都要有一个出入口。彩超室这种地方不属于国家机密单位,它的内部通道主要是为医务人员工作方便而设,不需要把出入口弄得像藏宝洞一般神秘,找到它应当不难。柳宗源记得彩超室里,紧挨着工作台有一个边门,从边门进去,里头房间应当是辅助工作室,供医生们办公或做操作前准备等。看来这个辅助工作室还有另一扇门,通往另一个地方,需要的话打开门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好比潜水艇各个密封舱都有门,全部打开就能从船头走到船尾。彩超室不是潜水艇,不需要设计得太精密,根据楼层建筑特点,它的内部通道口只可能与所属科室其他功能区域相关,不会另搞一套。
柳宗源走到走廊拐角,右转,抬眼一看,不禁一愣。
这里是护士站,今天一早到医院后,柳宗源先在这里排号,然后才转到侧面彩超室门外等候。此刻护士站门口站着个人,拿着手机在接电话,就是刚才说“松皮带。脱”那个年轻医生。年轻人个子不高,偏胖,身穿白大褂,脸上戴一个大口罩,该遮挡的地方全遮挡了,柳宗源怎么知道是他?因为那个电话,还有表情。年轻医生懒于言辞,干什么都像不太情愿,“老子不高兴”,接电话连个“嗯”都不应,回话简单粗暴:“不知道”“没有”“屁”。这还能是谁?就是他。
可见彩超室确有一个内部通道,其出入口就在护士站这里。这家医院超声科位于楼层东侧,占据一个转角,护士站正对自动扶梯口,而彩超室在转角另一侧。转角内侧房屋间肯定有通道沟通本科室相关部门,所以年轻医生才不需要于柳宗源眼皮底下从彩超室大门出来,就能出现在护士站门外。柳宗源感到惊讶的是这年轻人本该待在他的工作台边,往那位超岳父大人的肚皮上抹胶水或称耦合剂,怎么可以把那么重要的人物丢下不管,擅离职守,跑出来打电话?不会是轮班时间到了吧?
年轻医生居然一眼也认出柳宗源。他没吭声,只是扬起一只胳膊,拿着那手机指着柳宗源,用力向走廊另一侧比画,接连几下。这什么意思?应当与手机无关,他那电话该是打完了,手机已经“不在通话中”,可以拿来像粉笔擦一般应急比画。该医生这一套动作大约是要求柳宗源别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赶紧回彩超室大门那边坐铁长椅,不要叫名字时找不着人,耽误了检查。
柳宗源笑笑,问了句:“快了吗?”
年轻医生不吭气。
“要下班了?”
“早呢。”
“里边有医生?”
“主任。”年轻医生不耐烦,再次使劲往走廊那头摆手比画,“那边等。”
柳宗源不禁想笑。原来这回不只是柳某人赶紧提裤子让贤,年轻医生也得洗洗手让位走人。所谓“主任”应当是本院超声科的主任,通常那是专家、权威级医生,无论年龄、资格、经验都比这位年轻医生高出几个档次。重要人物的重要彩超自然得重要主任亲自做,有如重要领导才有重要讲话。无论年轻医生为什么总不高兴,显然还不够重要,但是他几番挥手比画,竟让柳宗源印象改善许多。此医生虽然懒于言辞,却也没把柳宗源之流只当成纸片,他还有一颗心,会担心这个被赶下床的人胡乱转悠找不着北,时候一到耽误了脱裤子。
柳宗源决定放弃,以他这种身份,充当福尔摩斯有些勉为其难了。既出来之则安心等之,待彩超室里边插队者做完,就轮到他二进宫了。插队进来的那位无论多重要,于柳宗源实不算什么,没必要去认个明白。就柳宗源本人而言,多脱一次裤子又不会缺斤少两,浑身上下里外部件该在哪里还在哪里,因此无需放在心上,最多在肚皮底下骂两句就行。心态摆正了,想明白就好。
柳宗源没料到这一回真是见鬼了,他回到彩超室大门前,坐在铁长椅上等候,转眼半小时过去,然后又是半个小时,身边众多等待者躁动不安,频频起身打听,唯那扇大门始终纹丝不动。里边是在做开颅手术还是彩超?如果是彩超检查,哪怕主任亲自操刀,至于要这么长时间吗?
半年前,柳宗源在省立医院做年度体检时,彩超发现“右肝后叶实质内探及稍高回声结节”,怀疑是血管瘤,医嘱定期复查。时过半年,家人催促再去查查,由于居住于本市,不想跑省城,柳宗源决定就近处理,找人请医生开了单子,自行前来市医院做彩超。当天上午十一点柳宗源另外有约,自忖早点到医院排队,不至于耗一个上午,耽误不了事情。不料时候一到,脱了裤子又功败垂成。由于所约事项牵动他人,不好擅改,柳宗源看着彩超室紧闭大门,只怕还要再等。
他再次前往护士站。年轻医生不见了,不知是否回到彩超室不高兴。柳宗源向值班护士了解里边什么情况,为何总是闭门不开?护士大约已经被不耐烦的排队者问得麻木,眼睛瞅着另外地方,嘴里让柳耐心等候。柳宗源称自己上午还有事情,不能再等。护士双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实在不行就另外安排时间吧。
“我的单子还在里边。”柳宗源说。
“没关系,我给你收起来。”她回答。
护士似乎也还不错,她给了柳宗源一支笔和一张纸条,请柳把名字和电话写下来。明后天有空再来,报个名字就可以,到时候尽量让他优先。
柳宗源没吭声,遵命写了递交。护士不经意间看了纸条一眼,忽然抬头一瞅柳宗源。
“你是……”她有点支吾,不确定,“柳,柳?”
“我不是。”柳宗源不等她说清楚就摇头否认,随即悄声问,“里边是谁?”
对方略犹豫,左盼右顾,终于低声回答:“陶副。”
“陶峰?”
她点点头。
“这家伙。”柳宗源笑笑。
话只说出前半,后头骂娘那部分没说,留在嘴里。
柳宗源离开护士站,掉头走过走廊,到了自动扶梯口,准备登梯下楼。他的身后突然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不及惊雷炸起,也算声量不凡,在人来人往闹如市场的医院空间里显得突兀异常。随后响起一阵喊叫嘈杂声。
出事了,就在柳宗源刚离开的护士站那里。
有一个汉子在那里发飙。看模样是乡下人,四十上下,个很高,瘦如竹竿。竹竿一头长着两只长脚,穿一双老式塑料凉鞋,几个脚趾在凉鞋口探头探脑。竹竿另一端是一张长条脸,此刻那上边满是黑气。
他在大喊大叫,异常冲动,用土话连声咒骂。护士站柜台前边,地板上有一摊破烂儿,是陶瓷碎片,还有几枝塑料花杂乱散落在碎片间。那些破烂儿原本组合成一个花瓶,摆放于护士站柜台一侧,作为一种传递温暖和美好的文明饰品点缀此间。该陶瓷花瓶最初应是用于供养鲜花,可能因为鲜花日常保养比较麻烦,终退而求其次被塑料花取代,唯陶瓷花瓶依旧。此刻该陶瓷已经成为一地碎片,刚才那一声突兀声响,显然是它在硬质地板上摔碎时发出。花瓶和塑料花都不是活物,没有外力作用,绝对不会自行从柜台上坠落。那么是谁干的?肯定是那个站在碎片旁冲动咒骂的汉子,此人如果不是蓄意肇事,至少是在无意间损毁了无辜公物。
人们开始驻足围观。即便在医院这种地方,依然少不了看热闹的。柳宗源也在第一时间停步,没有踩上自动扶梯。他退到一旁往护士站那边看,只一眼就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也清楚那是因为什么。
柳宗源从不喜欢看热闹,他这种人实不宜参与类似围观,当然更不宜卷入类似事端,眼下尤其不宜。他对此非常清楚,但是他却没有犹豫迟疑,还是及时停住脚,转身,在第一批围观者聚拢之际快步走过去,一直走到护士站柜台前,他的鞋底咔嚓咔嚓接连踩着了地上的花瓶碎片。
乡下汉子脸上青筋暴起,怒火万丈,正使劲拍着柜台,似乎恨不得一掌把柜台拍烂。他一边拍打一边大吼:“搞什么鬼!搞什么鬼?”柜台里侧站着两个护士,一个年纪大了点,一个很年轻。年纪大点的就是刚才让柳宗源留下姓名电话的那位,她比较镇定,面对暴怒汉子表情漠然,似乎见怪不怪。另外那年轻护士紧张至极,一张脸全吓白了,浑身哆嗦,可能是第一次碰上这种阵势,生怕汉子拍翻柜台进来打人。
“搞什么鬼!欺负人!”汉子吼叫。
年长护士回答:“我告诉你了,机器故障。”
“骗人!”
“机器故障,真的。”
汉子抬手,啪的又是一声重响。还好柜台可称结实,远胜陶瓷花瓶。
柳宗源在一旁插话进来:“别急,听我一句。”
汉子一转身,怒目直视,一只手还举得老高,似乎立刻就要挥掌劈下。
“是我。”柳宗源笑笑,“有话好说。”
汉子的表情立时有变,没再那么凶,显然是认出人了。他把高举的那只手臂放下。
“糊弄人!”汉子对柳宗源叫,“气死我了!”
“你可不能死。”柳宗源问,“你妻子呢?”
一个矮个女子突然从一旁蹿过来,一边拿土话大叫:“作死啊!作死啊!”一边扑到汉子身边,不顾众目睽睽,一把拽住汉子,把他往外拖。
“堪麦堪麦!”她连声叫唤。
那是土话,其字面可对应普通话中的“牵马”,内涵却是“赶紧”。赶紧个啥?离开,逃离,别找死。
这女子是乡下汉子的老婆。柳宗源刚向汉子问起她。
如果说柳宗源的出现让乡下汉子怒气发生转移,其妻的到来则有效浇灭了他的满腔怒火,有如一盆凉水当头淋下。汉子顿时失声,手臂也不再高举。柳宗源顺势而为,用力一推他的肩膀,把他推离护士站柜台。其妻在一旁使劲一拉,拔腿就走,汉子没再强犟,听凭老婆拖动,一地花瓶碎片在他的塑料鞋底吱吱有声。
事情如果就此了结,也算风波旋起旋停,点到为止,不会把其他人例如柳宗源什么的卷入事端。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没那么简单:乡下汉子夫妇刚走出两步,人群后边就传来大喊:“闪开!闪开!不要围观!”
来了两个人,保安,身着保安服装,一人手持对讲机,另一人手持橡胶棍,匆匆而至,分开围观人群到达事端发生地点。
他们来得够快。仅从时间效率看,本医院保安反应敏捷。这里边应当有应急机制和设施的作用,估计护士站柜台那里有一个紧急按钮,有如藏在银行前台柜台底下的那种报警装置,一旦发生歹徒抢银行,柜台小姐悄悄伸手一碰,警铃大作,警报同时外传,警察分分钟赶到,歹徒不赶紧离开就是找死。医院功能与银行有别,通常不会有歹徒蓄意抢劫,但是必须防备医闹,那种闹有时会酿成恶性事件,当下时有所闻。
乡下汉子夫妻慢了一步,保安已经上场,哪容他们在眼皮底下溜走。
“站住别动!”他们大喝,“不要走!”
汉子夫妇停步,回头看。女的一见保安手持橡胶棍,一下子慌了神,身子发软,突然坐到地上。男的大怒,当即跳脚:“来啊!”
“不许乱来!”两保安大喝。
其时柳宗源就在双方之间。乡下汉子被其妻拖走后,柳宗源也朝自动扶梯那头走,拟悄然离开,不料又碰到保安突然现身。应当说保安认得很准,一眼盯住乡下汉子夫妇,并没有要求柳宗源“站着别动”,但是柳宗源让自己再次卷入了事端。他回过身,朝两保安举起右手掌,以示阻止。
“不要过来。”他发话,声调不高,声音很平静。
两保安感觉意外,一起止步。
“你是谁!”一个保安大声问。
柳宗源没有回答,转身对乡下汉子一摆手:“走。”
汉子一动不动,紧握两个拳头,似还怒气难平。其妻倒是清楚,那时顾不上说话,即从地上一跃而起,拽住汉子转身就走。
“站住!”对面那两保安立刻发话制止,“不要动!”
柳宗源两眼一睁,喝了一声:“喊什么喊!”
两保安愣了。
“听我的。”柳宗源道,“有什么问题我解决。”
“你是什么人!”
“我是柳宗源。”
这里没有谁认识柳宗源,两保安面面相觑。柳宗源指着其中一位保安手持的对讲机,要对方打开,找他们领导。
“让我跟你们领导说。”柳宗源道。
保安给镇住了。这两位虽为本院安保专业人士,身上制服貌似某时期警服,毕竟不是拥有执法权的正经警察,底气相对薄弱。柳宗源既不慌不忙,又不容置疑,像是大有来头,不免让他们满腹狐疑,只怕碰上个什么领导,不好得罪。
保安呼叫对讲机之际,乡下汉子夫妻踏上自动扶梯,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十几分钟后,柳宗源给带到了院保卫科。
本院保卫科长姓林,高大魁梧,言语举止有军旅之风。人家不认识什么柳宗源,此刻唯照章办事,首先就是确认柳宗源的身份。
柳宗源问:“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你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科长肯定,“但是请在笔录之后。”
“行。笔录吧。”
科长指了指办公桌上的一个托盘:“请把手机放在这里,暂时替你保管。”
“必须吗?”
“我们有规定。”
柳宗源照办。林科长当面拿起手机看看,可能是要确认该手机未偷偷开启录音。
现场另有一位保安负责记录,讯问场面很正式。特别是林科长正襟危坐,面容威严,端着拿着,很负责、很享受,很像那么回事。他一定有个基本判断:如柳宗源这般只身混迹本院者,无论三教九流,都不是需要他特别顾忌的。柳宗源按照他的要求,把姓名、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告诉对方,让人家记录在案。柳还报称自己目前居住于本市,工作单位在省城,一个省直机关部门。
“具体是哪个单位?”
“省人大。”
“请说全称。”
柳宗源说了。对方威风凛凛的脸上略显犹疑。
“有工作证吗?”
“有。”
“请出示。”
柳宗源告诉他,此刻工作证不在身上,没有随身携带习惯。
对方问柳宗源到本院来干什么,柳宗源没有明说,只讲办理个人事务。柳宗源为什么要阻止两位保安执行任务?柳答称并没有阻止或妨碍两位保安,主要还是协助他们平息意外纷争,恢复正常秩序。对方查问柳与放射科护士站外肇事的汉子是什么关系,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柳宗源回答,他不知道汉子的名字,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其妻。在今天上午之前,他跟那两位从未有过交集。
“不会吧?”林科长怀疑,犀利目光紧盯柳宗源。
“就是这样。”柳宗源说。
如果柳宗源连那汉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以往并无交集,两人毫不相干,他为什么对其一再相助?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着?骗鬼嘛。即便柳宗源是活雷锋,乡下汉子也不是走不过马路的老婆婆,柳宗源帮他必得有个理由。同样地,如果该汉子与柳宗源没有任何瓜葛,柳宗源在火头上去招惹人家,别说劝服,一顿痛打都是自找。为什么那汉子不对柳动手,反而乖乖听命熄火?
柳宗源不多解释,只说因为某个偶然因素,他碰巧知道乡下汉子是陪送其妻从下边县里到本院检查,医生安排其妻于今天上午做彩超。其夫情绪冲动,是因为彩超室不知何故临时关闭,耗时数小时,等待检查者无从得知究竟,焦虑不已,屡屡追问护士站工作人员无果,导致耐心丧失。就此而言,院方也有问题。
“这种情况本可避免。”柳宗源说。
林科长表示,医疗事务不在他工作范围,他只管安保。但是无论如何,有问题可以反映,可以投诉,在公共场所吵闹肇事,破坏公共秩序,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我帮你们化解了。”柳宗源说,“你的手下赶到时,事情已经平息。”
“大闹一场,破坏公物,可以这样一拍屁股走人吗?”
柳宗源说,乡下汉子情绪失控,语言动作过激,问题确实存在。所幸化解还及时,没有酿成更多损害。就柳宗源观察,现场公物损毁不过就是一个花瓶,还有几枝塑料花,损失不大,还在本医院能够承受范围内。该汉子未必是有意砸损公物,很大可能是拍打柜台表示气愤时,不小心震落了那个花瓶。即便需要他为此负责,非得锱铢必较,追索这笔损失,相信本医院保卫科找到这对夫妇并不困难。无须利用监控录像、人脸识别,只要查一下彩超预约记录,人就找到了。或许不要几小时这对夫妇就会自己回到医院,他们恐怕承受不起再交一次彩超检查款的损失,需要回来把检查做完,因此搞清楚他们的姓名住址不费吹灰之力。即便人家不回来,医院也可以上门追讨损失,甚至可以要求对方加倍赔偿,都做得到。但是柳宗源不建议这么处置。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个小事端,不要往大里去做,让小事端酿成大事端。矛盾可以化解就应当想办法化解,不要无谓激化。毕竟这件事之所以发生,院方也不是没有任何过失。
“但是医院的东西可以说砸就砸,砸了白砸?”
柳宗源还是不建议去追索那位患者。以柳宗源观察,那对夫妻眼下更需要帮助,不是追究。能得到帮助,他们的情况便有望向好,对自身错误也会有正确认识。不当处置则可能导致此事恶性发展,特别是本案中的汉子性情比他人火暴。如果林科长耿耿于怀,本医院这笔损失务必要一个出处,柳宗源愿意承担。既然柳宗源出面介入此事,那就他来代为处理吧,所幸数额当不会太大。
柳宗源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两张百元钞票,放在林科长办公桌那个托盘上,时柳的手机也还躺在那里供“临时保管”。如今口袋里装着钱包的人已经很少见,有如珍稀出土文物,偏巧柳宗源就是一个,他从不用微信、支付宝或者什么卡片付账,平时基本也不买东西,无论线上线下,网购街购。特殊需要时如独自上医院,他就带上钱包与现金,没想到这会儿用上了。放射科护士站摔碎的陶瓷花瓶肯定不是什么古董,不可能多值钱,二百元应当足矣。
林科长看着托盘里的两张钞票,满眼狐疑。
“告诉我,你为什么?”他问。
这是所谓“元问题”,该林科长已经不止一次问起。
柳宗源说:“我已经解释过了。”
显然他的解释没有说服力。柳宗源为什么要帮助乡下汉子,仅仅因为“碰巧”知道该汉子陪送其妻来做彩超?柳宗源为什么要出面阻止保安执行任务,真以为那是在“协助”维持公共秩序?柳宗源究竟是什么人?即便如其自称是省人大工作人员,那些事就是他该干的吗?那么他为什么?
这时外边有人敲门:“林科长,电话。”
林科长让柳宗源稍候,自己起身离开,关上门。几分钟后他再推门进来,什么都没再问,拿起桌上托盘里的手机和钱,把它们交还给柳宗源。
“你可以走了。”他说。
“结束了?”
他点点头。
柳宗源笑笑:“笔录呢?要不要本人签名属实?”
“不必。”
“我该说谢谢吗?”
对方忽然低下嗓门:“不好意思。我也是照章办事。”
“这是对的。”柳宗源说。
他不再说话,起身离开。出门后,他注意到外间桌上有一个电话机,外壳是红色的。这当是本院“红机”,为内部通话设备,模仿大机关的内部保密电话系统。刚才一定有谁用该红机给林科长打了个电话,那一定是管得着林的“重要领导”,该电话的内容当是让林立刻放了柳宗源,别再什么“笔录”,搞得像派出所所长抓到惯偷一般。今天早些时候柳宗源躺在彩超室那张床上时,当班医生也曾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柳宗源就得赶紧穿上裤子,即便那年轻医生“老子不高兴”也没招,有如这位姿态很足的林科长。问题是怎么会有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导突然冒出来帮助柳宗源,好比柳宗源突然冒出来帮助肇事汉子?特别是柳宗源出于避免张扬考虑,自始至终没有给谁打电话求助,是哪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主动把他从“笔录”中打捞出来?不得而知。可以断定的是,显然有人认出了柳宗源并迅速反映,直至触发“红机”电话。此间认识柳宗源的人实已不多,包括本医院院长,于柳宗源都是陌生人,但是毕竟还有人认识他,可能是现场围观者中的某一位,也可能是超声科护士站那位护士。此前她让柳宗源留下姓名电话时曾想起什么,有点支吾,不太确定,询问他是不是柳什么。柳宗源不等她说清楚就回称自己不是,因为他早已不是,现在尤其不是当年那个柳什么。也许这位护士注意到保安带走的不是肇事汉子,却是柳宗源,感觉特别不踏实,赶紧上报情况?该护士显然觉得柳宗源可能是那个人,所以在柳宗源悄悄打听彩超室的插队者时,她才会透露那是“陶副”,陶峰,未曾刻意隐瞒。
那么会不会就是陶峰?在一个电话把柳什么从彩超床上挤下来后,又是他一个电话让柳得以从威风凛凛的林科长的犀利目光和“你为什么”中解脱?
谁知道呢。(节选自《芙蓉》2021年第6期中篇小说杨少衡《小事端》)

杨少衡,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市和省直部门工作。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海峡之痛》《党校同学》《地下党》《风口浪尖》,中篇小说集《秘书长》《林老板的枪》《县长故事》《你没事吧》等。
来源:《芙蓉》
作者:杨少衡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