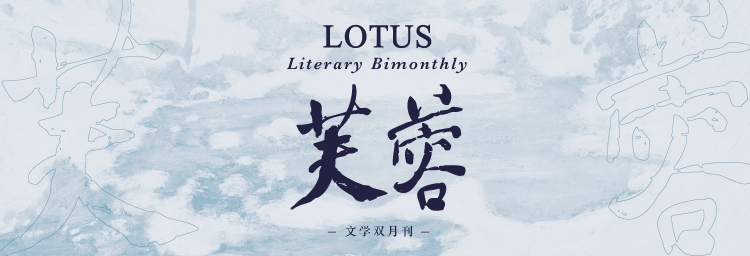

小河的左岸和右岸(短篇小说)
文/第代着冬
出高庙乡场口,有条河。初冬,两岸草叶黄了,河水清瘦,蓝如宝石。站在场口看去,只见一线河水在荒草里淙淙流淌,一如披蓝皮的蚯蚓在鹅黄中蜿蜒。蚯蚓之上,有一座小桥。桥的一头连着右岸,另一头,连着左岸一条大路。大路旁有座土地庙。
土地庙离桥头不远。说是庙,其实是用三块片石在土坎下搭建的一个洞状房屋,屋里坐着面露不屑的土地老爷。土地老爷也是一块石头。有人用毛笔在石头上画出人的眉眼,勾出颈脖和肩、衣服和手,这块石头便成了土地老爷。画者才疏学浅,不知土地老爷来往于仙界,衣着应该有别于凡人,他想当然地给它画了一件西服。土地老爷于是一脸无奈地披着一件皱巴巴的西服,终日坐在不足三尺宽的石头房子里,对着路人苦笑。
土地老爷苦笑了很多年,没人在意过它的表情。它冷锅冷灶地坐在路边,看桥下河水流淌;看庄稼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也没人停下脚步,给它敬奉一炷香火。多年之后,这个局面才得以改观,土地庙成了住在乡场上的苏一万和住在小河右岸的边志广的结拜之地。那天,苏一万如同捣蒜一般,不断将脑袋砸到松软的土地上,信誓旦旦地说,我,苏一万,请土地老爷做证,我与边志广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边志广说,这个不行。
苏一万说,兄弟,你啥意思?
边志广说,我不能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想,我比你小二十岁,怎么可能跟你一起死?
苏一万说,那我改一下,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富。
两人重新跪下来,请土地老爷当证人,花了不到一分钟,结成异姓兄弟。苏一万从土地庙前站起身,拍着膝盖上的泥土,表情称心如意,仿佛他刚刚离开公证处,做了一个满是虚假信息的公证。
在高庙乡人眼里,苏一万和边志广不应该成为朋友,更谈不上结拜成异姓兄弟。他俩性格不同,年龄差距也大。苏一万四十六岁,能当边志广的父亲。两个人本来不相干涉,是十五年前边志广阴差阳错救了苏一万一命,为他们结为异姓兄弟埋下了伏笔。事实上,边志广也不是真刀真枪救了苏一万,而是不经意间,把去劁苏一万卵蛋的周久顺给惊跑了。
周久顺是麻柳坪的骟牛匠,麻柳坪在小河左岸。骟牛匠长得圆头圆脑,四四方方。他长相大,眼睛却很小,又是斗鸡眼,看东西目光斜斜的,像鸡看东西那样。高庙乡的人认为,斜视的人心眼多。周久顺不仅没啥心眼,反而有些憨头憨脑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学骟牛。
年轻时,周久顺的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让他跟麻柳坪的篾匠当徒弟。那时农村还不像现在这样空荡,到处是人,对竹编器具需求量大,如果当上篾匠,不仅一日三餐不愁,每日还有些零星收入。可周久顺对当篾匠没兴趣,一心想当骟牛匠。每当他听见骟牛匠吹着羊角号走村串寨,就忍不住丢下篾刀,跟在骟牛匠身后,看他如何捆牛,如何取卵,又如何将牛卵穿在篾条上,像项链一样带回家。
周久顺对骟牛十分着迷,百看不厌,只要听到羊角号,不管手里在做什么事情,都会丢下不管,先去看骟牛匠骟牛。被篾匠赶走那次,他正用锋利的篾刀给师父剃头。剃到一半,羊角号响了,他放下篾刀撒腿就跑。他师父顶着一个阴阳头,在他身后喊,狗日的,我头发没剃完!
周久顺说,等骟完牛我再来剃你。
他师父说,放你妈屁,快回来,如果你再跑,老子就不教你当篾匠了!
周久顺说,不当就不当!
从那天起,周久顺被篾匠扫地出门,他毫无悔意,整天跟在骟牛匠身后看他骟牛。不明就里的主家,以为他是骟牛匠的徒弟,给骟牛匠做吃食时,也顺便给他煮一碗。他瞪着斗鸡眼,提心吊胆地斜着去看骟牛匠。见骟牛匠自顾埋头吃饭,才敢放半个屁股到板凳上,勉强吃上几口。渐渐地,他胆子大起来,吃得理直气壮,有时甚至催促主家快点搞饭,说师父饿了。听他的口气,仿佛他真是骟牛匠的徒弟。
高庙乡的骟牛匠,是乡兽医站的兽医。他不喜欢骟牛,也不喜欢小河左岸麻柳坪那个斜视的大个子,他懒得管,才没把周久顺从身边撵开。一个东西在一个地方放久了,会慢慢变得顺眼。人也一样。一段时间后,周久顺像长在骟牛匠身上的一个器官,协调、自然、妥帖。他对骟牛程序也熟悉了,适时帮骟牛匠递上一些用具,比如,绳索、刀具、缝针、篾条。过了两月,连骟牛匠也忘了那个斜视的家伙是自己送上门来的,错把他当成徒弟,主动让他打下手、干粗活。到最后,骟牛匠连刀都懒得动了,他抽着烟,蹲在地坝边,看周久顺骟牛,就像当初周久顺看他骟牛一样。
周久顺一上手,兽医就看出了他在这方面的过人天赋。骟牛的关键,是动作要快、伤口要小。周久顺无师自通,甚至骟得比兽医还好。兽医是农校科班出身,但他不喜欢骟牛,手艺比较粗糙。周久顺半路出家,但他对骟牛喜爱有加,誓要练成独门绝技,没事就拿劁刀在南瓜上练习掏籽。不到一年时间,他把自己练得有如猿猱之捷,被交叉捆绑的牛犊刚刚倒地,人们还没看清楚,两只牛卵就已经到了周久顺手上,像两只睡鼠蠕蠕而动。
牛卵自然归师父。周久顺已坐实徒弟身份,骟牛匠回家干煸牛卵下酒,也会让他尝一两箸。骟牛前,周久顺没吃过牛卵,以为除了一股腥臊味,没什么搞头。他喜欢骟牛,是爱听羊角号尖锐的声音,就像歌迷喜欢歌手。吃过牛卵之后,他才知道骟牛匠为什么要把牛卵归为己有。
周久顺说,师父,我懂了。
骟牛匠说,你懂啥?
周久顺说,原来你把牛卵带回家,是为了自己吃。
骟牛匠说,不为吃,还能为啥?
周久顺说,我原来以为,你是为了让领导知道,你一天骟了多少头牛,有多么勤快。
骟牛匠说,你不像长相那么蠢。
那以后,周久顺不仅喜欢上了羊角号,也喜欢上了牛卵。他像条影子,跟在骟牛匠身后走村串寨,学会了骟牛手艺,也学会了干煸牛卵。
周久顺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骟牛匠,是他二十五岁那年。那一年,高庙乡的兽医站撤销了,兽医调回县畜牧局。临行前,兽医将一把磨得油光锃亮的羊角号交给周久顺。羊角号还是那只羊角号,但声调欢快多了。以前骟牛匠吹,因为心情不好,只是吹出声音,有个调调。现在周久顺吹,心情大好,能把羊角号吹得像唢呐一样欢快。在羊角号的欢鸣声里,周久顺一跃成为高庙乡唯一的骟牛匠。从此,在小河左岸和右岸的地面上,人们听到的羊角号,都是周久顺吹的;人们看到的牛卵,都是周久顺取的。
高庙乡有乡谚说,莽人有莽福。这话不假。别看周久顺不爱动心眼,做事莽撞,仿佛所有事情他注定是吃亏的那一个。其实不然,他莫名其妙就能占到便宜。周久顺当上骟牛匠后,干得比兽医欢,得到的牛卵也比兽医多。除了自己吃,还有不少剩余。他把剩下的牛卵高价卖给苏一万,苏一万又以牛卵为原材料,以泡椒、八角、花椒、蒜末、葱花、姜片、橘皮为辅料,做出一道叫以卵击石的美食,一时供不应求,高庙乡的男人一度以吃上以卵击石为荣。
苏一万是乡场上的人,祖上以生意为业,自恃比乡下人要高一等。从他爷爷那辈起,留下左脸神经抽搐的习惯,成为家族遗传。苏一万的脸抽搐起来没规律,全凭面部神经高兴。没来由地,左脸肌肉忽然往耳后扯,将嘴压扁,形成一个鄙夷的神情。一个男人动辄面露不屑,会被好斗的男人视为挑衅,容易招惹麻烦。据说,苏一万的爷爷因此多次与人斗殴,一辈子拖着一条残腿。
尽管教训深刻,左脸神经抽搐还是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代传下来。到了苏一万这代,他脸上的不屑表情更鲜明了,每当他看见小河右岸麻柳坪的那个大个子肩挎一串牛卵,站在屋檐下斜视,他的咬肌就像口弦上的簧片那样,不停地上下颤抖,嘴巴扁扁地形成一条缝,满脸尽是鄙夷之色。
周久顺说,你嘲笑哪个?
苏一万说,我吗?我没嘲笑哪个。
周久顺说,你是不是笑我的牛卵?
苏一万说,我没笑你的牛卵。
周久顺说,那好,我让你认识一下牛卵,让你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接下来,周久顺给苏一万推销牛卵。他之所以要推销牛卵,是因为苏一万开了一家酒楼,叫一万酒楼。开酒楼前,苏一万在乡场上有一家卖小百货的门店,叫百货总汇,卖一些诸如牛鼻绳、斗笠、弯刀、铁锅、历书、卫生棉、酒精、绿豆、大米、白醋、创可贴、安全套、膏药、棉布、拖把等小东西。后来他在百货总汇旁边开了家一万酒楼,生意一直不好。
人们认为,如果不是命运阴差阳错,麻柳坪的骟牛匠无论如何不会把牛卵卖给苏一万,因为他是高庙乡著名的吝啬鬼。苏一万的吝啬也是祖传的。从他爷爷那辈起,一根牙签就得用半年。到了苏一万手上,他把祖传的吝啬更加发扬光大。如果他家还能扔出一点垃圾的话,确实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缘故。
事情往往是这样,明明不可能,有时毫无道理,一下子就变成了可能。在高庙乡,除了骟牛匠,没人吃过牛卵。人们觉得,向吝啬鬼推销一个他没吃过的东西,无异于找他要钱箱子的钥匙。莽人自有莽办法,周久顺送了苏一万一只牛卵,同时告诉了他干煸的方法。吝啬鬼本来爱捡便宜,也不管吃了是不是会死人,他如获至宝带回家,把牛卵煎炒一番吃了。牛卵从此一跃成为一万酒楼的主打菜,菜名叫作以卵击石。
以卵击石一经推出,供不应求。乡场上的男人们为了吃到这口美食,得提前三天订座,有时为了争一只牛卵,几个大男人在一万酒楼前怒目而视,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们在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为了抓住商机,苏一万逮到周久顺就让他跑快点。
周久顺说,我又不参加跑路比赛,跑那么快干啥?
苏一万说,你跑快一点,能多见几头牛。
周久顺说,我见那么多牛干啥?
苏一万说,你见的牛多,不是能多骟几头嘛。
周久顺说,我懂了。
周久顺真懂了。小河右岸麻柳坪的大个子不会动心眼,这次稍稍动了一下,斜着眼睛想了半天,发现苏一万离不开他,借机给牛卵涨了价。原来,周久顺将一只牛卵卖给苏一万,只要二十元钱,苏一万经过加工,做成以卵击石卖给场上吃酒的男人,半个牛卵一份,收费三十元,一只牛卵可以卖六十元。苏一万让周久顺跑快点之后,周久顺看到了商机,借机把一只牛卵涨到三十元。经过讨价还价,苏一万接受了周久顺的条件。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每份以卵击石涨五元钱,他的本钱就回来了。
经历了这件事,苏一万看出骟牛匠学聪明了,不像过去那么傻。为了拴住高庙乡这个唯一的牛卵货源,苏一万不得不改变策略,把供货商周久顺发展成了自己的朋友。单单成为朋友还不足以让周久顺横下一条心要劁了苏一万的卵蛋,关键是他们成为朋友后,除了买卖牛卵,还会跟对方家人往来,这就牵涉到了周久顺的老婆万之菊。
出场口过小桥,走过土地庙,沿小河左岸走上五里大路,就到了周久顺家,家里住着他老婆万之菊。周久顺跟苏一万成为朋友前,万之菊也常来高庙乡场上赶场,她东游西逛,没个定所。自从她男人跟苏一万成了朋友,她赶场就去百货总汇,有时买个发夹或镜子一类的小东西,有时啥也不买,就站在柜台前跟一脸鄙夷的苏一万摆龙门阵。摆到高兴处,万之菊会拍自己的腿。如果离得近,她也会拍苏一万的手、肩、背以及上半身其他地方。万之菊拍苏一万,没别的意思,在麻柳坪,她是个有名的“大夸夸”,自来熟,摆个龙门阵喜欢动手动脚。
如同所有闲话那样,周久顺是最后听到的那一个。他能听到闲话,得益于在百货总汇门口摆摊的牙医。百货总汇门前有几个小摊,一个牙医,一个铁匠沟卖草药兼相面的金铁嘴,还有一个是车阳坝边志广的父亲。边志广的父亲利用草药摊子旁边的一块空地,放了一个小蒸笼,在那里卖都卷子。都卷子是高庙乡的一道小吃,将蕨根粉摊成饼,卷成棍状,切成小段,在蒸笼里蒸熟,佐以葱花、姜末、香醋、酱油、辣椒而食。万之菊在百货总汇拍来拍去,三人都不说。后来牙医见周久顺挣了不少钱,想给他镶颗金牙。把万之菊拍苏一万上半身的事情给暴露了。
那天,周久顺挎着一串牛卵,从百货总汇前路过。经过牙医摊位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牙医。周久顺一旦盯住某个东西,就说明他眼里装的是别的东西。那天他假装看牙医,其实是在看路。牙医被周久顺的目光打动了,他想借机动员骟牛匠装一颗黄铜做的金牙。牙医说,骟牛匠,你停一下,我给你说件事。
周久顺说,啥事?
牙医吐了泡口水,搓了一把脸,仿佛他要理清一下思路。牙医搓完脸,不说镶牙,却对周久顺说,老兄,我想给你说说眼下这个社会。你知道大城市的街头广告都宣传什么东西吗?全是装潢门面的东西,仿佛一个城市不装潢一下门面,都不能表明自己在进步。人也一样,老兄,你也应该装潢一下门面。
周久顺说,我为什么要装潢一下门面?
这个问题把牙医逼到了死角。他最初只想做成镶牙的生意,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做成镶牙生意,得先说清楚镶牙理由。他吐了一泡口水说,你没有像样的门面,怎么可能留住老婆的心?
周久顺说,哪个说我留不住老婆的心?
牙医不说话了,用手往百货总汇指了一下。这一指,含义深刻,一下子把周久顺的疑心病勾出来了。本来,周久顺不爱动心眼,自从当上生意人,做起牛卵买卖,也爱动心眼了。那天过后,周久顺一有空,牙医的手指就在他脑子里乱晃。顺着这根手指看过去,他一般能在虚空之处,看见一些经过想象加工后的不堪画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周久顺胡思乱想,而是他很快拿到了证据——万之菊怀孕了。万之菊是不可能怀孕的,这一点别人不知道,周久顺心里却明镜似的。他们结婚十年,老婆一直没怀孕,周久顺怀疑老婆有问题。直到有次他骟牛骟到别的乡,在乡场的公厕墙上,看到了一个专治不育不孕的名医小广告。顺着小广告,找到一家小旅馆,花了八百元钱,经过名医一番捏摸,周久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是自己不行。这个秘密从此埋在他心底。现在,万之菊怀孕了,周久顺像个哲学家一样拍着胸口大声自问,难道,吃牛卵能治疗不育不孕症吗?他冲动地大声回答说,不能。
既然不能,当然是万之菊和苏一万有问题。那段时间,周久顺也不出门骟牛了,天天跟万之菊讨论这个问题。万之菊自然不承认,她拍着自己的腿,痛心疾首地说,周久顺,我们结婚十年了,我的肚子你还不明白吗?
周久顺说,我是不明白它怎么忽然就怀上了孩子。
万之菊说,也许是遇巧?
周久顺说,有这么巧吗?十年都没瞄准的靶子,我乱打一枪就上靶了?
万之菊说,我不跟你扯了,你说怎么办吧!
周久顺说,我得把面子捞回来,先割下苏一万的尿管子,让他没有当丈夫的本钱。
万之菊是个大夸夸性格,不怕事。加上她太了解周久顺了:他骟牛可以,绝对没劁人的胆量。他在她面前提些虚劲,只是为了过过嘴瘾,于是她接着周久顺的话说,你说话算数,去把苏一万劁了,劁回来我给你干煸了下酒。
周久顺说,劁就劁。
万之菊说,我等你捷报。
周久顺被万之菊逼到绝路上,只能去把苏一万劁了。他骟过无数牛,没劁过人。他相信技术是一样的,区别在于胆量不一样。为了壮胆,周久顺喝了半斤白酒,摸黑提着劁刀,来到高庙乡场上,趴在了百货总汇的窗前。周久顺跟苏一万是朋友,知道他的生活习惯。苏一万以前住在楼上,因为早晨要起来准备酒楼的早餐,就搬到了临街的一间空房里。空房年久失修,门窗不很牢靠,窗闩是横插的,只要用劁刀轻轻一拨,就能顺利拨开。
那夜周久顺是铁了心要把苏一万劁了的。一方面是自己有气,另一方面是跟老婆打赌。他最终没能把苏一万劁了,不是胆量不行——他已经喝醉了,一个酒鬼跟疯子差不多,谈不上有无胆量——而是跟车阳坝的边志广有关。
车阳坝在小河的右岸,沿小河走五里到了麻柳坪对岸,就到了边志广家。十五年前,边志广十一岁,他跟村里一群半大小子到高庙乡场看露天电影。电影的名字他已经忘了,因为他们跑到场上时,电影已经开演了。乡场中间有一个小广场,电影银幕架在小广场边上,后面是一个猪圈。边志广转了一圈,发现银幕正面已无立锥之地,他独自一人跑到猪圈楼上,睡进稻草堆里看银幕的反面。反面也很清晰,只是动作相反。边志广看了不到五分钟,就在稻草堆里睡着了。
等边志广醒过来,电影早已散场,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一地暗影。高庙乡的黑夜里,一切都显得低调,只有夜风十分疯狂。它们在巷道里穿行,在屋檐下呼叫,在树枝下摇晃,很快把边志广吓坏了。他从猪圈楼上下来,跑过百货总汇,本意是想跑回车阳坝。等他跑到场口,看到小河,才想起回家要路过一座坟山,腿一下子软了。
他在场口坐了一阵,决定继续回到猪圈楼的稻草堆里,等天亮了再回家。当他跑过百货总汇,借着发蓝的夜光,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趴在窗子上,脑子里迅速想起吸血鬼的传说。在边志广卖都卷子的父亲讲的故事里,吸血鬼是最厉害的一种鬼,它除了身形高大、青面獠牙,还有一条长喙,隔着门窗也能吸到里面睡觉的人的血液。
边志广尖叫了一声。他看见吸血鬼回过头,又尖叫了一声。边志广感觉这一声效果不错,场上有人打开电灯,百货总汇的灯也亮了。窗前的鬼影见窗缝透出灯光,蹲了一下,佝偻着往小广场方向跑了。他的步伐东倒西歪,明显像个酒醉鬼。在边志广眼里,吸血鬼是踩着空气逃跑的,脚步忽高忽低。
苏一万打开门,发现明亮的灯光里,边志广被吓得瑟瑟发抖。苏一万认识这个小家伙,他有时会跟他父亲来赶场。他父亲在草药摊边卖都卷子,他则在场上乱窜。苏一万说,你为啥不回家?
边志广说,我在猪圈楼上睡着了。
苏一万说,刚才是你在尖叫?
边志广说,是。
苏一万说,为啥?
边志广说,我看见你家窗子上趴了一个吸血鬼。
苏一万说,你梦游了。
那一夜,所有人都认为边志广看花了眼。只有周久顺知道,是边志广救了苏一万,也救了自己。当他一口气跑回麻柳坪,酒醒了,被吓得惊恐万状,手心直冒汗。他再也不敢跟万之菊打赌了,也绝口不提劁人的事。第二年,万之菊生下一个儿子,跟他一样长得圆头圆脑,一双斗鸡眼,一看就是他的儿子。周久顺从此对那夜的莽撞行为守口如瓶,仿佛他从没干过准备劁人的事。
这个秘密被泄露出来,跟金铁嘴有关。金铁嘴跟牙医的想法一样,也想在周久顺身上找点钱。他见周久顺不断往一万酒楼卖牛卵,得了不少钱,如果相上一次面,说点好话,说不定能挣不少。金铁嘴像个替人挖坑的人,逮到骟牛匠就胡言乱语,好在周久顺是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不吃他那一套,来来往往搞了很多年,金铁嘴一次也没搞成。
后来之所以搞成了,是金铁嘴发现,骟牛匠酒后没把持。他于是挖了个更大的坑,请他吃了一次酒,也吃了以卵击石。喝醉了,骟牛匠像缴械的流寇,没什么抵抗能力,只能任人宰割。金铁嘴先算了周久顺的前世,认定他前世是只兔子精,得了三百元钱。又算了他的后世,认定他再过五十年会变成一棵摇钱树。周久顺说,金铁嘴,你的意思是我还能再活五十年?
金铁嘴说,当然,你能活一百多岁。
周久顺说,够了,一共花了六百元钱,不仅知道自己前世是只兔子精,还知道自己能再活五十年。金铁嘴,你够意思。
金铁嘴说,这是你命中带的。
周久顺说,我得感谢边志广。
金铁嘴说,那个卖都卷子的儿子,为啥?
周久顺说,你不知道,十五年前,我听信牙医打胡乱说,想去把苏一万的卵蛋劁了。正要得手时,边志广叫起来,惊动了苏一万,把我吓跑了。如果不是他,我现在说不定已经被枪毙了。
金铁嘴说,劁两个卵蛋,枪毙倒不至于。
周久顺说,你想,苏一万会甘心让我劁?打起来,我失手把他杀了,不把我枪毙了,怎么平息高庙乡的民愤?
金铁嘴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周久顺说了也就说了,酒醒之后很快把这事忘了。金铁嘴没忘,他捂着嘴乐了半天,这条信息对他来说很值钱。在他的宏大规划里,他不仅想给周久顺相一面,也想给苏一万相一面。自从知道那夜的真相后,金铁嘴像钓鱼人先往鱼塘里撒饵,他通过牙医,断断续续给苏一万透露一些消息。比如,金铁嘴说苏一万最近可能要好好发一笔,又不说怎样才能发;又比如,他说苏一万近期可能有喜,又不明说有何喜。苏一万本来不信金铁嘴那一套,然而,似是而非的消息太折磨人了,到后来,苏一万真是担心,如果不理睬金铁嘴,很有可能错过发财机会。
像偷食的鸡假装看着别处,苏一万抽搐着左脸,一脸讥讽地在金铁嘴面前晃荡。金铁嘴何许人?一眼就明白,苏一万上钩了,急于知道下文,可金铁嘴偏不说。钓鱼人不急,鱼就急了。没几天,苏一万找到金铁嘴,鄙夷地说,金铁嘴,你不要逗我,我沉得住气,不吃你那一套。
金铁嘴说,那好,我说点你知道的。
苏一万说,你说。
金铁嘴说,十五年前,边志广看电影那夜,他看见了啥?
苏一万说,你先说,他看见了啥?
金铁嘴说,你自己想。
金铁嘴一句你自己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胀死麻雀的最后一粒高粱,彻底把苏一万的矜持击垮了。他一反常态,像宴请要人,私下准备了一桌酒席,并利用一个门前只有金铁嘴的空隙,很诚恳地邀请他晚上赏光,到一万酒楼尝尝以卵击石。酒桌上,他们相谈甚欢。
金铁嘴说,你这几年生意怎样?
苏一万说,还不错。
金铁嘴说,我问你,天天有人叫你输一万,你不仅没输,还赚了,为啥?
苏一万说,老天爷帮忙?
金铁嘴说,不是老天爷,是因为你有贵人相助。
苏一万说,哪个是我贵人?
金铁嘴说,车阳坝边志广。
一听说是卖都卷子的那个人的儿子,苏一万哈哈大笑起来。他原来觉得金铁嘴手里可能真握有打开命运之锁的金钥匙,没想到,他也就混个吃喝。苏一万左脸上的神经更频繁地抽搐起来,他的表情已经不是鄙夷了,而是在嘲笑和愤怒之间变换,如同揭开了骗局的受害者那样。金铁嘴安心吃着酒肉,让苏一万一个人跟自己的表情过招,直到他快要愤然离席时,金铁嘴才像武林高手一样抛出撒手锏,谦恭地请苏一万回忆一下十五年前那个夜风呼啸的夜晚,边志广看到了什么。
苏一万说,吸血鬼。
这一次,金铁嘴没有保留。他把那夜周久顺如何要劁他,又如何被边志广惊跑;惊跑后边志广又如何在场上睡了一夜,周久顺从此不敢再劁他,一一说给苏一万听了。听着金铁嘴如同从枯井里传来的冷飕飕的声音,苏一万背脊阵阵发麻。他悄悄从裤兜里伸出手,心有余悸地捏着自己两个已然苍老的卵蛋,吓得冷汗涔涔,面如白纸。想当初,他差点一不留神成了太监。
这个一辈子都在貌似鄙视别人的人,第一次被人说得心服口服。在金铁嘴的引导下,他想起十五年来,自己确实很顺。百货总汇和一万酒楼赚了不少钱,虽然大家都赚钱,但经过金铁嘴一番分析,他赚钱似乎确实跟贵人相助有关。尤其是他能保住两个卵蛋,看似巧合,其实是命运的必然。想到这一层,苏一万觉得自己见识太少了,有必要向金铁嘴请教。他说,我知道边志广是我的贵人又有啥用呢?
金铁嘴说,缠住他,让他成为你的靠山。
苏一万说,怎么才能缠住他呢?
金铁嘴说,搞桃园结义呀。
苏一万说,我明白了。
当苏一万提着礼物在小河右岸的车阳坝出现时,所有人都恍惚了。在人们眼里,苏一万是场上人,比乡下人高一等,怎么反倒给在他门前卖都卷子的人送礼?苏一万费了一番口舌,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边志广惊跑了小河左岸的周久顺,替他保住了男人的本钱,他来感谢救命恩人,要和边志广结为异姓兄弟。大家听了,觉得他够朋友,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边志广的父亲听了苏一万的来意,笑得合不拢嘴。他在百货总汇门前卖都卷子,一直感觉寄人篱下,不那么理直气壮。现在,既然苏一万提出要跟边志广拜把子,他觉得有必要张扬一番,提议到埋有他家祖坟的竹林里去结拜。苏一万不同意,他不想给别人祖先下跪。他提议,到土地庙前去结拜,请土地老爷当证人。
结拜那天,除了为誓词起点争执,还算顺利。当他们从地上站起身,苏一万觉得,边志广是他的了。有了靠山,不敢说无法无天,至少财源滚滚,出入平安。边志广不这样看,他才二十六岁,不太相信这一套,如果不是为了方便父亲在场上卖都卷子,他才不会跟苏一万结拜为异姓兄弟。
拜完把子,边志广以为没什么事了,他把异姓兄弟丢到一边,独自一人跑到福建打工去了。他一走,苏一万急了。他不是急异姓兄弟的安危,而是急贵人离自己太远,有可能法力不够,罩不住他的前途。他请金铁嘴帮忙,金铁嘴看不到好处,不愿出力。这个难不倒苏一万,他有以卵击石这道菜,不愁金铁嘴不帮忙。夜幕降临,当寒风穿过空洞的场口,发出梦呓般的声音,金铁嘴一边吃着牛卵,一边替苏一万操持命运,他说,这个好办,让他回来。
苏一万说,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说我想他?
金铁嘴说,说你不顶用,得说卖都卷子那家伙快完蛋了。
苏一万说,让我给他说?
金铁嘴说,不,得让卖都卷子的自己说。
即使再吝啬的人,如果有求于人,也肯下本钱。苏一万的付出有了回报。金铁嘴没费啥力气,三言两语,就让卖都卷子的家伙相信,如果他儿子边志广还待在遥远的福建,不出十天半月,就会一命呜呼。呜呼的原因不好说,有可能出车祸,有可能摔下楼,也有可能醉死。车阳坝的人知道,出门在外,醉死了连个赔钱的人也没有。
回到小河左岸的车阳坝,当天晚上,边志广的父亲就痛得在床上乱滚。他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很快传遍车阳坝,传遍小河左岸的麻柳坪,以及麻柳坪后面的铁匠沟。好心人用短信、微信,把这条不幸的消息通过空中数条看不见的通道,源源不断地发到边志广的手机上。一夜之间,他的手机像只吃撑了的鸡,咕咕地叫个不停。边志广相信,如果动作慢一点,可能真见不上父亲了。他带着一身委屈,昼夜兼程,三天后,当他在高庙乡场简陋的公共汽车站跳下汽车,看见他父亲露出一口烂牙,在牙医面前开怀大笑时,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可他父亲都卷子卖得好好的,为啥要骗自己呢?边志广顺着父亲这条线索往下捋,捋出金铁嘴。又从金铁嘴那里,捋出苏一万。再从苏一万身上往前捋,捋出了事情真相。原来,苏一万跟他结拜不是知恩图报,而是想让他继续替自己开路,如果苏一万遇到人生的坡坡坎坎,他还得给苏一万当炮灰。
狗日的,太歹毒了!边志广骂骂咧咧地沿小河往上走,从小桥上由右岸跨到左岸,去百货总汇找到苏一万。边志广以为,他知道了事情真相,苏一万会不好意思。恰恰相反,当边志广告诉异姓兄弟,自己在土地老爷面前说的话作废,他们散伙了时,苏一万竟然笑了。苏一万说,兄弟,我们散不散伙你说了不算。
边志广说,谁说了算?
苏一万说,谁说了也不算。
边志广说,为啥?
苏一万说,因为我们拜了把子,相当于签了合同,你见过有哪个单方面撕毁合同的?那叫违约,得赔钱。
边志广对赔钱没有思想准备,他灰溜溜地回到小河左岸的车阳坝,才想起拜把子跟签合同不是一回事。他又返回左岸,来到乡场上,站在一万酒楼门前大吵大闹,又让苏一万找个理由给骗回去了。如此反复几天,整个高庙乡都知道,那两个在土地老爷面前赌咒发誓的异姓兄弟撕破脸了。
边志广越是不愿意当苏一万的贵人,苏一万越把边志广当贵人。苏一万一度固执地认为,如果边志广心安理得地当他的贵人,他倒要怀疑这个贵人的真实性了。眼下好了,没啥可怀疑的,他抽搐着左脸,一心一意给边志广捣乱。他坚信,既然他们在土地老爷面前许过愿,边志广就是他的。
两个家伙在高庙乡折腾,没折腾出什么结果,却把大家闹糊涂了。本来,这件事的起因是牙医,牙医的源头是小河左岸周久顺的老婆万之菊,万之菊夹在周久顺和苏一万之间,怎么变成了苏一万跟小河右岸的边志广扯皮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没等人们回过神来,又出事了,苏一万把边志广的对象给拆散了。
这门亲事是牙医介绍的。牙医是朱家湾的人。朱家湾在小河左岸,有个姑娘叫朱小艳,长得蛮规矩。她去小河右岸车阳坝看了地方,对边志广很满意。金铁嘴免费看了两人的生辰,八字也合,边志广于是觉得朱小艳非他莫属。边志广一得意,忘了他有个异姓兄弟。苏一万也没闲着,听说有人跟他分享贵人,颤抖着左脸,一脸不屑地去朱家湾走了一趟,把边志广的朱小艳给说没了。苏一万给朱小艳说了些什么话,下了些什么烂药,对边志广来说至今是个谜。他只知道,朱小艳从朱家湾带来口信,以左岸和右岸的性格不合为由,把他的手机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五天后,边志广喝醉酒,从小河右岸车阳坝来到高庙乡场上。路过土地庙时,这个醉酒的家伙把土地老爷从庙里掏出来擒在手里,他说,土地老爷,你的任务是守护土地和收成,不要乱当证明人。我宣布,你的证明无效,我跟苏一万结拜的事情作废。听懂了没有?你吹黑哨,被我搞下课了。
说完,边志广把土地老爷丢进小河边的草丛里,那块石头真像神仙那样,瞬间消失了踪影。边志广拍掉手上的泥土,走进乡场,来到一万酒楼,找到苏一万。苏一万正在给骟牛匠周久顺结账。他把一大堆揉得皱皱巴巴的纸币丢在柜台上,又一张张地碾平。当他挑出一张绿色的五十元钞票,用指甲把它卷起的边角抠平时,扑进门来的边志广从周久顺手里抢过劁刀,像有预谋似的,埋头捅了苏一万一刀。
据乡卫生院的医生说,那一刀边志广捅在了苏一万的腹部。如果再抬高三厘米,苏一万就没救了,边志广肯定不止判三年。医生说这话时,边志广的刑期已经判下来一个月了。时值春天,淅淅沥沥的春雨把高庙乡笼罩在一片寂寞的响声里。听了医生的话,站在一旁的闲人说,这到底为啥?两个结拜兄弟,怎么忽然动起了刀子?
医生说,这个问题你得问土地老爷,听说它当过证明人,那两个家伙为啥反目成仇,只有神仙知道。
闲人说,现在没法问了。
医生说,为啥?
闲人说,土地老爷下课了。
医生说,又为啥?
闲人说,它连左岸和右岸的事情都管不好,是个庸官,让边志广搞下课了。
闲人说完,对着不远处的小河吐了一泡口水。顺着口水划出的弧线,医生看见空中的雨滴亮出长长的雨脚,像流星一样闪亮。此时,小河左岸和右岸的土地上一片空旷,闪亮的雨滴形成珠帘,悬挂在土地庙前。透过雨幕,医生发现,没有了土地老爷的土地庙像一张无声呐喊的嘴巴,里面除了幽暗,只有无边的安静和空荡。

第代着冬,男,196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十月》《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山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转载;入选《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1世纪年度小说选》《中国短篇小说100家》等选本及教辅读物。曾获《中国作家》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
来源:《芙蓉》
作者:第代着冬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