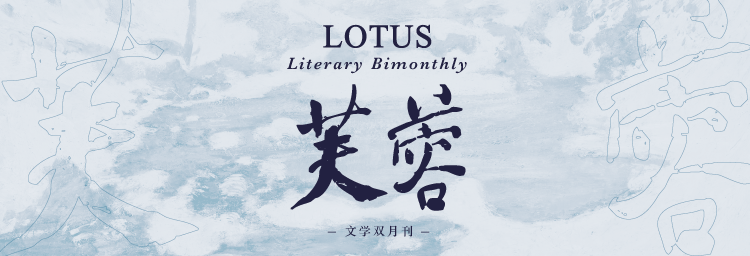

暂居者
文/李晓君
景象
初冬的萧瑟感,是通过门口那槭树、榆树的叶子显示出来的——像悲苦的老人紧皱的眉头,瑟瑟风中,已经变黄的叶子尚未完全脱落,还挂在枝上,又像冷风中抖动的肩头。第二天一早,我去停车场取车时,看到车身满是落叶,那贴在玻璃窗上的叶子混合着雨水,像墙上的小广告片。冬天的雨丝,夹带着寒意侵入脖颈、手腕,衣物上全是雨痕,糟糕的天气影响着人们的心情。这个停车场,在小区门口左侧,农商银行营业部对门,总共不到二十个车位,由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女同志看管。女收费员年纪不大,但头发全白了(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帽子)。天气好的时候,她坐在银行门前,手里织着毛线。每次我从贤士横街开车过来,她都会主动帮我引导,收费有时也不那么严苛,看得出来是个宽厚的女性。
现在,雨水夹带着落叶,在冷风中,将停车场、人行道制造成狼藉的景象。女收费员也坐在农商银行营业厅里避雨,享受暖气。营业厅还没有人来办理业务,银行职员穿着黑色西服白色衬衫,在玻璃后面,影影绰绰;大厅经理站在刷卡取号机器旁边,皱着眉头,正用手去拔指头上的一根倒刺。米色地砖干净、透亮,倒映着顶上悬挂的红灯笼,方形柱子上还挂着红色中国结,侧面是“严禁吸烟”“禁止拍照”的警示牌。电子滚动屏显示着“欢迎光临”以及“①号窗口”“②号窗口”的字样,猩红的宋体字。室内有暖气,女收费员舒适地坐在金属椅子上编织毛衣,不时地朝窗外的停车场张望。
鸿松图文数码快印的卷闸门已经打开,我和太太经常会去那里复印和打印资料,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机器 :数码直喷机、复印机、电脑、打印机。阳明东路一条街下去,到文家路北口站台,不到一公里之地,街道两边大大小小的图文数码店有十几家。数码店旁边是一家理发室——生意不怎么好,换了几个店名,也换了几个老板。再旁边是个网吧——我曾经进去过,那次正遇上家里宽带坏了,我走进网吧,通过网络直播收看欧冠半决赛(我是英超曼城队的球迷)。
益丰大药房和汇仁堂专业药房面对面,中间隔着贤士横街,它们门前也停满了汽车,隔三岔五就会有交警过来张贴罚单。药店旁边是洗脚屋,狭长的室内排着六七个躺式沙发,在白天,除了店主——那对夫妻,再无一人,而晚上,明亮的灯光下,似乎显得特别忙碌。谭记水煮门口放着几个灌满混凝土的油漆桶——为防止停车占道设置的障碍。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我开车下班回来,在贤士横街寻找车位(停车场车位难以满足需求,当女收费员低着头,对试图前来的车辆不理不睬时,那就表示车位已满;偶尔她也会抬起头来,扯着嗓子说,车位满了!)。来回几遍,无从见缝插针。傍晚的贤士横街,是一片停满了车辆的乱糟糟的景象。
有时,晚上我从家里出来,经过贤士横街,在猛味烧烤店旁右拐,进入一条黑黝黝的小巷子。巷子路口有个自助洗衣房、公厕,还有狭小简陋的杂货铺、早餐店,幽暗的路灯下,显示出一种蛮荒和陈旧的气象。天气好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老人坐在屋檐底下,现在是寒冷的冬夜,这里显得更加荒凉。在贤士花园小区,住着女儿学校的一个美术老师,姓萧,比我小几岁,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蜷曲的头发凌乱地在脑后飘着。他在这片居民房里,租赁了两间房子作为画室(他的工作室则在我们小区里),他带了十来个学生,都是实验中学美术班的孩子,他们晚上在这里学画。我的女儿跟着萧老师学过一段时间的画,每周有三个晚上在这里上课。我曾经去过萧老师的工作室,对一幅描绘着陈旧街巷的风景画印象颇深——这正是画室所在的位置,也是萧老师儿小时生活的地方,他住在这里,度过小学、中学,直到读大学才离开。萧老师身上有着与这片陈旧的平民区相一致的气息。他个头瘦小,右腿前两年被车撞了,显得有点不方便,性格羞赧、内向,像调色盘上一团收缩的灰色,毫不张扬和醒目。他可能是女儿学校里最好的美术老师,平时开一辆银灰色的低价位的本田车。
现在是晚上,我行走在漆黑的巷子里,踩着地上的积水。这里的住户,以老人和租户为主。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有房子,住在更干净明亮的小区,留下他们年迈的父母在这里,只在周末或节假日来探望。再就是租户,在贤士花园农贸市场以及周围一带的小生意人,仅仅够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者,以外地人居多。这是片由数十栋密密匝匝的楼房构成的片区,分列在我行走的巷子两边,中间又有几条狭窄的小巷子通往外面的街道以及农贸市场。从地理上来看,是东邻贤士花园、南沿贤士横街、西邻永外正街、北沿玉带河的方圆几千余平方米的区域。这样的生活区在南昌市内不算孤例,是若干个类似陈旧生活区的一个缩影。
萧老师的画室在一楼,一栋老住宅楼的一室一厅,想来租金不会很贵。楼前沿着墙角摆着几张旧凳子、椅子,平时都是一些老人坐在那里晒太阳、聊天。门前停着一辆小四轮车,那是其中一个租户用来运载蔬菜的。我和几个家长,在漆黑的夜里,或坐在旧椅子上,或蹲在墙角,沉默着没有交流,都在看手机打发时间,等待孩子下课。下过雨的地面形成了水洼,椅子上湿漉漉的,空气中散发着一种陈腐的气味。听得到房间里电视机的声音、老人咳嗽的声音,不远处的玉带河席卷着城市的污水、从路面流下的雨水,顺流而下。我们听见萧老师的说话声,铅笔在画板上的唰唰声。几个家长,有男有女,年纪相仿,像秘密接头的地下工作者,在这个墙角会聚,除此之外,户外看不到别人。但他们并不交流,各自满怀心事,低头缅想。
雨似乎在某个时刻停了。天上乌云涌动,沉寂的夜潮湿、寒冷,人世间此刻在我心中泛起某种酸苦、复杂的味道,我似乎品尝到生活的不易。我们都是平凡之人,杯水悲欢,以匹夫之躯去泅渡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窄小的水域。因为偶然的原因,走到这陌生的墙角,在一段鸡肋般的时间里,让自己抛锚在这夜的岸边。远处是城市辉煌的夜景,灯火璀璨、车水马龙,而我们站在这城市灰暗的角落,闻着空气中陈腐的气味,在陈旧楼房的垂垂老者身边,在对身边暗红砖墙、满是锈迹的楼道扶手、矮楼、小巷、电线杆的凝视中,像个隐匿者、局外人。
有一次,我们站在墙角,夜色中,突然一个学生家长(一个女性),对我说,你女儿学了多久的画啊?我女儿坐在你女儿后面,她说你女儿画得蛮好的。我记得她有一张圆脸,短头发,眼睛大大的。当她突然问我的时候,我看到她架着腿,正斜坐在一辆支起来的电动车上。
脸
如果不在房子中,我们不会刻意注意到自己的脸。房子中的浴室镜、电脑屏幕、电视机里的镜像、在厨房漫不经心收拾时印在金属厨具上弯曲的投影,甚至陷入深思时仿佛从书本纸页上浮现出一张古老的脸庞,书架前用手指逡巡读物翻开的勒口上的作者头像,以及在睡眠中仿佛从天花板上纷纷向你走来的面影……此类种种,都在提醒着脸的存在。仿佛那是一本书,让你随时进入、阅读。而在户外、大街上、旅途中,你不太会关注自己的脸——你的注意力被外部的图像、声音所牵引。只有当你独处一室时,才会真正注意到它,你会习惯性地用手去触摸脸,在镜子里寻找那仿佛变得陌生、可疑的面孔,以便确认自己的形象。
阅读脸,这一行为,何其古老。有一度,我对博物馆里陈列的古铜镜充满兴趣,揽镜自照——隔着玻璃窗,想象那镜前的影像。博物馆通常灯光幽暗,那在地底下沉睡千百年的古铜镜,现在又换了个位置继续沉睡——每次走进博物馆,在铜镜前,我都难免产生一种穿透玻璃,拾起那枚镜子映照的冲动。铜镜斑驳,泛着绿锈,看起来完全失了光芒——不免让人深深怀疑,它能否清晰地映现美人的面容?这与我们在博物馆书画厅看到的,几近暗黄的美人图感觉一样——我们看不出那超凡绝尘的佳丽形象,就像是时光的做旧,给观者展示出一个过气的、暮气沉沉的美人,一个赝品,美人不可靠的替身。铜镜古老,仿佛容颜一经映照便迅速老去。而玻璃永远年轻——这是一种奇怪的物质,有时,我们在乡下见到那种古宅——也不那么古老,一百多年的历史,房子已经老旧、颓败不堪,但镶嵌在门扇、窗格间的玻璃(有些是彩色玻璃),却还像新的一样。而古铜镜却不会这样,它一经同主人埋入地下,便彻底黯然失色,拒绝再让别的形象在那曾经光滑冰凉的深处升起。
是镜子唤醒了自我的存在。镜子重叠的形象里产生的却是孤独。在你与妻儿老小欢乐共处的时候,镜子仿佛消失了。通常,只有在太太不在身边、女儿上学去了——唯独我一个人在家时,我才会听到镜子的呼唤——我会不自觉地走到它面前,看到里面那个有时睡眼惺忪、胡子拉碴、发如飞蓬,有时目光炯炯、满面春风、轻松自若的“我”来。无论是脸颊塌陷了,还是白丝增多了、眼圈更黑了,或是神情焦虑、若有所思,抑或脸上恢复了血色、显示出一种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脸,都在提供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证明。只有当你凝视自己脸的时候,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处境,并在那一情境中,对自己的状态做出反思。虽然镜子的属性是映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揽镜自照这一行为,得到的多是孤独。
我小的时候,对悬挂在乡间门楣上方的剪刀和镜子不解——如果镜子,不是为了使形象现身、显影,那镜子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我不知道,那里面藏着一种简朴但也深奥的有神论的认识——在人类学或民俗学意义上,这枚镜子不是为了照见,而是为了阻挡(使污秽和鬼怪不能进屋),具有驱邪避秽的功能。在神话故事里——无论欧洲、中东还是东亚,镜子都有着服务于超自然和异己力量而不仅仅是脸的传统。而神话的机能和怪力乱神的故事,都要通过脸来反映,只有在镜子里的形象得到确认,上述神话学的传说和故事才能成立。
有一度,我还对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这幅画感到不解。画家在精心地描绘一对富裕的新婚夫妇同时,在身后墙壁上还画了一个精美的镜子,里面却藏着画家本人的形象。如果说这一仿佛是美好爱情的“婚纱照”,葆有中世纪资产阶级兴起催生人文主义思潮的意思在里头,那么画家“恶作剧”式的在一幅充满着忠贞和宗教意义上的新婚场景里,插入自己的脸,似乎在消解着什么,是对爱情和忠贞的怀疑?是对资产阶级生活观念和情趣的戏弄?还是其他,则不得而知了。无疑,墙上的镜子拓深了画面的空间,使之具有无限循环下去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张隐藏在镜子里面的脸,也具有无限循环和增殖的可能性。画家似乎想要让自己在无限延伸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爱情和婚姻进行旁观和审视。
通常我独处的时候,唯有书和镜子,是使我受益的。我的阅读很宽泛(但似乎也很局限),我通常喜欢同时阅读好几本书,它们有的摊开在书桌上,有的折页放在沙发上,有的(经常是好几本)叠放在床头。至于哪本会成为睡前的读物,则不一定。也许,我在客厅里关灯准备去卧室上床时想好了阅读哪本书,但伸手拿起的却是另一本。我不能保证某本正在阅读的书能完全读完。我的书柜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加缪全集》,购来已有二十多年了,数次决心全部读完,但都是半途便丢下了——我又拿起了另外一本书。我习惯于(和满足于)这样一种阅读方式,仿佛在家里坐下来,随时可以阅读。当目光随着文字移动时,那书中的画面(伴随着自己的脸),会在镜子般的书页上浮现——没有哪一种方式,会比阅读文字更让人欣慰和满足。
有时我会突然中断阅读,将书搁在腿上,手指不自觉地轻轻滑过书页,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似乎还紧紧夹着某页纸张。我侧躺着,将眼镜摘下来,眼前一片模糊。我不断地进出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或站在浴室镜前凝思时,感受到阅读带来的短暂晕眩和幸福感。浴室的空间将室内的静谧放大,对音响的阻挡和排斥,是内心获得完整宁静的前提。帕慕克说:“我对着镜子阅读自己的脸。我的脸是罗塞塔石。”这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诏书的石头,分别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我看到镜子里的脸,不是历史的景深和衰落的文明,而是一种中年人——有着东方古老民族特征——寄予幻想和臣服命运的脸,是疲惫、犹疑,也是超然和平淡。有时我坐在桌前凝思——我的手机压在摊开的某本书上,手机光滑、黑色的镜面倒映着窗帘、天花板——往前俯视,一张戴着眼镜的脸在里面出现。通常我不会注意到这个形象,我在打开的笔记本前写作,我在写作《脸》这篇短文时,试图回忆自己的面容,仔细看白色的文档页面,有一张淡淡的脸的虚影,躲在文字后面。
脸和房子构成一种修辞、一种隐喻。脸在房子里无处不在,那是它窥探、自察、回忆的证明,脸在房子空间各个角落浮现——当它端详着眼前的绿植:蕨类、橡胶树、栀子花、金钱草、绿萝、菖蒲——当我现在,在自己家里回忆居住在郑女士出租屋里的绿植,我不能完全确认上述植物就是当时太太所种植的品种。我当时附身去看这些植物——太太出门远行,吩咐我照顾好这些花草,我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它们似的。我记不起它们搬进我们家时的模样——它们何以长成现在这个模样,我也一无所知。说实话,我对这些植物平常并不上心,我没有种植花草的习惯——这是太太的爱好,虽然,在这方面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次数多。我端详这些绿植,脸几乎淹没到里面去了——甚至在一个透明的球形玻璃缸里。我在那浸着植物根茎的水面上看到一张古怪的脸:一张对照顾花草没有信心的、冷淡的脸。
我也许应该想到,一张出现在出租屋中的脸,它与房子之间构成的修辞和隐喻,毫不稳固。事实上,这空气里,还浮动着许多消失的脸——虽然消失,但依然存在,就像那位尼德兰画家描绘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卧室里携手留下这一无法磨灭的瞬间——被画布照相般写实地留存下来,其实在那深处的墙壁镜子里,还隐藏着另外一张脸。
密语者
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尝试与小区更多的人进行交谈。交流的障碍,不仅对我,我发现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样如此。而有时,一个与人交流的愿望,像突然丢进湖面的石子儿一样,显得突兀和异样。有一次,在电梯里,住在我斜对门的一位女性(虽然她退休不久,但我很难用老太太这个词来形容她),暗中偷偷盯着我已经很久了,终于忍不住问起我来:你们是新住进来的啊?你多大啦?做什么工作啊?(短暂沉默)这电梯就是这样,老旧了,经常出故障。唉,过一天是一天。我起初对她稍微有些反感,对她的“盘问”感到不适(缺乏应有的尊重)。但过后一想,这未必不是出自好意,或者关心。她是个瘦高女性,短头发,黄白色的脸,穿着偏于中性化,一种政工职业者的形象。
我的这一看法在餐桌上得到印证。午餐时,我说起对门这个女性,出乎意料地,太太和母亲迅速把话题接过去了。她们遭遇了同样的“困窘”。太太和母亲也在电梯里,被这位女性善意地“盘问”(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方式)。同样地,母亲和太太感到了不适。母亲还用了老家一个词(恕我这里无法直述出来)来形容她,大意有多事、多言的意思。母亲来自小县城,一个长年工作在灶台和菜园的农妇,其貌不扬,有些拘谨和木讷,可以想见,在电梯里遭遇伶俐的女邻居的问话时的尴尬和难堪。我的太太是位观察多于言语的人,不爱讲话,喜欢独来独往,也不善于与人交流,但很有主见。她的形象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柔婉、和善的印象。当她进入女邻居的视野,两人在沉闷的电梯里,从14楼伴随着电梯哐当哐当的响声往1楼下坠,那双阅人无数的凌厉眼睛的注视和“关心”的问话,不可避免。这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家,应该是任何在电梯里引起她兴趣的人,都能获得的待遇。
她不像小区里其他的老人,一种随遇而安的、与小区的氛围贴合度很高的状态。她不是,像是一台老旧机器上松动的螺丝,总无法与机器完美地拧在一起。我见她不时地坐电梯上下,在院子里走两步,并不走远,又回到14楼,然后又下去。她像个满腹心事、焦躁不安的人似的(但她的神情却是一种恒定的平静表情)。
我们曾经离开过小区C栋一段日子。当我们重新回到这栋楼(已经从14楼变为9楼了),有一次,在电梯里,她“意外地”再次见到我,略显惊讶的表情写在脸上,同时“欣喜”地看着我,对我重新出现在她的视野毫不意外似的。她有个老伴,但我很少见他们一同出行,有那么两次,见到他们,一前一后,隔着好几米的距离。有一次,她主动说起她的儿子,是在外地(广州还是哪里)工作,给她生了孙子,但她不愿过去帮他们带,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原话如此)。她似乎习惯了不黏人的生活,同时也不喜欢别人黏她。她独来独往,缺乏交流,但又喜欢与陌生人攀谈。
她的老伴身上有种老干部的气质。机关生活似乎消磨了他们生活的情趣,连夫妻间的交流也变得那么冰冷。
而其他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譬如,在早餐店里。有段时间,我经常去那家福建馄饨店。如果是周末,我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就会长一些。那是个二十平方米的小空间,店主是位三十出头的小伙子,有一个助手——一位女性,看起来比他大几岁,从他们的表情和举止来看,不像是夫妻或者姐弟。总之,几年来,这对搭档一直配合着,没有拆散过。来吃馄饨的人——买菜的老妪、休息的上班族、学生、生活在周围的居民、老板和小生意者,他们在店里,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如果有,比如,有一次,我看到的是一对父子,儿子像是从外地回来,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像是交流职场之道和生意经,东拉西扯的,看起来很亲密,但又显示出这对父子平时疏于联系,有着亲情上的罅隙。我注意看,那位儿子,三十岁不到,比父亲更早地露出谢顶的迹象,他像是IT从业者。再有,就是恰好在店里遇到一对小区的邻居或者熟人,我们客气地交流两句,似乎也没有话再继续下去。沉闷的空气里,只听得到壁扇摇动的声音和调羹撞击瓷碗的声音。
惠民家电制冷维修部门前,倒常能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儿打牌,包括涵平衣铺、卡西形象设计、卤鼎记、爱婴堡、小熊水果店的店主们,在下午时辰,玩“梭哈”或“斗地主”。与其说这种“亲密”状态是由沟通、交流的愿望引起的,不如说是赌资的刺激所导致的。他们熟练地洗牌、切牌,将抓在手上的扇形扑克紧紧捏住,所有的眼睛以桌面为中心,在其中汇聚,而完全不管店里的生意。那些站在身后观看的人,有一种局外人的轻松和无压力状态下的愉悦——但久而久之,则变成一种乏味、单调和无聊。输赢不定和牌面的不可重复性,是这游戏能不断继续下去的“潜力”。这古老的游戏,考验人的,不仅仅是智力、记忆、观察力,也考验着人的耐心和脾性。玩牌的人,那种在游戏时的热乎劲,在散场时迅速转为冰冷,仿佛热情的火焰突然化为灰烬。那些从牌桌前离开的人,回到各自的店里,不再看对方一眼,更不多交一言。仿佛在游戏中的失误、失利,转变为了对对方的仇视和忌恨。
有个老妪,曾经是母亲麻将桌上的牌友,是个退休老师,每天接送读小学的孙子。她不仅与母亲一起打麻将,还曾一起去理疗店里听讲座,受到骗子的洗脑。有一次,我们一起在电梯里,突然,另一位老人——一位退休老干部模样的老头,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小区周边哪有什么好学校啊,都是些垃圾学校。这是个平素看起来“优雅”、持重的老头,脸上有种养尊处优的神情。这一瞬间,我发现,母亲的麻友——这位老太太,脸色突然变得绛紫,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焰火。我似乎也感到震惊,不知道这老头突然为何这样说——他说的也许是客观事实。但潜台词是日益增多的陪读的租户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还是他自己的感受,抑或其他什么缘由?总之,他失礼的表现,使这位送孙子去上学的退休老师——老妪,感到了难堪和愤怒。而老头仿佛低语一般,脸上是云淡风轻的表情,貌似无心,只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讲了那么一句,却不知这句话像刀子一般扎入了老妪的心。
我曾读过一篇小说,对作者阐发的“门槛理论”印象颇深。“在人们通常的意识里,门槛是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过渡”,“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我在贤士花园居住的时光,正是具有“门槛”性质的。这特别的空间,和特别的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最后,我似乎颇留恋这个“门槛”,待在里面不愿出来了。当我离开它时,我显示出恋恋不舍。在南昌工作生活二十余年,在贤士花园居住的几年时间,才真正让我与这座城市建立较为深入的联系。在居住过的其他小区,都没有此种感受——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过客,而不是它的居民。当我以一个租户的身份住进贤士花园小区,我反而拥有了更多的市民——而非过客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并不以我与人际关系的深入展开为特征,相反,我在这里,几乎与人没有交集,平时小心翼翼,尽量隐藏自己。
我经常回望,在老家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的情形。那是个建筑在山顶上的中学——仿佛华莱士·史蒂文斯著名的诗歌《坛子的轶事》所描述的:“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那中学,也仿佛成为某种哲学的象征,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在这个中学教书的时间,与我在贤士花园生活的时间差不多。教书时,我也很少与人交流——像个密语者。阅读和写诗,伴随我度过那时间。我是周末骑车下山,回到县城家中看望父母,周一再骑车回学校。每周都是如此。我在贤士花园,获得了如同早年乡村中学般的感受。两者都具有“门槛”的性质。
我试图去勾画贤士花园人们的交流,以及人际关系的展开,却发现用一个社会学用语“内卷化”来形容,较为恰当。每个人都不缺少交流的愿望,但这种愿望经常被中断、悬搁,对他人的关切有时却异化为一种“干涉”。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事实上的密语者。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1972年6月生,出生于江西莲花县,现居南昌。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昼与夜的边缘》《寻梦婺源》《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等。
来源:《芙蓉》
作者:李晓君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