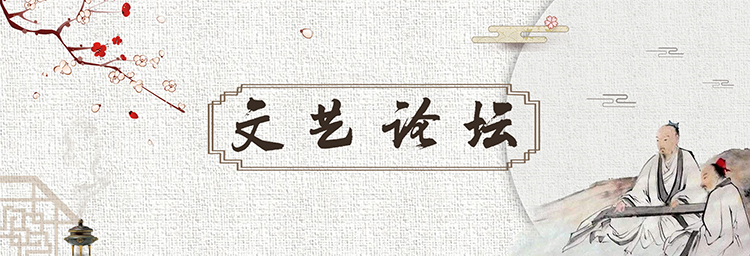

五四早期“小诗”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文/朱颂 王金黄
摘 要:五四早期的汉语“小诗”所受到外来影响的直接渊源是日本诗歌,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小诗”在创作观念、体式、语言和意象的选择、情感表征等多个方面,都受到日本和歌、俳句的影响,从而产生出许多新的特质。探讨“小诗”所受外来诗歌的影响,对当下中国新诗创作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五四“小诗”;小诗运动;日本诗歌;外来影响
五四早期的小诗运动为中国新诗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小诗”,周作人在《论小诗》中将其定义为“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用来表达我们日常生活里忽然而起,忽然而灭,不能长久持续但却一样真实的感情;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①郭沫若、康白情、俞平伯、徐玉诺、沈尹默、冰心、宗白华、何植三、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谢旦如、谢采江、钟敬文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小诗”作者。除了冰心的《繁星》《春水》,还有宗白华的《流云》、刘大白的《旧梦》、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汪静之的《蕙的风》、湖畔诗社的《湖畔》和海音社的《短歌丛书》等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诗集。朱自清在《杂诗三首》之《序》中说:“从前读周启明先生《日本的诗歌》一文,便已羡慕日本底短歌;当时颇想仿作一回……”②余冠英在《新诗的前后两期》中写道:“‘五四’时期,摹仿‘俳句’的小诗极多。”③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也谈到了当时“小诗”创作的盛况:“周作人介绍了他的所谓日本的小诗,居然有数不清的人去摹仿”,“大家一起争着传诵,争着翻译,争着模仿,犹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得到一本古典的稿子”。④直到1924年的前后,持续了三年的小诗运动才衰落下去。1927年,朱自清在《新诗》一文中指出:“周先生的短歌俳句的翻译,虽然影响不小,但他们的影响,不幸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泰戈尔的翻译,虽然两方面都有些影响,但所谓影响,不幸太厉害了,变成了模仿”;“这自然都是介绍者始意所不及的。这样双管齐下的流行,小诗期经两年卒中止”。⑤朱自清指出了小诗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即“小诗”对日本短歌、俳句的借鉴只停留在形式的肤浅层面,而对泰戈尔诗歌又仿效过度。果真如此吗?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五四早期的“小诗”这个风靡一时的“新诗坛上的宠儿”、探寻它的精神与艺术魅力时,有必要首先厘清“小诗”受到了何种外来影响,以及这种外来因素与“小诗”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与艺术联结。
五四运动落潮后,诗歌形式逐渐趋向于泛滥无序的状态,诗人们开始寻找新诗的表达方式。周作人是五四早期仅有的日本和歌与俳句翻译家。早在1916年,他就发表题为《日本之俳句》的短文,后来又写了多篇译介和歌、俳句的文章,如《日本的诗歌》(1921)、《日本俗歌五首》及其《译序》(1921)、《一茶的诗》(1921)、《啄木的短歌》(1922)、《日本的小诗》(1923)、《日本的讽刺诗》(1923)、《日本俗歌六十首》及《译序》(1925)等。日本传统的和歌、俳句,在语言和诗型上与中国古诗差别很大。和歌是5、7、5、7、7五个句段,共三十一个音节;俳句是5、7、5三个句段,共十七个音节,另有音节数及韵律的修辞方法,因此翻译的难度极大,极少有人问津。只有周作人在此方面有知难而进的勇气与日本文学方面的修养。1921年,在《日本的诗歌》一文中,周作人说:“凡是诗歌,皆不易译,日本的尤甚: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鸠摩罗什说同嚼饭哺人一样;就是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也正如将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变,但此外别无适当的办法。”⑥因此周作人所翻译的和歌、俳句,采取了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办法,“只用散文说明大意”,撇开了原诗在形式上的特点。到1922年,郑振铎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至此,中国诗坛掀起了小诗创作热潮,史称“小诗运动”。
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中,冰心说她的“小诗”创作主要是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她偶然看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充满的诗情画意和富有哲理的语言,让她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⑦。《飞鸟集》的天然美感和她自己这些零碎的思想,便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声无调的音乐——《繁星》由此诞生。而另一位小诗运动中的佼佼者宗白华,则喜欢唐人绝句中闲和静穆的境界及天真自然的态度,并自述他的小诗和短诗是受了唐人绝句的影响。他似乎也受到泰戈尔园丁集诗的影响,因为他曾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朗诵泰戈尔《园丁集》,并在《我和诗》中专门评价泰诗:“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⑧。因此,周作人在《论小诗》中总结说:“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与享乐。”⑨。冯承藻认为,对“小诗”创作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要推印度泰戈尔的小诗。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比泰戈尔的诗晚出两三年,因此,“周作人对小诗创作绝非开路先锋,他只不过是在已经形成的小诗运动中推波助澜而已”⑩。在《论“湖畔”派的诗》一文中,陆耀东认为“小诗”的来源有三:“一是日本的俳句与和歌,二是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三是中国古代的小诗。”{11}他认为冰心的《繁星》《春水》属于第二种,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属于第三种,“湖畔”派作品中的小诗,接近于第一种,又自成一派。王向远在分析了“小诗”的来源之后,所得观点与陆耀东的基本一致,他也将中国“小诗”大体分成三派。一派较多地受日本和歌与俳句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具体的、写实的、感受的、天真自然的,代表作是湖畔诗社的《湖畔》和海音社的《短歌丛书》;一派较多地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抽象的、冥想的、理智的、老成持重的,其代表诗作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还有一派主要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如宗白华的《流云》和俞平伯的《冬夜》等。王向远指出:“泰戈尔的《飞鸟集》本身就是在日本俳句的影响下写成的”。{12}1916年,泰戈尔出访日本时接触并了解了日本的古典俳句,尤其对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赞叹不已:“够了,再多余的诗句没有必要了”,“日本读者的心灵仿佛是长眼睛似的”;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写道,“这些罕见的短诗可能在他(泰戈尔)身上产生了影响他应(日本)男女青年的要求,在他们的扇子或签名簿上写上一些东西,……这些零星的词句和短文,后来收集成册,以题为《迷途之鸟》(现译成《飞鸟集》)和《习作》出版。”{13}罗振亚在《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生成》中有进一步追溯:泰戈尔那些简短美妙的哲理诗是受日本俳句体的启示,并在俳句的影响下写成的,其清新的自然气息、浓郁的宗教氛围和频发的哲思慧悟,有梵文化和“偈子”背景的制约成分,更多来自日本俳句自然观和禅宗思维的隐性辐射。因此那些自以为受惠于泰戈尔滋养的冰心、郑振铎等小诗诗人,实则是间接承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和洗礼。{14}周作人和泰戈尔,都是现代史上中日交流的两座文化桥梁,一显一隐地存在着。因此,“小诗”外来影响的主体是日本俳句,受到印度泰戈尔诗歌的影响,实质是间接受到日本诗歌的影响,周作人对日本和歌俳句的翻译和介绍,直接促成了“小诗”的产生。
20世纪初,随着日本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日本和歌与俳句的革新已经完成,已由“古诗”向“现代诗”转变,他们保留了原有的诗形,又获得了现代精神。周作人在多次翻译和介绍日本和歌与俳句之后,把日本诗歌的特点总结概括为“诗思的深广”和“诗体的简易”,以及“感觉敏锐,情思丰富,表现真挚,具有现代性”{15}。本文将从创作观念、体式、语言、意象的选择和情感表征等四个方面,针对“小诗”所受日本诗歌的影响问题,力求进行认真的辨析和深入的考察。
一、创作的观念:超政治性与实写情景
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在于“风雅”,把政治问题放在个人生活的范畴里来加以领会的是“风”,把人类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是“雅”。“风雅”观在中国文学思想中一直被继承下来。中国古诗讲究“风雅”,首先要考虑政治观念,其次是古典美。然而,日本诗歌有意地回避政治问题,它在吸收中国的“风雅”观时,完全去掉了政治性的东西,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提到“风雅”,日本人首先想到“典雅”和“消遣”,其次是追求游离于人生之美的心情。铃木修次指出:“日本人的文学范围,一直存续于家族式的同族集团中。从宫廷妇女社会、短歌团体、连歌众人座集团等等,到同人刊物的社会里,总的说来,是一种同族的社会,也是个封闭的社会。在日本文学界里,异邦人式的土气,常常遭致嫌恶,同人之间,一般不容许他人介入。只有通晓共同的前提与趣味的伙伴,才能组成‘行家’的社会。”{16}如果诗人开始关心与其他势力的均衡或统治等政治问题时,则会有损于同族之间的信赖。因此,日本文学似乎总是异乎寻常地避免诗歌创作与政治意识的纠缠。
日本诗歌注重实感,认为“愍物宗情”的情趣最重要,共有五项,即“真实、特殊、清新、幽雅及美”{17}。而古典俳句尤其重视写实,上岛鬼贯就曾指出:“真实之外无俳谐”;松尾芭蕉也曾强调过,“松的事向松学习,竹的事向竹讨教。”{18}因此,日本诗人要求自己尊重客观事物的“真”,用审美的眼光去关注大自然的一切。他们以亲和的感情去注视自然,认为自然是生命的母体和根源,人生与自然密不可分,相互依赖依存,和谐地共生于同一宇宙中。正如周作人所言:“新派歌人的著作,原是十人十色,各有不同。芭蕉提倡闲寂趣味,首创蕉风的俳句;芜村是一个画人,所以作句也多画意,比较的更为鲜艳;子规受了自然主义时代的影响,主张写生,偏重客观。表面上的倾向,虽似不同,但实写情景这个目的,总是一样。”{19}
受到日本诗歌影响而产生的中国“小诗”,也不再关注政治问题,不再注重表达明确思想,而只是捕捉眼前景色和瞬间的现象,来抒发刹那间的感兴。周作人认为“小诗”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几乎是迫于生理的冲动。”{20}自古以来,中国源远流长的山水诗都以自然为中心,只是后来因改朝换代、治乱更迭的社会现实而萎缩;直到此时,才得以在日本俳句的外力刺激下逐渐复苏。梁宗岱呼吁——“到民间去,到自然去”{21},一时间写景诗极度繁盛,如“露珠儿要滴了,乳叶儿掩映,含苞的蔷薇酿着簇新的生命”(应修人《含苞》)、“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冰心《繁星·七五》)、“插在门上的柳枝下,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冯雪峰《湖畔·清明日》)、“新谷收了,田事忙了,萤火虫照着他夜归了”(何植三《农家短歌·三》)、“落日斜照到秋柳上,看哪,黄叶要在残光中飞舞了”(谢采江《野火·三》)、“太阳的光/洗着我早起的灵魂。天边的月/犹似我昨夜的残梦”(宗白华《晨兴》)等。“露珠”“叶儿”“蔷薇”“海”“柳枝”“萤火虫”“落日”“黄叶”“太阳”“残月”等等本属平凡的自然之物,一旦由诗人倾注了情绪和感兴,便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宗白华希望诗人要“直接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感觉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因为“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声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22}而在五四时期的小诗创作中,人们也不太关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而是以诗人的自我情感和自我想象中为中心进行艺术表达,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对于历史有所忧思,有的对于自然有所感悟和发现,有的对于人生有一些感叹,有的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感性记录,有的是对苦难人生的一种同情和怜悯,所有这些都让当时的小诗创作比较具有多样化和丰富性的特征。而这样的特点正是从日本诗歌而来的,是一脉相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二、体式与语言:小巧简练而余韵悠长
日本民族所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人们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并处在温和的自然环境的包围中,养成了纤细的感觉和淳朴的感情,乐于追求小巧和清纯的东西,“以小为美”“以小胜大”,追求一种“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这种审美意识首先体现在日本的和歌与俳句之中:和歌31音节,句调是五七五七七;俳句更短小,只有17音节,句调是五七五,言而不尽,言辞简短。“万事以不过分深入为宜。达人决不因自己通晓事理而故作渊博,喋喋不休”{23},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受到和歌与俳句的影响,“小诗”的诗形也顾名思义地小巧起来。周作人认为,小诗只是限于“一行至四行的新诗”{24}。然而,古远清认为,周作人对于“小诗”“有点武断”,冰心的“小诗”最短的两行,最长的十八行,一般是三至五行;“小诗”既然是自由诗的一种,我们大可不必在行数上做过于呆板的规定。{25}罗振亚则将其定义为:“用一到数行文字即兴表现一点一滴的感悟、一时一地的景色”。{26}
由于日本诗歌在修辞上与中国古诗差别很大,中国古诗讲究对仗,日本诗歌中几乎没有对偶的意识。此外,中国古诗还极为重视“押韵”,而日本诗歌却能根据一定的音节数自然地形成韵律。周作人所翻译的和歌与俳句,采取了只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办法,他基本上撇开原诗在形式上的特点;但在韵律方面,“小诗”诗人们的确从外国诗歌中受益颇多。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泰戈尔的诗歌,对西行上人与松尾芭蕉的诗句评价很高,认为诗是纯粹的内在律,因为“我们读泰戈尔的《新月》《园丁》《几丹伽里》诸集……外在的韵律几乎没有”{27}。在情调和声调上,冰心小诗的节奏主要表现为沉静、柔和与自然。“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在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冰心《繁星·一五九》)这首小诗就颇具代表性,情感先扬后抑,外形结构对称,语言循环反复,有余音绕梁之感。
然而,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影响不仅在形式和韵律上,更在余情余韵的表达上。日本诗歌几乎没有对偶的意识,也少有“押韵”,日本诗人把这种单纯韵律结构的短诗型,打造成情绪上具有多义性的结构体。尽管短歌、俳句是世界上最小巧的诗歌形式,音数和句数都有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它的简练、含蓄、暗示和凝缩,却能使能人联想到绚丽的变化和无限的境界。因而,它更兼具“以小胜大”的无穷趣味和隽永余味。周作人就曾在译介日本诗歌时指出,日本诗歌的长处在于“将最好的字放在最好的地位”,将要点捉住,利用联想,暗示这种情景,能令人感到言外之意,“正如寺钟一击,使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的心中永续地波动”{28}。松尾芭蕉的俳句都重在暗示而不在明言,诗中之意无不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所以“说尽”这一句话,便是批评毫无馀蕴的拙作;而中国“小诗作者们对俳句的简洁含蓄、朴素凝练、余味深长、满含着悟性的象征的抒情是努力仿效的”{29}。诸如“芭蕉姑娘呀,夏夜在此纳凉的那人呢?”(汪静之《蕙的风》)、“声声不息的鸣蝉呀/秋/一声声长此逝了”(郭沫若《鸣蝉》)、“风吹皱了的水,莫来由地波呀,波呀”(汪静之《波呀》)等等,都深得俳句精髓,使用了切字,简洁干净,通过捕捉一时且容易消失的现象,而感到快意。“小诗”之余情、余韵如同日本俳句一样,“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微榄,越吃越有回味。”{30}这样一种特点的形成,虽然与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相关,但也是直接来源于日本的诗歌,因为不论是周作人还是朱自清,他们对于日本的诗歌都是相当熟悉的,当然日本的诗歌艺术最终也是来自于中国古诗,来自于中国古诗里的某一部分。就语言的简练而言,中国古诗特别是七言八句,或五言四句,是不可能再简的了。然而,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俳句,一共只有十七音,有的只有一行,长的也不过三五行,实现了艺术上的更大留白与压缩。而五四时期的许多小诗,特别是像宗白华和冰心的部分作品,与日本的短歌的俳句,在体式和语言上特别接近。
三、意象选择:交错官能与立体视觉
诗人对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全新的意象中。梁宗岱说:“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藉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31}意象是现代诗歌艺术中最为常见的手法,“新派歌人的著作,原是十人十色,各有不同。但是感觉敏锐,情思丰富,表现真挚,同有现代性。”{32}日本诗歌中意象的官能交错与视觉立体的特质便是这个观点的最好证明。
意象“可以是视觉的,可以是听觉的”,或者“可以完全是心理上的”;其中,“官能的交错”,就是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意觉的界限打破,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33}如“比远方的人声,更是渺茫的那绿草里的牵牛花。”(与谢野晶子)这首俳句将远方不清楚的人声与牵牛花淡淡的颜色进行比较,从而使视觉与听觉混杂在一起。除此之外,日本诗歌还极其钟爱一种触觉中的触觉,即“渗透”的感觉。“秋风袭人萩花落,夕阳返影入壁中。”(永福门院)光线是不可能渗透进墙壁内的,这里却将夕阳的余光,慢慢地在青碧上变淡直至消失的自然现象,描写为夕阳的余光消失在墙壁里面,多么令人震撼的触觉呵!“深山幽静,蝉声渗入岩石中。”(松尾芭蕉)就在蝉声渗入坚硬的岩石之时,突出了蝉声的尖锐与高亢。“官能的交错”使物理科学中难以置信的现象,在诗意的空间里变成一种感性的真实。“暗水流深分岩去,幽静水声渗花香。”(凡河内躬恒)流水在黑暗中分开岩石,表现出了一种敏锐的触觉;而流水的声音渗进了花香,则表现了听觉和嗅觉的互通。
同时,意象还具有异常的视觉性,能够建构起一种立体的视觉感。首先,意象具有一种视野逐渐缩小的立体感。“在东海小岛之滨的白沙滩/我孤寂、哭泣/逗弄着一只蟹子”(石川啄木),诗人连用三个“的”将四个空间意象“东海”“小岛”“海滨”“沙滩”连接起来,然后一层层逐渐压缩。把辽阔无际的“东海”缩小至“小岛”,然后把“小岛”缩小至“海滨”,“海滨”缩小至“白沙滩”,层层压缩,直至压缩成一个点——“蟹”的甲壳,最后用“我哭湿了衣襟……”把一片汪洋大海变成了一滴眼泪。“春天的雪花/软绵绵地落在了/银座街后的三层瓦房上”(石川啄木),诗人所描写的景物——银座被渐渐缩小,最终视线停留在银座街一座砖造三层楼房的顶上。其次,诗人还可以通过透视法来观察意象。小林一茶俳句中的视觉就具有着透视性,他常常透过“洞孔”来观察物体,而这种通过“洞孔”的意象来看世界的视角,颇为新奇有趣。
其实,自六朝以来,意象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出:“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34}与日本诗歌相比,中国古诗中“比”“兴”往往难以独立成诗。受日本诗歌的影响,中国“小诗”中“比”与“兴”却能够独立成诗,捕捉眼前的景物,摄取刹那间的感兴,以象写意,具有“官能的交错”的特质。“月落时/我的心花谢了,一瓣一瓣的馨香/化成她梦中的蝴蝶。”(宗白华《流云小诗·月落时》)诗人将低落的心绪比作凋谢的花,又将花瓣的香气比作梦中的蝴蝶,意觉、视觉、嗅觉的互通。“我底洁白的心儿,就给一缕悲哀的情丝,缠在伊墓头青草上了!”(应修人《忘情》)在这首小诗中,诗人的意觉与听觉是互通的。“她静悄悄的眼波/悄悄地/落在我地身上。我静悄悄的心/起了一纹/悄悄地微颤。”(宗白华《流云小诗·眼波》)眼波落在身体上,激起了诗人心灵微微的颤动,触觉“渗透”且互通。可见,“小诗”诗人们通过捕捉眼前的景物,提取一瞬间的感兴,创造了一个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意觉互通的感觉世界。
与此同时,诗人们也聚焦于意象的立体视觉效果。“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明月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繁星·七十一》)从“园子”到“藤萝”,再到“母亲的膝上”,空间逐渐缩小,却抒发出温馨而深厚的母女之情。宗白华的“我筑室在海滨上:紫霞作帘幕,红日为孤灯。白云与我语,碧月照我行。黄昏倚坐青石下,蓝空卷来海潮音!”(《流云小诗·筑室》),“紫霞”“红日”“白云”“碧月”共同建构了一个辽阔的海滨空间,激发着读者的审美想象。谢采江的“落日斜照到秋柳上,看哪,黄叶要在残光中飞舞了”(《野火·三》)在这首诗中,“落日” “秋柳” “黄叶”“残光”好像一张动感绚丽的彩色立体照片,让人思绪万千。“太子塔落影在莲衣池里,二只白鹅游上了塔尖,石路上有几声沉重的脚步。”(旦如《苜蓿华》)诗人视角奇特,从池水中看塔,“白鹅”游上了“塔尖”在水中的倒影,情趣顿生,从而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官能交错和立体视觉,在中国古诗中是不明显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苏东坡还是黄山谷,在语言上和体式上也少有这样的追求。只有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歌,具有部分这样的审美特征。而日本由于自己的岛国文化和人生瞬间的感悟观念,对于诗歌以及其他艺术有这样的讲究,并且在俳句和短歌中表现特别明显,因此,我们认为五四“小诗”中所出现的类似的审美特征,主要是来自于日本诗歌,而不是中国自己的传统。
四、情感表征:丰富的童心与童趣
由于日本列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日本较少受到外敌侵略而能够幸运地享受国内和平,从而使人们相信纯粹自然的力量。再加上日本春秋两季的气候富于变化,动植物的种类也丰富多样,这才形成了日本人自然崇拜的观念。与之辉映的是,日本歌人咏物的对象,从日月风雨、霜露雪雷到山河水田、花鸟红叶;从虾蝉蟋蟀、柳梅榛松到荷叶棠棣、云雾烟霞;可谓无所不包。纪贯之在假名序中指出,“和歌以人心为种,威于万言。……花间黄莺鸣,水边河蛙叫,万物皆发歌谣。无须假力,可撼天地,感鬼神,和男女,慰武士者,歌也。”{35}和歌的“种子”萌发自“人心”,然后以千变万化的语言形式,来表现自然万物的变化,无论是于花间婉转的黄莺,还是在水边欢唱的河蛙,所有的生命都无一例外成为了动人的歌谣。
在俳句中出现的虫鱼禽之类,数量极大。仅《岁时记》中,夏季的昆虫就有蝉、蜻蜓、吉丁虫、亮绿丽金龟、独角仙、灯蛾、班蝥、蚜虫、蜈蚣、天牛、异色瓢虫、苍蝇、蚊子、蚂蚁、蜘蛛、衣鱼、白蚁、玻虫、蜗牛、孑孓、水蛭、海蛆、夜光虫等等。此外还有蚊帐、蚊香、苍蝇拍、跳蚤药、诱蛾灯等,与昆虫有关的词语。自从俳谐产生之后,多种多样的小动物成为了日本诗歌表现的对象;诗人们在曾经被认为是卑俗的东西中发现了诗趣,以一种滑稽的态度来处理眼前的事物。
周作人最喜欢小林一茶的俳句,因为它“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一茶“将动物植物,此外的无生物,森罗万象,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是以万物为人,一切都是亲友的意思。”{36}周作人还翻译了一茶的俳句文集《俺的春天》,原诗中歌咏动植物的诗句随处可见,尤其是有很多歌咏鸟兽虫鱼的俳句,例如“山雀”“啄木鸟”“蜻蜓”“青蛙”“蝗螂”“火虫”“蝴蝶”“蚊子”“苍蝇”“跳蚤”“蚂蚁”等等,这些俳句无不包含了一茶对于幼小生命的广博之爱。在敏锐观察的基础上,周作人怀着对昆虫小生命的爱意,创作了《山居杂诗》,诗人或同情“苍蝇”,或歌咏“石榴”“藤”“柏树”“银杏”“梅的果实”“核桃”“松叶之菊”“槐树”“白果”等植物,或描写“黄蜂”“小虫”“蠓虫”等小虫类,丝毫不逊色于一茶。他把弱小的动植物视为同类、视为朋友,在《湖畔》中也随处可见此类小诗;诸如“蚱蜢儿,我也不能不怜你们呵!”(应修人《暴风去后》)“雨止了,操场上只剩有细沙。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应修人《雨后的蚯蚓》)等等。
一茶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孩子气”的俳句,独具天真的童趣。高岛平三郎说一茶是“小儿诗人”,而周作人说一茶是“子烦恼”的诗人,其诗表现了对于孩子和弱小生命的深刻同情。实际上,在《湖畔》中,也有许多“小诗”充满了这种天真的孩子气,如“伊香甜的笑,沁入我的心,我也想跟伊笑笑呵”(汪静之《笑笑》)“亲爱的!我浮在你温和的爱的波上了,让我洗个澡罢”(汪静之《爱的波》)“几天不见,柳妹妹又换了新装了!——换得更清丽了!”(应修人《柳》)“可爱的小孩儿,采了几些草儿,手里捏一枝,头上戴一朵。”(汪静之《路情》)这些由中国诗人创作的五四“小诗”无不素朴天真、稚气扑人。胡适就曾指出,这些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37}。事实上,周作人也写过多首直接以儿童为主题的小诗,包括《对小孩的祈祷》《儿歌》和三首同名诗《孩子》等,或天真清新,或婉转悲悯,表达了对儿童的关注。“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周作人《对小孩的祈祷》)诗人在儿童身上发现了“真正的天性”,他祈祷儿童能够为自己和先人赎罪。“小孩儿,你为什么哭?你要泥人儿么?你要布老虎么?也不要泥人儿,也不要布老虎;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鸦,哇儿哇儿的飞去了。”(周作人《儿歌》)这首“小诗”则充满了淳朴生动的童心和童趣。中国古代诗学中有“虚静”说,后来又有“童心”说、“赤子之心”说,然而中国古代文学中始终少有真正的儿童诗;直到现代,周作人才将自古流传的“童心”说理论,付诸于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日本诗歌的浸染下,“小诗”作为一项诗歌革新运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禁锢,在创作观念、体式和语言、意象的选择、情感表征等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而并非如朱自清所说“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38}。但是由于模仿者甚众,难免有粗制滥造者,泥沙俱下,故而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有些“小诗”成了纯粹的说理诗,缺乏情感,对于“闲寂”精神没有很好把握,缺乏幽深的余韵。1923年,郭沫若批评“小诗”肤浅随意:“目今短诗流行,甚者乃类小儿说话,殊非所取。简单的写生,平庸的感想,既不足令人感生美趣,复不足令人驰骋玄思,随随便便敷敷衍衍,在作者写出时或许真有实感随伴,但以无选择功夫,使读者全不能生丝毫影响。此种倾向我辈宁可避免。”{39}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也曾受到闻一多、茅盾、梁实秋、成仿吾等人的质疑。闻一多认为“哲理本不宜入诗”,“国内最流行的《飞鸟》,作者本来就没有把它当作诗。”{40}茅盾则认为冰心“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41}梁实秋在《<繁星>与<春水>》中称冰心是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训者”,认为“《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的便成一集”,因此,“《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42}到1923年,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对五四初期译介日本小诗、创作上模仿日本小诗的“小诗热”进行不留情面的否定。他以夏目漱石“情绪是文学的骨髓”的观点,对和歌、俳句进行了严厉的斥责,甚至完全否定了“小诗”的哲学化倾向:“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他终始……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与感而不在使我们理解”;因此,“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是不对了”,这样的哲理诗,更加难以激起读者的感兴。{43}
纵观中外诗歌的创作历史,诗歌的艺术特征是由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所决定的,而民族的基本性格则是在这个民族的历史、风土与文化形态的构成和动态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民族的历史、风土的要素不同,文学表现的特质也就有所不同。正是由于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的岛国文化,日本才会形成俳句和短歌这种细腻闲寂、余韵悠长的诗歌形式。以长江黄河为基础的气势雄伟、广博宏大的中国文化,决定了冰心、宗白华等人创作的“小诗”,与日本诗歌迥然不同。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审美形式,“小诗”一度风靡于20世纪20年代,并在抗战时期以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的形式,化为一声声嘹亮的号角;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一次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而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以许多新的作品屹立于诗坛,足以证明“小诗”自身的独特美学价值,因此,五四时期的“小诗”与小诗运动,对于当代中国的新诗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朦胧诗时期有一些诗人的作品是关注政治的,如北岛和顾城的一些小诗,政治性比较强,当然是内化的一种存在。“小诗”发展到了今天,由于网络的发达与自媒体的发展,参与诗歌写作的人来越多,在网络上创作和发展长篇作品的可能性不大,许多长篇小说也是以连载的方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因此,小诗创作的兴盛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现实。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诗人们就要从五四时期的小诗运动中吸取力量,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如在体式、意象、语言、情感、内容、审美方面有更多的讲究,从而发展出新时代的全新小诗创作。“小诗”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在历史上得到自己的地位,是因为它符合诗歌艺术表达的需要,符合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也符合现代人的生存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诗不可能与小说、戏剧、散文去比长短,诗本来就是短小的、精致的、精美的,而五四时期的“小诗”就是这四个方面的集中体现,未来中国的汉语小诗创作,也只能是如此。
注释:
{1}{9}{20}{24}周作人:《论小诗》,原文署名仲密,《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第6卷第29期。
{2}朱自清:《<杂诗三首>序》,《诗》1922年第1卷第1期。
{3}余冠英:《新诗的前后两期》,《文学月刊》1932年第2卷第3期。
{4}{43}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923年第1期。
{5}{38}朱自清:《新诗》,原文署名佩弦,《一般(上海1926)》1927年第2卷第2期。
{7}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诗刊》1959年第4期。
{8}宗白华:《我和诗》,《文学(上海1933)》1937年第8卷第1号。
{10}冯承藻:《“小诗运动”与冰心的小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1}陆耀东:《论“湖畔”派的诗》,《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
{12}{29}王向远:《中国现代小诗与日本的和歌俳句》,《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1期。
{13}[印度]克里希纳·克里巴拉尼著,倪培耕译:《泰戈尔传》,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317页。
{14}{26}罗振亚:《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6}[日]铃木修次著,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17}{36}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7·日本管窥日本·日文·日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第232页。
{18}[日]正冈子规著,王向远、郭尔雅译:《日本俳味》,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21}梁宗岱:《诗与真》,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页。
{22}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8期。
{23}[日]吉田兼好著,王新禧译:《徒然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04页。
{25}古远清:《小诗:一幅令人注目的文学风景》,《名作欣赏》2017年第19期。
{27}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6}{15}{19}{28}{32}周作人:《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5期。
{30}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宇宙风》1936年第25期。
{31}梁宗岱著,马海甸主编:《梁宗岱文集·评论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33}汪耀进:《意象批评》,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34}刘勰:《文心雕龙》,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35}[日]大冈信著,尤海燕译:《日本的诗歌其骨骼和肌肤》,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7}胡适:《“蕙的风”》,原文署名适,《努力周报》1922年第21期。
{39}郭沫若:《丝雨》,《心潮》1923年第1卷第2期。
{40}闻一多:《泰果尔批评》,《文学旬刊》1923年第99期。
{41}茅盾:《冰心论》,《文学(上海1933)》1934年第3卷第2期。
{42}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创造周报》1923年第1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编号:16ZDA2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