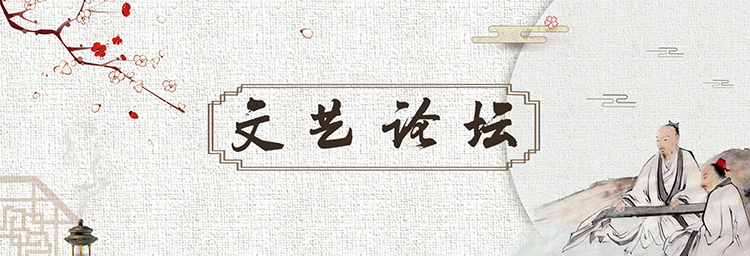

《修改过程》: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文/李作霖
摘 要:《修改过程》是韩少功继《马桥词典》《日夜书》之后推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具有现实主义“回归”意向的历史小说。作者以马湘南、楼开富、史纤等人的身世浮沉折射四十年当代中国的沧桑巨变,又从历史视域阐释人物的人性异变,从而使历史与虚构相得益彰。从虚构形式而言,韩少功的小说语言众声喧哗、多声对话,最终形成和谐的艺术体系,而引人注目的元小说实验难言成功。
关键词:《修改过程》;历史;虚构;元话语
在《日夜书》出版5年之后,《马桥词典》出版22年之后,韩少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如果说《马桥词典》是以词语为触发点展开的对马桥人事的记忆书写,《日夜书》是对下放于白马湖的“知青”一代的三十多年身世沉浮的历史实录,则《修改过程》是以湖南师范大学77级中文系的同学为原型,书写从大学校园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展开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同样是“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然而最新的这一本书,却是含泪的笑,是光荣的颓败,是假作真来真亦假,是历史的虚幻。
所谓“修改过程”,专业读者一般认为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生就是不断被历史修改的过程,二是写作也是个不断被修改的书写过程。这既可以做抽象的玄学一样的理解,像萨特所批评的“灵魂的信息”一样作为心灵鸡汤传达给青年读者,又可以做具体的历史的理解,它所谓“人生的修改”是书中所录的77级中文人所经历的人世沧桑,他们既怀揣“理想国”和“施工图”修改了共和国的历史,又被体制和市场无情地修改,宏阔的历史修辞变成一地鸡毛,变成似真还假的滑稽剧,它所谓的“写作的修改”,具体指77级中文系的故事撰稿人肖鹏对《修改过程》的修改,他有时是因为书中人对号入座引起麻烦被迫修改,有时却是因记忆和想象的驱动尝试更有趣的写法而修改(比如给人物行状设AB章让读者选择)。
我从未在公共传媒或私人场合听韩少功先生谈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也没听他说这本新作想表达什么。我所熟悉的他向来的观点是:我想得清楚的就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就写成小说。既然我写的是小说,它当然就是一言难尽的对人生细节的描绘,这种形象的、情感的、梦境般的展示实在难以以观念性的话语来转译。所以他常常对非文学专业的记者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写的究竟是what(而记者的专业性提问首先就是要抓到这个W)。所以标题也好,主旨也好,人物也好,作家建议读者用文学或诗的眼光来审读为妥。
然而正如本书的副文本(封面广告词、封底作者语录、附录一“1977:青春之约”的纪录片大纲)所示,这部小说是对77级的“我们”的回顾与惦念,是对那四年及其后的四十年的“我们”的生命记录。附录一提到的一些校园内外的历史事件和热点(比如“学潮”、读书热、文学热、马湘南的望月湖工程)也在小说本文得以详细描述,甚至一些具体的地名如“岳王亭”“望月湖”都是真实存在的,书中提到的通宵排队购书的那家校门口的新华书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还依然存在。可以说,就像作者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修改过程》是依据确有的历史事实和特定的人物原型加以创作的,仍然属于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再现”传统。至于实与虚,真和假的问题,作者在答记者问中已显出端倪:“生活与文学好像是两回事,把它们变成一回事,像物理学里的一个莫比乌斯纸带,两面变成一面,效果会怎样?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舞台小世界,人生大舞台,差不多也是讲这个大道理。”①
如此看来,对《修改过程》的解码,关键是这个“莫比乌斯纸带”是如何做成的?换句话说,历史如何经过虚构而成为小说(包括小说中的小说)?而本书的虚构形式——结构、叙事话语和自我拆解等又有何成败得失?
一、历史、虚构与想象
莫比乌斯带是由二面的纸条经过扭曲与缝合而变成一个平面,而对一个文学文本而言,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传统上所认为的现实与虚构(比如所谓“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统一。著名的德国美学家伊瑟尔,在其晚近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中,提出现实、虚构与想象“三元合一”的理论。在阐明《修改过程》的历史真实与虚构特点之前,让我们先简要说明一下这一理论观点。
伊瑟尔认为,“把现实与虚构对立起来的那种‘不言而喻’的传统认识认为,虚构的最基本特征就是现实的必然缺席,这样一种十分可疑的‘必然’,把一个现代认识论困惑不已的中心问题掩盖了起来,这个问题就是:尽管某些事物实际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们却不能分享客观事物的真实性”②。从对这样一种虚构/现实“二元对立”的反思出发,伊瑟尔认为,客观现实不是自明的真实(在西方语言中,reality既指“现实”,也指“真实”),真实依赖于主体的创建,借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正是“此在”的在场才揭示世界的意义。而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只有通过“历史的文本化”才能被把握。而在包含大量现实再现的词语的文本中,“文本并不是为了追求现实性而表现现实的。这就是说,文本没有必要依照事实本身使自己成为虚构之物。实际上,在文本产生过程中,作者的意图、态度和经验等等,它们未必就一定是现实的反映。这些意图、态度和经验等,在文本中更有可能只是虚构化行为的产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虚构化行为转化成了一种符号化的真实,同时,想象也成了一种顺着符号指向驰骋神思的形式”。③
伊瑟尔的“三元合一”论并不仅仅是在传统理论中增加一个“想象”,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调解了现实与虚构和想象的关系,并且赋予虚构以新的解释。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虚构经常与不真实、谎言、欺骗等相联系而成为现实/真实的对立面,而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阐释中,虚构表示一种意向性行为,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意义的建构。正因如此,虚构和现实,虚构与想象的性质和关系也更清晰。对于文学和艺术文本而言,现实不再是客观真实之物,而是“对客体的描绘”,这一文本化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它们所摹写的原型”。“虚构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疆界的跨越。这实际上是一种‘侵犯’行为。这种行为是与想象紧密相连的。”而想象通常以一种弥散的、瞬息万变的形式把握对象,“它是自我意志的显现,以绝对的任性标明自我的本质”(胡塞尔),那虚构化行为就要引导和控制想象,“赋予想象一种明晰的格式塔”④。这样,虚构就充当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纽带,一方面,虚构所再造的现实指向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本身,另一方面,无边的想象或多或少分享了对象的现实性,并被虚构纳入到某种形式之中。
现在可以回到《修改过程》并尝试解答前文中提到的问题:“历史如何被虚构为小说”(而能获得合法性)?这个问题既宏观又微观,既有赖于对历史语境的参照,又需对自身意义系统的语法建构加以细读。先从宏观方面说。
《修改过程》既可视为历史小说,也可看作是现实主义的长篇叙事。英国批评家罗吉·福勒认为历史小说“为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条件,并最终与之合流”⑤。正是在两者相互融合的意义上,王德威曾如此给历史小说下定义:
历史小说一词通常指的是由真实或虚构的历史人物与情节相互组成起承转合的叙事。这样的小说之所以产生历史感,不只是靠作者对特定时代的人物、环境、风俗等做出信而有征的描写,而有赖读者对特定事件以及作品所描画的历史动态所产生的推想和反省。⑥
在谈历史小说涉及“历史”和“小说”的两造时,他还说过一段话,也值得引述:
历史与小说是两个特别息息相关的叙述话语,因为两者在探索人类经验上有相当的重叠,而所谓经验可以是想象的或实证的、虚构的或观念的,遑论两者相互跨越、挪用的现象。历史小说特殊的魅力正是因为它跨越了这两种叙述话语。⑦
王德威的这一解释,显然是在一种“后学”语境中,通过吸纳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海登·怀特诸辈新历史主义观念之后推导出来的。而这样一种普遍主义话语并不一定契合于具体的历史实际。比如明清时期的白话长篇小说,尽管也往往脱胎于历史,并参照历史正典的范式展开叙事,但这种“历史小说”始终得不到主流话语的承认,在历史叙事的宏大家族中顶多充当一个看门人的角色。只有在梁启超提出“新小说”以后,更确切地说是五四之后,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前驱借助西方现实主义范式构造新小说,才使得小说(fictional虚构的)话语具有历史合法性,才成为“一种严肃、生动、充满激情的伟大形式”(龚古尔兄弟语)。
韩少功的小说自然离不开五四先辈所开创的这个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种种文化和政治压力下已发生变异,如十七年时期提出的“正面人物论”“三突出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两结合论,“民族形式论”等等。这些观点指导下的创作,一方面使小说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小说变成了神话,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这就无怪乎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会一边倒,取法现代派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重建小说(虚构)范式。
韩少功也不满于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变异,并认为自己的早年小说“比较幼稚”,从而进行过多种取法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并做出新创的小说尝试,“词典体”“玄幻体”“缺略体”等等,不一而足。但纵观韩少功大部分小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所写的中长篇小说,如《报告政府》《山歌天上来》《赶马的老三》《日夜书》等,基调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是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茅盾、巴金、老舍和沈从文所奠定的俄国传统和中国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回归。——这一传统不仅包括从创作方法意义上的“严肃地处理日常现实,一方面使广大社会底层民众上升为表现生存问题的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时代历史进程这一运动着的历史背景之中”⑧,也包括世界观上具有伦理和政治意义的“人民”本位的道德关怀和权利诉求。
《修改过程》对历史的虚构,正是得益于现实主义经典所传承的遗产和经验。它一方面从个人的日常行为的描绘中,反映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又注意从变动的时代背景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拿捏人物的情感与思想变化。前者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小说对马湘南的生活和命运的描写。马湘南在就学时对专业毫无兴趣,一门心思想着赚钱,文学社的油印刊物被他拿到大街上热卖,向陆哥提供危情警报也要收取信息费(这种似乎夸张的细节突显的是被我们忽略的历史真实),而他体现其商业奇才的、赚取第一桶金的运作——“望月湖工程”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八九十年代“个体户”商业操作的特点——与政府、传媒的合作。这种操作模式在后来与郭副省长的亲密互动、互相帮衬中运用得更为成熟与有效。马湘南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资本家的一个典型形象。尽管他的日常言行常常是通过一种漫画化的夸张手法得以表现的——比如在歌厅里必唱《打靶归来》,公司管理是仿照解放军军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高兴就让司机给所遇之人一人一张百元大钞——但这种描述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当代商业大佬们的辉煌、霸气与虚弱。只是马湘南的突然下降缺乏左拉或茅盾似的社会学分析(比如他的权力太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而只能靠假借和象征来获得权力幻象),韩少功是从道德人性、从家庭悲剧的角度揭示其虚弱和没落,并让他以自杀谢幕,这多少有些偶然性,削弱了这一人物的悲剧意义。
第二种现实主义的常规手法,从变动的时代背景中反映人的性格和命运之变化。司汤达、巴尔扎克这些现实主义大师,早已从历史社会学视域来观察和研究人,从而刻画出于连、拉斯蒂涅、高老头这样的经典形象,而这样的创作范例也促生了恩格斯“现实主义意思,……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新的批评理论。比起以前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现实主义更具现代性的特点,一方面现代性个体更具个性,另一方面个体的自我塑造和筹划又越来越依存于变动的社会力量。在《修改过程》中,楼开富、毛小武和史纤等人的形象,特别是其大学毕业后遁入都市或乡村的生存际遇,让我们慨叹四十年社会变迁之剧,而造化之弄人也烈。
单以楼开富为例来说吧。楼开富学生时代是这个班的班长,热衷于“宣讲文件精神,把品德、理想、现代化、革命传统说得振振有词”,热衷于学雷锋做好事,甚至面对女同学的浪漫示爱,他也无动于衷,把她送的两张电影票,当做礼物送给系领导王副书记。他也操心个人的前途和地位,比如试图通过结交干部子弟,通过恋爱登上权力高塔。但他的“做报告、讲理论”的交际风格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女儿给吓跑了,马湘南为他安排的相亲节目以戏剧性的尴尬收场(这是全书中最有笑点、令人过目不忘的一幕)。
楼开富“左得可爱”的性格是在变动的大环境下造成的。第九章“最新敌情”详细描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比如政治学习小组活动开展不下去,“思想纷争不少”,“学生们纷纷缺课”,“‘八禁’早已取消”,“林欣好几天没回校,陆哥、马哥也是各怀鬼胎,忙得神出鬼没的”,“野生动物”们提出各种自由、民主的要求,让主管思想工作的王副书记忧心忡忡:“照他们这样闹下去,这校内校外还有没有上下?离天下大乱还能有多远?”对“最新敌情”的发现和侦破,其实正是这种“后革命”时代继续革命理念的余响,而楼开富所紧跟的王副书记,正是革命化的一种符号。
毕业后的楼开富终于如愿“嫁”入豪门,当了厅长的乘龙快婿,自己也成为党报的一名干部。但“天堂也有人间烟火”,领导也信迷信,有怪癖,不好服侍,书中对楼开富得罪大领导姚部长后的惶恐和焦虑的描写,让人想起契诃夫笔下忧惧而死的小公务员。
之后的情节有AB版两种展开。A版楼开富因为老婆查出患有不治之症而断送出国梦,工作也丢了,他沉入社会底层,以长跑磨练自己的生存意志,同时打几份工,照料病妻,抚养幼儿,终于赢得黄家的尊重。而且他的生活从此反而过得有滋有味,多次获得马拉松冠军,成了“体育新星”,遇见同学会送各种奖品和小礼品。在结局他晨跑撞上汽车时,头脑中浮现两句歌词“海阔天空我们在一同长大,普天下美好一家”——他回归了,回归到革命的乌托邦,回归到美好的青年时代。B版的楼哥出国又回国,开起移民中介公司。这一章围绕他与毛哥的冲突写成。毛小武是真正的底层,想要靠老同学帮忙出国镀金,楼哥看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就让他办“政治移民”,提供的模板和案例都是作假,有违毛小武做人的底线。毛小武在电话中大骂老班长以前“大道理比谁都讲得顺溜”,“到头来也当个人贩子,偷鸡摸狗打地洞,转往屁眼里扣粪渣,中国米国一起蒙”。而楼班长的回应是“You stupid Chinaman!”。这一版的楼开富是一个在域外资本主义环境中蜕化变质、继续迷失的楼哥,尽管作者最后暗示他还有“一颗中国心”。
不管是哪一种命运的展开,楼开富都是这一代人里变化最大的角色,从一个开口闭口大道理的“革命人”到一个追求地位、物质利益甚至不择手段的人,前后反差甚为剧烈。如果没有环境的交代,这样的转变是不可理喻的。而要理解时代环境如何影响到楼开富的后半生,不可忽视第11章楼开富随马湘南去特区“体验”的一段描写:
“……特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闪闪耀眼的太多可能性。那里群楼林立,车队潮涌,缤纷商厦大若迷宫,白天和夜晚都在沸腾,到处都翻涌出空调机排放的冷气或热浪,一片形如冰炭的繁荣。像‘时代’这样的词,只有在那里才会蠕动,才会伸缩和起伏,一个个活起来,啃咬内地人等等绵绵情思……这太不公平了吧?从那样的会所里出来,楼哥全身上下从里到外热烘烘软酥酥,鼻子边余香犹存,生命能量似乎在每一个毛孔里喷涌……”
很多腐败官员在其忏悔录中,都会谈到多少年前,去南方某个城市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正是觉得“不公平”,觉得这种“非人”(非一般人,非公务员)的生活才值得一过,才有了思想和行为的转变。而特区的风景并非奇观和幻影,它后来转化为历史时间,转化为当代人置身其中的戏剧舞台,楼开富和楼开富们的悲喜剧正是在这一似真似幻的舞台上上演。
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关于楼开富的叙事在形式上采用了后现代的拼贴法,但内里还是现实主义的。即在革命化、体制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变迁中,个体如何被社会力量所裹挟和不断命名。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不能不变得自私冷酷,楼开富也不可能寻觅到真实自我。毛小武对A版楼开富的结局不满意,是因为觉得小说不能这么瞎编,楼开富不可能返璞归真。所以他批评肖鹏的创作是“十八扯,跳大神”,迫使肖鹏根据他的陈述写出第二版。而对韩少功来说,历史的残酷和道德的温情让他难以取舍,从而做出并置之举;即使在B版中,他也不忍继续无情地讽刺楼开富,而让他洒泪离场。也许毕竟是老哥们,书内书外离得太近吧。
《修改过程》以人物为经线带出历史的纬线,全书20章,除了“抗议者”“最新敌情”“解放军叔叔”“重新开篇”“现实很骨感”五章,其他都可以看作人物行传,分别是陆一尘(1.3)、马湘南(4、5、6、16)、肖鹏(7)、楼开富(8、11、12)、毛小武(10)、史纤(13、14、20)、马波(17)。如同《日夜书》一样,它是借鉴古代史传的方式纪叙历史,表达人生经验。这样做的好处是适合于民族传统与读者习惯,易于激发读者的道德感情。而其弱点是缺乏时间性(历史感)和因果性。70年代末的陆一帆和马湘南的说话口吻和行为举止与21世纪的人物如出一辙,这是令人惊讶的;而缺乏事件的因果联系,也容易导致人的形象的孤立和人的命运缺乏必然性(作者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安排了插入章节、串场人物等手段来弥补)。比如马湘南的商业成功因与郭副省长的联系而得到社会学的证明,但是他的命运跌落和自杀结局就缺乏必然性的事件的解释;史纤的生病和黯然离校得到了事件的解释,并且其被骗、被查这一公共事件有力地串起了毛小武的生命轨迹。但结尾补叙的“花花太岁”和“飘魂”两章因为缺少事件的联系就成为了“狂想曲”,表征的似乎不是史纤坚实走过的人生而是叙事者想象的人生,一种情感的符号。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不必对事件的起迄和因果耿耿于怀,现代主义之后的小说也早已内转化和形式化。但我以为,对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小说而言,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传统依然弥足珍贵,他们对历史因果的苦苦探寻,对个体意志如何受社会力量驱遣的精密研究,造就了一种与理性、民主息息相关的艺术。韩少功的许多早期作品诚然是体现类似的历史理性精神的。但他后来把这种“议题化”的虚构难题主要交给了散文,而他的小说则少了一分历史理性而多了道德情感的表露与普遍性的哲学意味。
二、虚构叙事话语:叙述言语与元话语
叙事学意义的“话语”,一般指与“故事”(story)或“内容”(content)相对的叙事表达层面,涉及事件组织的秩序(order)、控制表述的“视点”、以及叙事速度、叙事声音、描述和评论等等。比如就“秩序”或“结构”而言,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马湘南的故事在4、5、6章连续叙述后突然中断,然后在第16章写出他的结局。比如“视点”,我们可以讨论“花花太岁”中视点的转换(“呵呵呵你疯狂的花羞涩的花淫荡的花”,叙述者为何转向人物的内视点?)。但囿于篇幅,这里只能在“三分法”(米克巴尔:“素材、故事、话语”)意义上讨论其“叙述话语”中的两项:叙述言语和元话语。
“叙事言语”类似于巴赫金所用的“叙事语言”“小说话语”,它包括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巴赫金有时称“作者语言”)。而叙事语言又包括语式上划分的“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等,从表达上讲的“描写”“陈述”“评论”等。这都是学院派的形式研究,未若巴赫金的“小说话语”来得明确和及物。
巴赫金认为小说的话语是多元的“杂语”的集合,包括方言、文学语言、历史语言、社会及职业性行话、谚语等等,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世界观,“小说家不清除词语中他人的意向和语气,不窒息潜存于其中的社会杂语的萌芽,不消除显露于语言的词语和形式背后的语言面貌和讲话姿态。相反,作家让所有这些词语和形式,都同自己作品的文意核心,同自己本人的意向中心,保持或远或近的一段距离”。⑨由于长篇小说往往包含更多的人物、更多的对话关系、更复杂的情感和思想的冲突,所以,“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进入长篇小说,在其中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体系。这正是长篇小说体裁独有的特点”。⑩
以此检视《修改过程》的语言,我们能体会韩少功一贯的风格和魅力,也能发现其新的创获。比如韩少功的人物语言,往往因为作者对人物及其社会阶层、职业比较熟悉,而能做到“如闻其声口”,非常生动而有表现力。
比如写马湘南与郭副省长的对话:
马湘南大惊:“你好歹是一方大员,堂堂巡抚,怎么搞得像个地下工作者?警察都到哪里去了?”
“你以为是你们当年娃娃造反,打一打口水仗了事?”对方笑了,“工人最怕失业,农民最怕失地。你断人家活路,兔子也要咬人。”
马湘南一方面称郭副省长“堂堂巡抚”,另一方面又冲着令人景仰的高官用长沙方言讲粗痞话,生动再现了他与领导的亲密关系、直爽的性格和说话的艺术。而郭副省长的话既是行话又是真话,很得体地揭示了其身份和性格。
再看毛小武的说话:
(在马家受气后在公交车上发无名火):“嘿,阎王殿放假了?什么破汽车,装猪也不能这么装啊。”他一张狗脸说变就变,还与气象台不共戴天。“前天说降温,昨天说降温,降你贼骨子的尸。抽胡说不上税么?臭王八蛋,臭不要脸,臭狐狸精……”
一连串的方言和粗痞话,把一个底层市民的愤怒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本书中,毛小武和史纤的语言最让人亲近。因为他们讲的是“自然语言”,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语言。韩少功对人民大众的语言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深厚的感情,他写农民、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时候也最得心应手。这与很多同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形成鲜明的区别。
在叙事语言上,韩少功也非常注意叙述者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自然衔接、转换,注意声音的层次和高低变化,从而形成多声对话和多种风貌。比如写毛哥母子去马府表示感谢,马太太嫌他们脏,没让他们坐沙发,让保姆搬来两张木椅:
毛妈迟疑地落下一小半屁股。毛哥却依然站立,紧扣椅背,气息越来越粗重,肯定是血流呼呼往头上涌。小条子(此语难懂——原文注),马哥怎么找了这么个骚货?连礼数都不懂,连长幼都分不清。是不是事后还要差人洗椅子、刮椅面、喷药水、干脆把脏椅子扔出大门?是不是自己还要一连呕上三天?
他想说什么;不,想喊什么;不,想吼什么——但终于半个字都没有,只是低头盯住脚尖。
毛哥和马哥是老同学老哥们,受到马太太轻慢后感受奇耻大辱,叙述者在外焦叙述后迅速转入毛哥的心理活动,因为非此不足以表现人物的耻辱和愤怒,“想说什么、想喊什么、想吼什么”,以外观混合着人物的情绪,破折号一转,又回到中距离的外在叙事声音:“终于半个字没有,只是低头盯住脚尖”,表明人物已经意识到地位的落差,或者说让读者理解这种落差所带来的驯服。
书中“炸裂”的语言比比皆是,包括叙事人拟作的古典诗词、快板词等等,这里不做详述。可以肯定的是,韩少功在长篇中延续了他写短篇小说时的上佳的语言感觉,他还能写。
最后不得不简单说一下《修改过程》中的元话语问题。这是一个青年批评家比较感兴趣的议题,而且据说他们对此颇多肯定和溢美。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未具体统计,据说书中元话语的出现有十多次。这些元话语的表现和功能各不一样。有的表现写作者肖鹏对故事的处理,对写作或文学自身的议论,对人物的揣度;有的表现外叙述者对肖鹏写作过程的说明,外叙述者通过肖鹏来表达对文学的议论(比如肖鹏与惠子的对话);还有的则是混合着内外两个叙述者的声音(比如全书最后一句:“好了,接下来的故事……”)。
其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元话语,我以为除了传媒(阅读环境)的变化,作者—文本—读者交流系统的关系和功能的变化等因素,最主要的是作者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了写作难度——让肖鹏写小说并引起麻烦。因为是肖鹏写的小说,面对的是假想的特定的网民(包括小说中的人物),遭遇的是特定的发表机制和修改机制,所以就有怎么写啊删帖啊超链接啊小说与现实关系为何啊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叙述者(姑且说是韩少功)不可能让肖鹏全权取代自己的故事和声音,叙述者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读者,这批读者只需要直接进入77级的故事,包括肖鹏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马湘南、楼开富和史纤的故事是肖鹏还是韩少功写的并不重要,楼开富的AB版是韩少功还是肖鹏提供的也不重要(前者提供的不更好吗——事实上,真实读者怎么可能会认为自己读到的是肖鹏的小说?),相反,正因为肖鹏这一作者形象的出现,引出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干扰了文本统一的美学风格和阅读效果。
比如说,“解放军叔叔”一章,写毛小武犯罪被捕,同学们为之送行,群情激昂(读者的情感代入也至高点),这时候叙述者突然想到在场人物肖鹏是要写小说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多少年后,肖鹏写到这里,觉得当时还有点什么,或还应该有点什么。比方,他就不能写一写泪花,写一写扭曲的脸,写一写森林般伸出的手?”——这完全是游戏笔墨,不必要、也不自然的自我反射。
同样的道理,篇幅最大的元话语——“现实很骨感”一整章,肖鹏与惠子谈文学,也是不成功的实验。尽管惠子阐明的文学观念对普通读者不无启发,但显然会破坏审美幻觉啊,——有谁在看电影的时候愿意停下来听电影美学的讲座吗?
尽管如此,韩少功的长篇历史小说仍然是勇敢面对历史和自我的良心之作,其刻画的马湘南、毛小武和史纤等人物形象将深入人心,而其为适应新形势新读者所做的形式实验也必将收获成功,产生耀眼的美的光芒……
注释:
①舒晋瑜、韩少功:《完成一个对自己的许诺》,《长江文学评论》2019年第2 期。
②③④[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陈定家、汪正龙等译:《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第2页、第3页。
⑤[英]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⑥⑦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第33页。
⑧[德]奥尔巴赫著,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等译:《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1页。奥尔巴赫认为这一方法是“当代现实主义的基础”。
⑨⑩[前苏联]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第81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编辑: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