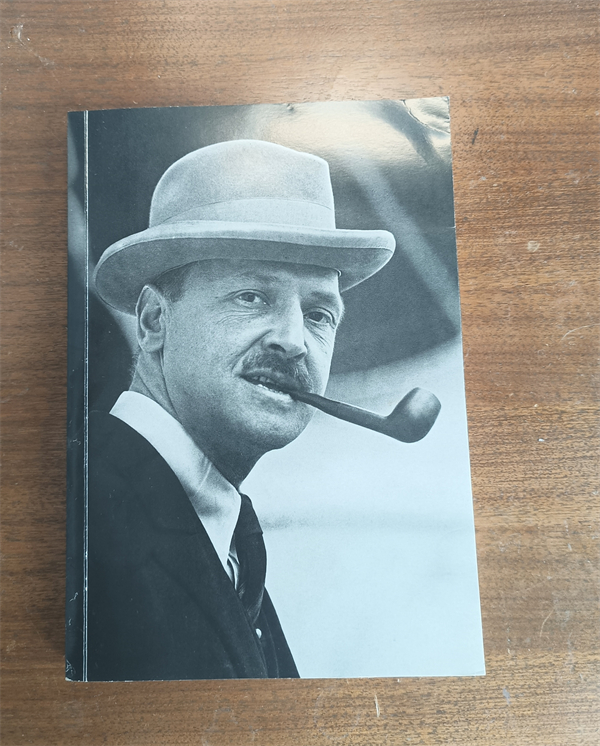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本身是包含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重人格的分离拉扯则是人性立体性的表现,而毛姆在其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刻画的主角正是三重人格失调下的产物,饱含精神层面的撕扯与混沌以及疯狂中酝酿的高贵。作品描绘了本性与物质现实不可剥离的矛盾,包含着深厚的生命视角,一针见血地解剖了世俗皮囊装饰下的人性,夹带着旁观者的戏谑和无情的目光,为人性的剖析提供了艺术化的视点。
(一)无法逃离的现实———社会框架下的“自我”。
自我是社会道德的衍生品,遵循着“现实原则”。自我是有逻辑、理性的,具有组织、批判和综合能力。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似乎集许多自相矛盾的性格于一身,诸如勇敢与胆怯,冲动与理智,这些奇妙的组合造就其性格的多面性。当他担任着证券经纪人,供养着一个沉迷结交小资文人的妻子,尽管平庸如常,却是正派地走在社会道德的钢丝上,无人叫好,也无人责难,如同许多人一样毫不起眼。这时的思特里克兰德完全遵循着自我的控制,臣服于现实原则,抑制着自己从孩提时就孕育着的本能和创作的欲望。自我是调节本我和自我并与现实打交道的理性思维,自我的能量大多被用来抑制和摒弃本能冲动。在世俗框架和家庭生态中,道德教化而得的理性思维迫使思特里德克屈从于普适的道路,将梦想束之高阁,压抑自己的欲望。他遵从着现实原则的自我安分守己,但这份自我的理智在家庭和欲望的撕咬中渐渐破碎,满溢的本我亟待爆发。

(二)追寻理想———执着出走后的“本我”。
人的躯体是一种现实的实在,人在外部世界中的行动以及人类的心理活动都离不开躯体而单独存在,所以部分本我向社会现实妥协,由此形成了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而当思特里克兰德放弃了证券经纪人身份只身来到巴黎时,在自然人格的层面上,思特里德克可以不受社会现实的困扰,他人格结构中本我的作用极大地显现出来。这时被本我控制的思特里克兰德脱离了桎梏,欲望急需得到释放与满足。物质对他而言根本不值一提,整个人完全受绘画的欲望控制。这样的仿佛是天性本能驱使的创作被荣格称为“自主情结”,荣格认为拥有这种情节的艺术家的创作欲望非常热烈,甚至会消噬其人性,使其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即便危害了自己的身体机能,破坏了普通人该有的幸福也无所畏惧。本我是混沌的,它不了解价值判断,更不在意道德,是一种放纵的激情。思特里克兰德被本我支配,他的所有作为都是随心所欲,丝毫不关心外界。无论是对身体病痛的漠视还是对待施特略夫一家“农夫与蛇”的行径都是思特里德克完全臣服于本我欲望的表现。这份汹涌的欲望不仅对于个人生理造成影响,更使得他人的家庭破碎不堪。此时,本我的力量支配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切行为,毫不在意道德原则,遵从欲望。流浪至马赛时,他依然毫无改变,本我还是在其人格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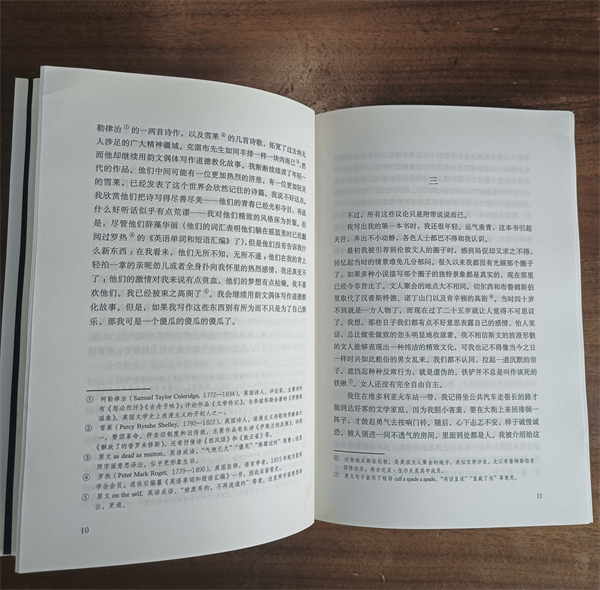
(三)心中的月亮———塔希提岛上的“超我”。
弗洛伊德曾说:“通过理想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随着自我理想的深度勾勒,思特里德克迸发了进一步脱离社会现实的渴求。他希望能有一片遗失的小岛,在那里创作出他心中追逐的那轮明月。终于,他找到了心中艺术创作的伊甸园———塔希提。在这里,思特里克兰德最初纯粹的绘画欲求转变成了超我中所蕴含的具有崇高意义的理想,最终成就了真正伟大的画家。他为了追求理想经受了许多艰辛,此时他的超我是出众的。但即便处在超我的人格下,他仍旧是是一个自大无礼的恶徒。这种与传统超我理论不协调的现象与毛姆对人性人生的观念密切相连。他认为人性复杂多样、十分矛盾,绝对的正邪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都值得追问。所以他并未将主角塑造成一个在逆境中充满力量的英雄,而仅仅是个追求崇高理想的恶棍。同时,毛姆热爱并推崇自由,认为世俗会束缚人的进步,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跳脱现实枷锁。因此,这种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背离的超我阐释与毛姆的自由观及人生观密不可分。
弗洛伊德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理应统一协调。倘如自我无法在本我、超我以及外部世界中找到理想和谐的状态,个人就将难容于社会伦理和广义道德。思特里克兰德的自我与本我正符合这种不协调的情形。他经历了欲望抑制的自我、欲望放纵的本我、最后达到超我,他对世俗框架的超越使他最终采摘到了心中那一轮月亮。毛姆对人性和理想的摹写让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放大升华,主人公的追寻逃离让人性本能的欲求迸发出巨大的艺术魅力,成为了探求人格精神的永恒佳作。
来源:红网论坛
作者:中南大学 唐雨霏
编辑:刘力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