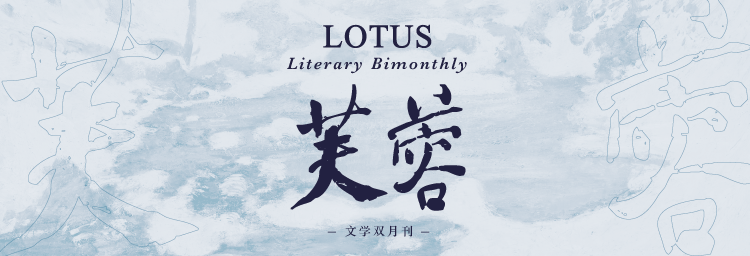

海上生月/摄
一溜儿堂(中篇小说)
文/王松
天津老城的东门外有一条街。街不长,东西向,西头顶着东马路,东头顶着海河。再早老城里没有甜水井,更没自来水,人们喝水只能去河边拉。后来洋人建了自来水厂,水管子通进老城里。但这自来水有一股怪味儿,城里人不懂这是漂白粉,都叫“洋胰子水”。有人说,喝了这种“洋胰子水”生不出孩子,也就都不敢喝,还认头去东门外的海河边拉水。拉水,也就得走这条街。这条街是条土街,每天拉水车的、挑水桶的过来过去,洒了水净是泥,日子一长也就总出事,不是人摔了跤就是车撞了人。后来有人捐钱,骑着街盖了一座观音阁。这条街是拉水的街,人们就把这观音阁叫“水阁”。再后来,这条街也就叫水阁大街。
刘一溜儿的棺材铺再早不在水阁大街,是在东门里广东会馆的后身儿。但东门里住的都是有势力的大户人家,出来进去总看见这棺材铺,不光碍眼,也丧气,就三天两头成心找别扭。刘一溜儿也明白,门口儿的人找别扭,无非是想把自己挤对走。其实在东门里,棺材生意本来也不好做。街上的人都活得好好儿的,谁家也不会三天两头儿总死人,经常十天半月也卖不出一口棺材。这么一想,刘一溜儿也就一咬牙,惹不起躲得起,干脆把这铺子搬城外去。后来选中东门外的水阁大街,倒不是冲着这座骑街的水阁,而是冲水阁旁边的一家医院。这医院看着不大,可人挺多。医院里自然都是病人,病人得病,就有治得好的也有治不好的,治好的自不用说,倘没治好,也就得说后一步的事了。这后一步的事,刘一溜儿的棺材铺也就正好接着。但刘一溜儿真把棺材铺搬到这条街上,过了些日子,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敢情这医院也是有来头儿的。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在天津办了一个“北洋军医学堂”,这家医院也就是那时一块儿办起来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不知当初怎么想的,这办的是一家女医院,专治女人的病。女人的病是麻烦多,但死的少。刘一溜儿本来想的是,医院死了人,苦主儿为图省事,也就会来自己这里买棺材。可这时眼瞅着还是没生意。刘一溜儿每天站在自己棺材铺的门口,朝斜对门这家医院看着,出来进去的女人虽也带着病容,可一个个儿还都挺精神,看样子别说一时半会儿,恐怕三五年也用不上自己的棺材。这时才想起街上的一句俗话,卖棺材的盼死人。这话听着有点儿缺德,可再想,也真是这么回事,倘若满大街上都是活蹦乱跳的人,自己这卖棺材的就得饿死。所以,粑粑三儿这天上午来棺材铺时,刚一进门,刘一溜儿就猜到他的来意,也看出他有要张口的意思,就立刻决定,赶紧把他的话堵回去。眼下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过去的三个伙计已经打发走两个,可是话说回来,跟粑粑三儿他爹毕竟有这些年的交情,只要他的话一说出口,再想驳就不好驳了,于是赶紧叹了口气,又摇摇头,咂着嘴说,你爸活着时,经常说一句话,阴阳饭最难吃,当初我俩也是走岔了道儿,现在他自己头前走了,把我扔下,再想改行也来不及了。
说着,两个嘴角就耷拉下来。
粑粑三儿虽然只有十几岁,看着傻,其实心里也明白事,听刘一溜儿这一说,就知道他是成心拿话堵自己的嘴。但这次来,还真不是想来刘一溜儿的棺材铺。
粑粑三儿的爹是个木匠,但不是做好活儿的木匠,用行里的话说, 是专摔寿材的“脏活儿木匠”。这个“脏”倒不是平常说的脏,只是不吉利。粑粑三儿从小就看着他爹摔寿材。他爹手巧,只要主家能说出样子,多跷蹊的寿材都能摔出来。但他爹也觉着这一行实在是“脏”,一直不想让儿子再入这个门儿。直到粑粑三儿十几岁了,眼看着干别的也不会有吗出路,这才一咬牙狠下心,让他跟着自己学了这门手艺。
可入行刚学一年,就出了这档子事。
粑粑三儿他爹一直在刘一溜儿的棺材铺干活儿,但不是伙计,也不拿月钱,是铺子里的木匠师傅,摔一口寿材拿一口寿材的钱。十几天前,刘一溜儿说接了一档子活儿,还是个急茬儿,南门外有一户人家儿,要迁坟,想趁这机会给两个老人合葬,一块儿摔两口寿材。又说,木料他家是现成的,已经送到铺子里来,给两天限,必须摔出来,第三天等着用。粑粑三儿他爹一听,三天两宿摔两口寿材,倒也不算太紧。可来到铺子的后面一看,木料虽还算整齐,却都是旧料,心里就有点儿不痛快。倘是旧料,刘一溜儿就该事先说明白,本来干的是这路活儿,也就不爱用旧料,用也行,但钱上得另说。不过粑粑三儿他爹是厚道人,也就没太争竞。赶着三天两宿把两口寿材摔出来了,这才发现,自己的左手腕子不知什么时候碰破了一块。本来木匠干活儿,整天离不开锛凿斧锯,碰破手是常有的事,粑粑三儿他爹也就没当回事。可当天晚上这腕子就肿起来。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再看,整条胳膊都肿了。粑粑三儿他爹心大,还没当回事。有手艺的人都好喝酒,中午又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喝了一回酒。想着再睡一宿觉也就没事了。可晚上回来时,整个人都肿起来。到后半夜,已经浑身发烫,人也不明白了。粑粑三儿一看,赶紧去棺材铺把刘一溜儿叫起来。刘一溜儿跟着过来看了,说不要紧,就是心里有点毒火,手腕子一破,这点毒火就拱出来了,先让他睡,睡一宿也就好了。但粑粑三儿他爹这一睡,就再也没醒过来。第二天早晨,粑粑三儿见他爹一直没动静,过来推了推,没动,再摸身上,也不热了,不光不热是已经凉了。这才知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气了。刘一溜儿得着信儿赶紧又过来,一听粑粑三儿说,他爹头一天中午还出去喝了半斤多酒,立刻跺着脚说,哎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早不说,他这一肚子毒火儿,再喝酒,还不是火上浇油啊。粑粑三儿曾听他爹说过,刘一溜儿当年做过汗门生意。汗门是街上的话,也就是卖药的。这时一听刘一溜儿说,也就信了,看来爹走,最后还是走在了酒上。
粑粑三儿这次来棺材铺,只是想让刘一溜儿给出个主意。
这几天已把爹的后事都办完了。粑粑三儿的爹摔了一辈子寿材,最后自己走,却连口寿材也没用上。本来刘一溜儿挺大方,跟粑粑三儿说,和他爹毕竟有这些年的交情了,知道粑粑三儿的手上也没几个钱,干脆就送他爹一口寿材,也算是这辈子最后的一点儿情分。粑粑三儿听了,心里还挺感激。可寿材送来了,粑粑三儿一看,不是寿材,只是个匣子。匣子跟寿材就是两回事了。寿材也叫寿枋,料最少也要半尺厚,且两帮起鼓,前后出梢,看着就像一条船,也像一间房。而匣子只是用几块薄板钉的,也叫“三块半”,不光看着寒碜,也不结实,埋在土里没一年也就烂了。街上的俗话说,倘有个“三长两短”,指的也就是这种匣子。但这时粑粑三儿已说不出别的,只好就用这匣子凑合着把他爹发送了。这时来棺材铺,先给刘一溜儿磕头谢了孝,然后才把来意说出来。本来是跟着他爹学木匠,现在他爹突然走了,手艺学了个半羼子,就不知后面该怎么办了。刘一溜儿一听粑粑三儿是为这事来的,心里才松了口气,想了想反问,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
粑粑三儿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想再干这行了。
刘一溜儿一听,顿时更轻松了,粑粑三儿当然是离自己这行越远越好。于是连连点头说,是啊,难怪你爹当初总说,阴阳饭不好吃,现在你看,就这么一甩手,说走就走了。
粑粑三儿说,我想进汗门。
刘一溜儿一听噗地乐了,说,汗门这饭碗,可是更难端啊。说完发觉自己走了嘴,赶紧又往回拉着说,不过也看怎么说,总还是个正经营生,比吃阴阳饭强多了。
粑粑三儿看一眼刘一溜儿,说,我想去济生堂。
刘一溜儿斜起脑袋眨巴眨巴眼,没立刻说话。
粑粑三儿又说,去找,施杏雨。
刘一溜儿嗯了一声,点头说,好,好啊。
粑粑三儿已看出来了,刘一溜儿点头并不是真点头,说好,也不是从心底说出的真好。粑粑三儿毕竟已经十几岁,就算听不出好赖话儿,对方的脸色还是能看出来。这时也就明白了,街上有句话,人走茶凉,现在爹已经走了,刘一溜儿跟自己,也就这么回事了。这一想,也就知道,再跟刘一溜儿说下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就告辞出来了。走到铺子门口,刘一溜儿又在后面追了一句,你爹没了,我还在,有事儿只管过来。
粑粑三儿站住,回头看一眼刘一溜儿,哦了一声。
粑粑三儿并没告诉刘一溜儿,他爹临走的那个晚上,曾对他说了一句话。那天晚上爹已肿得像用气儿吹起来,肉皮都撑得透明发亮。大概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就费劲地对粑粑三儿说,让他去济生堂,找施杏雨。当时已是半夜,粑粑三儿说,这会儿济生堂早上板儿了,等天亮吧,天亮再去。爹这时已说不出话来,只是拿眼看着他。他从爹的眼神里看出来,好像自己领会错了,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可不是这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直到把爹发送走了,粑粑三儿才明白,爹的意思是指以后,等他走了,让自己去找施杏雨。
施杏雨是济生堂药铺的坐堂大夫,再早并不出名。后来出名,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当时这事,粑粑三儿的爹就在跟前,后来也是爹对他说的。那天粑粑三儿他爹去北门里的乔四爷家里摔寿材。这乔四爷过去在南运河上养船,后来在北门里的街上也有买卖,地面儿上有一号,就是官面儿的人也得给点面子。这回是老娘死了,要办丧事。刘一溜儿对粑粑三儿他爹说,这乔四别看在街面儿上混,可最孝顺,早就给他老娘备了寿材的料,听说都是用船从广西拉来的上等好料,所以这回,让棺材铺的木匠上门去摔寿材。粑粑三儿他爹一听,就带上手使的家什去了北门里。乔家的这场白事果然办得挺大,来吊丧的,往外送客的,进进出出都是人。乔四爷不光孝顺,心也细,先跟粑粑三儿他爹详细交代了,按他老娘当初的心思,这口寿材要什么式样,都说清楚了还不放心,干脆让人搬来一把太师椅,就坐在旁边看着。粑粑三儿他爹一看就不太痛快。手艺人都有脾气,以往上门干活儿的事也有,可还没见过主家这么瞪眼盯着的,知道的是他心细、孝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对做活儿的不放心。心想,你这木料确实是上等好料,可再怎么好,还怕我偷吃一块不成?但转念再想,这乔四爷看着面色发暗,像挂了一层灰,想必是老娘殁了,心里难受,再加上连日操劳过度。这一想,也就不再计较。果然,一会儿底下的家人过来说,请的大夫到了。乔四爷说,让他到这儿来。底下的人应一声就走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大夫说,外面乱,看病得诊脉,最好还是找个清静地方。乔四爷听了倒没急,说话的声音也不大,又对底下的人说了一句,就在这儿。
底下的人不敢再多嘴,赶紧又走了。
一会儿,大夫来了。这来的就是施杏雨。施杏雨从一个粗布包里拿出脉枕,朝四周看看,问乔四爷,脉枕放哪儿。乔四爷用手拍了下太师椅的扶手说,放这儿。施杏雨又问,我坐哪儿?乔四爷抬头看他一眼,你站着,够不着我的手腕子?
施杏雨笑了,说,够是够得着。
当时粑粑三儿他爹在旁边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心想这乔四爷也太过分了,你对做粗活儿的木匠再怎么着,也就算了,可不该对大夫也这样。这时就见施杏雨站在太师椅的旁边,为乔四爷诊了脉,然后说,没大碍。乔四爷说,知道没大碍,可我这心口疼得厉害。施杏雨没再说话,朝粑粑三儿他爹这边看了看,就走过来,从粗布包里拿出一张草纸,在地上抓了一把锯末包起来,转身递给旁边的家人说,用它煮水,连喝三天。家人一下愣住了,看着施杏雨手里的这个纸包,不敢接。乔四爷也有点意外,歪过脑袋朝这边看了看,没想到这个施杏雨竟然如此大胆。显然,施杏雨是对乔四爷让他站着诊脉,心里不满,所以才这么干。
乔四爷毕竟是街上混的,瞥一眼这纸包说,你拿我开玩笑?
施杏雨说,医家治病是人命关天,不开玩笑。
乔四爷说,不开玩笑,让我吃锯末?
施杏雨点头,三分药,七分缘,管不管用,就只能看缘分了。
乔四爷笑了笑,好吧,我就信你,
施杏雨说,连喝三天,早晚各一次。
乔四爷又嗯一声,我不信缘,三天不管用,去济生堂找你说话。
粑粑三儿他爹说,当时乔家正办丧事,院里都是人,这事过后,一下就在街上传开了。这乔四爷是在街面儿上混的人,当然矫情,过后还真把这包锯末煮水喝了。他这时喝这锯末已不为治病,就想有个由头儿,三天以后,好去济生堂找施杏雨说话,在地上抓把锯末就敢给他吃,他还没见过这么大胆的人。可连着喝了三天,他把老娘的大殡出了,人也埋了,这才发现,自己心口疼的毛病竟然真的好了。本来街上的人还都等着看热闹,知道乔四爷不是省油的灯,济生堂的坐堂大夫施杏雨这回算是捅了马蜂窝,乔四爷非把济生堂一把火儿点了不可。可这时一听说,乔四爷喝了这锯末煮的水,心口疼的毛病竟然真的好了,一下又在街上轰动了。这回不光施杏雨出了名,连济生堂药铺的买卖也跟着火起来。
粑粑三儿听了这事,也觉着挺神,要不是他爹亲眼所见,简直没法儿相信。但他爹又说,后来棺材铺的刘一溜儿也跟他说起这事儿。听刘一溜儿一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刘一溜儿先问粑粑三儿他爹,那天在乔家摔寿材,用的是哪种木料。粑粑三儿他爹一听就连声说,料可真是难得的上等好料,摔了这些年寿材,还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刘一溜儿眨着眼问,到底是哪种料。粑粑三儿他爹说,是正经的广西沉香木,拉一锯,满院的沉香味儿熏得人眼晕。刘一溜儿一听就乐了,说,这事儿的毛病就在这儿。
粑粑三儿他爹不懂,问毛病在哪儿。
刘一溜儿说,这沉香不光是木料,还是一味药材。
粑粑三儿他爹当然知道沉香是药材,可沉香跟沉香木不是一回事。
刘一溜儿摇头说,当然是一回事,沉香木也就是沉香。接着又说,这沉香入药,从古时就有,专治谷气郁积,胃脘不畅,施杏雨那天也是走时运,正赶上你用沉香木摔寿材,他这才捡了个大便宜。粑粑三儿他爹听了想想,又摇头说,还是不对,这乔四爷那天不是胃疼,是心口疼啊!刘一溜儿又摇摇头,一般人不懂医,胃疼和心口疼当然很难分清楚。
粑粑三儿的爹对粑粑三儿说,起初刘一溜儿的这些话,他还将信将疑,以往刘一溜儿也说起过这个施杏雨,话里话外总带着不屑,就想,这也难怪,当大夫的都是想尽办法让人活,就是得了要死的病也千方百计给拉回来,而开棺材铺的当然盼人死,两边儿就算不是冤家,也是对头,刘一溜儿说起这施杏雨,当然不会有好话。但后来有一回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喝酒,才听说,刘一溜儿当年也是汗门出身,跟施杏雨不光同行,还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只是后来两人闹翻了。当时刘一溜儿在街上发狠说,是施杏雨砸了他的饭碗,既然这样,他干脆就往这锅里撒泡尿,索性这锅饭谁都甭吃了。就这样,他一咬牙离开汗门,开了这个棺材铺。施杏雨后来虽也离开汗门,却当了大夫,再后来就让济生堂药铺请去坐堂。
粑粑三儿这次来棺材铺找刘一溜儿,直到出来,才明白这趟不该来。本来想的是,施杏雨在济生堂药铺坐堂,毕竟是街上有名有姓的名医,自己就这么直脖瞪眼地去找人家拜师,说不定就得碰钉子,而刘一溜儿跟施杏雨的关系甭管怎么着,当初毕竟是师兄弟,臭嘴不臭心,况且自己的爹跟刘一溜儿又有这些年的交情,现在爹殁了,如果让刘一溜儿给施杏雨递个话儿,施杏雨怎么说也得念一点儿过去的情分。可这回来了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刘一溜儿嘴上虽说,好啊,好,但看得出来,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粑粑三儿这时才明白,刘一溜儿跟施杏雨的疙瘩不可能解开,而且随着施杏雨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疙瘩只会越系越紧。
粑粑三儿这么一想,也就明白了,当初爹在世时经常说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看来去找施杏雨,只能就这么撞着去了。至于施杏雨怎么说,也就只能听天由命。这时,粑粑三儿又想起一句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
这一想,自己反倒噗地乐了。
刘一溜儿本名叫刘福有,叫一溜儿,是因为棺材铺的字号叫“一溜儿堂”。棺材铺的字号本来没有叫“堂”的,听着不像棺材铺,倒像是药铺。但刘一溜儿在街上说,这棺材要说起来也是药,人得了病,如果别的药都不管用了,棺材也就是最后的一味药,这药吃了肯定管用,一副下去,保管一了百了。但也有人说,叫“一溜儿堂”不光不伦不类,也不吉利。刘一溜儿一听就乐了,说,当然吉利,叫“一溜儿”,是为了让人走得痛快,一溜儿就奔西去了,至于奔了西边儿是上天,还是入地,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在这个上午,刘一溜儿把粑粑三儿打发走,又寻思了寻思,就有点儿后悔了,心想不该就这么让他走了,粑粑三儿倒不是痴傻呆苶,可脑子不会拐弯儿,肯定听不出自己说话的弦外之音,倘若他信以为真,认为自己真赞成他去济生堂找施杏雨,这事儿就不太好了,虽说这粑粑三儿的脑子缺根弦儿,可一般的事还能分得出好坏,懂得倒正,他爹毕竟在棺材铺干了这些年,铺子里的这点事儿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他,如果回去都跟粑粑三儿说了,粑粑三儿去了济生堂,再把这些事告诉施杏雨,传到街上去,后边说不定就又要有麻烦了。
这一想,心里就打了个愣。
让刘一溜儿没想到的是,傍黑时,粑粑三儿又来了,这回还跟着崔大梨。刘一溜儿跟崔大梨也熟,知道他是粑粑三儿的表哥。崔大梨他爹跟粑粑三儿他爹是姨表兄弟,叫崔大杠子,是西门外杠房铺抬杠的。杠房叫杠房,其实不光抬棺材,也有出殡的响器班儿和一应执事。崔大杠子专管抬灵柩,还是头杠,在杠房铺里说话也就占地方,平时城里城外的街上谁家有办丧事的,就多一句嘴,问寿材置办了没有,倘没置办,就往粑粑三儿他爹这边引。粑粑三儿他爹揽来生意,刘一溜儿当然也不让白揽,多少给一点抽头儿。这个傍晚,粑粑三儿和崔大梨来棺材铺,是又带来一宗生意,北门里“庆祥布匹庄”唐掌柜的老姑奶奶殁了,要办一口寿材。崔大杠子连着两天都有事,脱不开身,就让儿子崔大梨带着唐家办寿材的定钱来棺材铺找刘一溜儿。刘一溜儿接了定钱,先问这寿材送哪儿,又问清主家要求几时送到,然后说了一句,还是老规矩。崔大梨一听就明白了,刘一溜儿说的是抽头儿。刘一溜儿又把粑粑三儿叫住,说还有点事要跟他说。崔大梨一见就头前走了。
粑粑三儿看看刘一溜儿,不知又要说什么事。
刘一溜儿见崔大梨出门走了,才问粑粑三儿,是不是已经去过济生堂药铺了。
粑粑三儿说,还没去。
刘一溜儿一听,心里才松了口气,看一眼粑粑三儿,嗯嗯了两声说,我跟你爹到底有这些年的交情,现在他走了,把你交给我,怎么说也得让你有个牢靠的饭辙,上午你问我,当时也是随口答音儿,没过脑子,你走了又想,要进汗门倒不是不行,也行,可如果去济生堂找施杏雨,就不如去找郭瞎子,虽说郭瞎子是气摸儿,但总是一门手艺,比汗门强。
粑粑三儿一听有些意外,眨巴着眼看看刘一溜儿,没说话。
刘一溜儿说的郭瞎子也是个大夫,但没有诊所,只是住家儿,就在这水阁大街东头,一间临街的门脸儿房,离刘一溜儿的棺材铺不远。不过这郭瞎子虽也是大夫,但跟施杏雨还不是一回事。施杏雨在济生堂药铺坐堂,是诊脉开方的大夫,郭瞎子只扎针灸,用街上的话说,叫“气摸儿”。这郭瞎子并不瞎,只是眼不吃劲,刚50多岁就已离不开老花镜,戴上老花镜看东西,还得凑到近前,看着不像看东西,倒像是用鼻子闻东西。粑粑三儿曾听爹说过,刘一溜儿最恨这郭瞎子。当初刘一溜儿刚搬来时,曾有一件事。这水阁大街东头把着河边有一户姓田的人家儿,老爷子再早是开布铺的,儿子在租界混洋事儿。当时这老爷子突然得了暴病,弄到水阁大街的医院去看。医院大夫说,这是女医院,不看男病,就算能看,这病人也已经没治了,回去想吃点儿啥就吃点儿啥吧。这田姓儿子一听,只好把老爷子弄回来,果然,当天晚上就没气了。这儿子是混洋事儿的,手里有点儿钱,老爷子殁了心里难受,为解心疼,就来刘一溜儿的棺材铺,说多花点儿钱没关系,想给老爷子办一口像样的寿材。刘一溜儿这时刚把铺子搬过来,还没站稳脚儿就来了这样一宗生意,心里自然高兴。先收了定钱,就赶紧把粑粑三儿他爹叫来,搬出平时不用的上好杉木,连夜给这田姓人家儿的老爷子摔寿材。可第二天早晨,寿材已经摔成了,这田姓儿子又来了,说寿材不用了。刘一溜儿一听,以为他又找了别的棺材铺。再一问才知道,这老爷子没死,夜里竟然又活过来了。人没死,这寿材自然也就用不上了。可这时寿材已摔出来,也已经上了上好的大漆,只是还没干透,有心不退这田姓儿子的定金,又知道人家是混洋事儿的,有势力,不敢得罪,也就只好忍气吞声地把钱退了。这时街上的人已都在议论,刘一溜儿一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敢情这事儿跟郭瞎子有关。当初刘一溜儿搬来以后,才听说旁边住着个叫郭瞎子的气摸儿大夫。开棺材铺的自然都躲着大夫,可这时已经搬来了,再想躲也躲不开了。据街上人说,头天晚上,这田姓人家的儿子一见老爷子咽气了,就赶紧给穿寿衣。可正穿着,突然听见老爷子放了一个屁,这屁不光响,还臭。天津的街上有句俏皮话儿,叫“死人放屁,有缓”。这儿子本来正一边给老爷子穿着衣裳一边哭哭啼啼,这时一听老爷子放了个响屁,知道可能有缓,也顾不上哭了,赶紧叫来家人,一块儿给老爷子窝巴。正这时,门口儿的郭瞎子听着信儿也过来了。郭瞎子已经行医大辈子,听说这田家的老爷子是得急病死的,而且死得这样快,就觉着不一定是死瓷实了。以往这种事也有过,人已经死了,也出了殡,可抬到坟地正要埋,却听见棺材里有动静,把棺材盖一掀开,人就在里边坐起来了。这个晚上,郭瞎子来到田家,先给这老爷子摸了一下脉,然后拿出随身带的银针,在他身上扎了几针。果然,行针不到一个时辰,只听这老爷子的嗓子眼儿里哏儿喽一声,先是睁开眼眨巴了眨巴,然后又长出一口气,就坐起来。这件事一下在街上传成奇闻。刘一溜儿听了先还不太相信,偷着去田家,想看个究竟。去了一看,果然,就见这田家的老爷子正坐在床沿儿上,抱着个大碗喝粥,身上还穿着黑亮的团花儿寿衣。刘一溜儿扭头就回来了。从这以后,虽然在街上还经常跟这郭瞎子打头碰脸,见了面也彼此打招呼,说两句不疼不痒的闲话,可心里却系了死疙瘩。
这时,刘一溜儿对粑粑三儿说,要拜施杏雨,倒不如去拜郭瞎子。粑粑三儿一下就摸不着头脑了,心想刘一溜儿一直恨郭瞎子,夜里做梦都想掐死他,现在怎么突然又拐弯儿,让自己去投奔他?但再想,又觉着刘一溜儿也许真是好意,倘拜施杏雨,就算他肯答应,学诊脉开方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能学好的,还真不如去跟郭瞎子学一门气摸儿的手艺。
粑粑三儿这一想,也就决定,还是去找郭瞎子。
刘一溜儿不是个大方人,但谁给铺子介绍生意,抽头儿的事却从不含糊。做生意不能一锤子买卖,有抽头儿,也才能有下回,这点道理刘一溜儿的心里自然明镜儿似的。
粑粑三儿这天傍晚从棺材铺出来时,刘一溜儿拿出一块大洋说,还是老规矩,北门里唐掌柜家的这口寿材,抽头儿是一块大洋,你跟崔大杠子爷儿俩怎么分,我就不管了。
粑粑三儿没说话,拿了这一块大洋就出来了。
鼓楼跟前有个小铺儿,专卖羊杂碎。粑粑三儿先在这小铺喝了碗羊汤,就着吃了两个烧饼,就奔西门外的杠房来。崔大杠子还没回来,只有崔大梨在,正帮着一个小伙计准备执事,回头一见粑粑三儿来了,就放下手里的事问,刚才刘一溜儿把你留下,看意思有事儿?
粑粑三儿把一块大洋掏出来,递给崔大梨。
崔大梨接过来看看他,你不要?
粑粑三儿说,都是你的。
崔大梨把这块大洋在手里掂了一下装起来,点头说,行啊,不要就不要,咱表兄弟往后的日子长了,也过得着这个。说完又看看粑粑三儿,问,刘一溜儿还跟你说别的事儿了?
粑粑三儿就把刘一溜儿刚才的话,都对崔大梨说了。
崔大梨听了也有点纳闷儿,想了一下说,他让你,去找郭瞎子?
粑粑三儿点头,说是。
崔大梨说,这刘一溜儿可没准儿,他在西门外这儿说话,你得上东门里那边听去,不能轻信,说不定在哪儿挖个坑,就能让你掉进去,已经这些年了,你还没看出他是吗玩意儿变的?粑粑三儿吭哧了一下说,这我当然知道,可他,跟我爹有交情。
崔大梨摇摇头,你呀,倒霉看反面儿,这话懂吗?
粑粑三儿说,甭管正面儿反面儿,我心里有数。
崔大梨问,郭瞎子前两天出事了,你听说了吗?
粑粑三儿说,这几天忙,没去那边。
崔大梨告诉粑粑三儿,他也是听街上人说的。几天前,水阁大街的医院里抬出个老太太,一帮儿子孙子,一边抬着一边哭。这时医院门口过来个人,是个瘸子,拄着半截拐棍儿,问怎么回事。一个孙子说,这是他奶奶,眼看要不行了,抬到医院来,大夫也不给治了。这瘸子听了朝东头一指说,去找郭瞎子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兴许还有救。孙子一听赶紧问,这郭瞎子是干吗的?瘸子说,气摸儿大夫啊,扎针灸,街上人都知道。说完又用拐棍儿敲敲自己的瘸腿,我当初在炕上瘫了几年,愣是让他扎针给扎好了。这帮儿子孙子一听立刻来了精神,问清这郭瞎子住哪儿,就抬着老太太过来了。郭瞎子那天刚出诊回来,也是累了,又没吃午饭,就在门口小铺叫了两个菜,又烫了一壶酒,正喝着,就见一帮人吆吆喝喝地抬进一个人来。郭瞎子先看了看,是个老太太,再一问,才知道是从医院那边过来的。要在平时,这样的病人郭瞎子就不接了。气摸儿跟一般的大夫还不一样。一般的大夫是先诊脉,再开方。开方也不是随便开,得先用几味平安药儿试一试,行话叫投石问路,药用对了,行话叫投了簧,才在方子上再做适当的加减。但气摸儿不行,扎一针是一针,这一针下去见效还行,不见效也不能有半点差池,倘真有差池就很难说得清了,所以这行的大夫都要先反复看,没有十分的把握不会轻易出手。但这天下午,郭瞎子也是喝了酒,加上在街上已有些名气,也就艺高人胆大,二话没说就让把人抬起来。这帮儿子孙子一听千恩万谢,赶紧抬过老太太放到床上。郭瞎子平时酒量很大,可这个下午空着肚子,喝了几两就已有些酒意。他先拿出针,对这帮儿子孙子说,大夫开方子都讲究投石问路,扎针也一样,我先扎一针,倘有动静了,再说下一步。但这时郭瞎子就忘了,他眼神不好,又没戴老花镜,所以并没仔细看,这老太太这时已经只剩了一口气,且这口气就含在嘴里。就在郭瞎子这一针扎下去的同时,老太太咕的一声把这口气咽了。这一来也就真的很难说清了,谁看了都得说,这老太太就是让郭瞎子这一针活活儿扎死的。老太太的这帮儿子孙子刚才看着郭瞎子,还都一脸的感激,这时立刻就翻脸了,一孙子上前一把揪住郭瞎子,一边哭着一边打,说他奶奶让郭瞎子扎死了,让他偿命。他这一哭一打,别的儿子孙子也都围上来。郭瞎子虽然50多岁,还是壮年,可人瘦,又水蛇腰,哪禁得住这帮儿子孙子这么打。但既然扎死了人,别管怎么说,也自知理亏,索性就倒在地上用两手抱住头,任由人家打,不躲,也不吭声。后来这帮儿子孙子一边哭着打够了,又把郭瞎子的家里砸个稀烂,才抬着老太太的尸首走了。
崔大梨说完,又问粑粑三儿,这么大的事,你没听说?
粑粑三儿摇头说,没听说。
崔大梨想了想又说,要说学一门手艺,当然是好事,总是一辈子的饭辙,可这话也分怎么说。说着又瞄一眼粑粑三儿,你爹有木匠手艺,我爹虽是抬杠的,说起来也算一门手艺,对吧?可你都看见了,有手艺又怎么样,手艺人再怎么说,就算一辈子饿不着,也撑不死。说着就噗地乐了,说白了,耍手艺的也就是这么回事,是个半死不活的营生。
说完看着粑粑三儿,这话,你明白吗?
粑粑三儿眨了下眼,脑子一下转不过弯儿来。
崔大梨说,这么说吧,街上有句话,好汉不挣有数儿的钱。
粑粑三儿听了又想想,好像有点儿明白了。崔大梨还有个兄弟,叫崔二梨。粑粑三儿知道,他兄弟俩一直在外面合伙儿倒腾事儿,但具体干的是哪一行的生意,连他们的爹崔大杠子也说不清楚。这时崔大梨看着粑粑三儿,又噗地乐了,有几分得意地说,说不清楚就对了,我俩干的事儿,要让我爹知道了,就得吓死。说着把脑袋凑过来问,前些天城外又打仗了,知道吧?粑粑三儿一听,就把眼瞪起来。这些日子城外经常响枪响炮,他当然知道。
崔大梨说,打仗是直隶总督操心的事,跟咱百姓没关系,可赚钱,就跟咱有关系了。
粑粑三儿仍然瞪着崔大梨。
崔大梨又说,详细的就甭跟你说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咱不偷不抢,干的都是本分事,没吗了不起的,我这么劝你,是想说,你要愿意,就跟我俩一块儿干。
粑粑三儿慢慢低下头,显然是在心里寻思。
崔大梨说,咱是亲表兄弟,往上说,是一个姥姥,不会让你吃亏的。
粑粑三儿又沉了一下,抬头说,我再想想。
粑粑三儿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还是去找郭瞎子。
粑粑三儿是第二天下午来找郭瞎子的。如果从街西头过来,得经过一溜儿堂棺材铺。虽然刘一溜儿也说,让他去找郭瞎子,但粑粑三儿真决定了,还是不想让刘一溜儿知道。粑粑三儿记住了爹当初说的一句话,自己心里想的事,只自己知道就行了,外人甭管谁,都不能说,除了自己爹妈,这世上没有真跟你一心儿的人,嘴上说得再好听,你也别信,心里怎么想的不用猜也能知道,你好了,他生气,你坏了就看乐儿,气人有笑人无,走到天边儿也是这么回事。粑粑三儿故意去海河边绕了一个大弯儿,从水阁大街的东头过来。郭瞎子的门脸儿房在一棵老槐树的旁边,门窗都擦得挺干净。粑粑三儿进来时,郭瞎子正背身坐在方桌跟前,水蛇腰扭出一个弯儿,背也有些驼。听见身后有动静,没回头说了一句,把门关上。
粑粑三儿在门口站了一下,就回身把门关上了。
郭瞎子不说话了,继续在方桌跟前忙自己的事。
粑粑三儿慢慢走过来。方桌上铺着一块粗布,粗布上摆着一溜儿长长短短的银针,短的一寸多长,长的有大半尺。郭瞎子戴着老花镜,正一根一根地擦这些银针。粑粑三儿来到近前,郭瞎子没抬头,捏着一根三寸多长的银针一边擦着说,你是程木匠的儿子?
粑粑三儿说,是。
粑粑三儿明白了,郭瞎子经常在棺材铺的门口过,铺子里的事都知道。
郭瞎子问,有事?
粑粑三儿犹豫了一下,没说话。
郭瞎子说,有事就说吧。
粑粑三儿定了下神,已经到这时候,也就不想再绕弯子,于是说,我想学气摸儿。
郭瞎子好像并不意外,把手里正擦的银针放下,又把老花镜从鼻梁子上摘下来,放到面前的方桌上,抬头看一眼粑粑三儿,忽然笑了,点头说,你叫粑粑三儿?
粑粑三儿说,是。
郭瞎子说,你爹怎么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
粑粑三儿想了想,觉着这话没法儿接。
郭瞎子又摇摇头,你现在来找我,胆子不小啊。
粑粑三儿明白了,郭瞎子的意思是,他这里刚出了事,家都让人砸了,现在别说有人来看病,街上的人见了他都绕着走。粑粑三儿说,我爹说,你是个好大夫。
郭瞎子点头,你爹也是个好手艺人,他做的活儿,我见过。
粑粑三儿又说,我爹说过,让我来找你。
郭瞎子听了,抬头看一眼粑粑三儿。
粑粑三儿把郭瞎子的目光避开了。
粑粑三儿说的这话撒谎了。也不是全撒谎,前面说的是实话。他爹活着时,确实说过,郭瞎子是个好大夫,但并没说让他来找郭瞎子。他这样说,当然是为了让郭瞎子高兴。
果然,郭瞎子笑了一下。粑粑三儿一看郭瞎子笑了,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郭瞎子突然又问,你去济生堂药铺找施杏雨了?
郭瞎子这一问,粑粑三儿的心一下又提起来。
粑粑三儿前一天带着崔大梨去棺材铺时,没跟刘一溜儿说实话。刘一溜儿问他,去没去济生堂,他说还没去,但其实已经去过了。那天上午去给刘一溜儿谢孝,从棺材铺一出来,他就去了济生堂药铺。粑粑三儿自从把爹发送了,自己也有点儿不认识自己了。过去爹总说,男人最怕没瘖子。粑粑三儿理解,爹说的没瘖子,也就是没主意的意思。爹总说,粑粑三儿遇事拿不准主意,男人这样不行,将来不光吃亏,也干不成大事。可自从把爹发送走了,粑粑三儿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光有瘖子了,再遇事也有主意了。他这次来给刘一溜儿谢孝,看着是想让刘一溜儿帮着拿个主意,可其实来之前,以后究竟入哪个门,走哪条路,心里已经盘算好了。所以当时刘一溜儿一听他说,想去找施杏雨,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含糊地点了下头,粑粑三儿的心里就明白了,如果真跟刘一溜儿提出来,让他给施杏雨递个话儿,肯定得碰钉子,说了还不如不说。这一想也就改了主意,没再说别的,扭头就出来了。
但粑粑三儿去济生堂药铺时,心里还是没底。粑粑三儿曾听街上的人说过,施杏雨这人的底儿很深,脾气也隔色。底儿深,指的是心计。不过在街上混饭吃,当然得有心计,且心计浅了还不行,真像一碗清水,能让人一眼看到底,在街上也就没法儿混了。但脾气隔色,就让人吃不准了,甭管急性子还是慢性子,脾气火暴还是绵软,都好说,这些都在明面儿,但隔色的脾气让人摸不透,也就不知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粑粑三儿也有心理准备,大不了碰钉子,真碰了也就碰了,他施杏雨总不能咬自己一口。
这一想,也里也就踏实了。
让粑粑三儿没想到的是,施杏雨竟然是个挺随和的人,话不多,声音也不大。他显然知道摔寿材的程木匠,一听是程木匠的儿子,把粑粑三儿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问,你是从刘一溜儿那儿来?粑粑三儿没想到施杏雨会这么问。这一问也就好办了,正好随口答音儿,于是点头说,是。施杏雨又问,是他让你来的?粑粑三儿又说,是。施杏雨接着又问了一句,他怎么说?这一下把粑粑三儿问住了,看看施杏雨,话在嘴里转了转,没说出来。施杏雨跟刘一溜儿曾是师兄弟,当年又闹翻了,但到底翻成什么样,是各走各的,再也不来往了,还是已经反目成仇,粑粑三儿的心里没底。倘是前者还好办,毕竟是同门师兄弟,还有情分在,而如果是后者就麻烦了,也许有刘一溜儿这一层,反倒不如没有。这时施杏雨一直盯着粑粑三儿。粑粑三儿偷瞟一眼。施杏雨的脸上没表情,就像一层雾,怎么看也看不透。粑粑三儿这时已经想到了,甭管自己说,刘一溜儿是怎么说的,施杏雨都会有一句现成的话等着,既然他让你来找我,他怎么不把你留在棺材铺?于是,粑粑三儿说,我来时刘掌柜说了,既然我不想再像我爹,吃这碗阴阳饭,索性就来找你,你这一行的碗饭牢靠,从古至今,哪个朝代也没有饿死大夫的。施杏雨听了,叮问一句,刘一溜儿是这么说的?粑粑三儿一咬牙点点头,就是这么说的。施杏雨说,好吧,我信。说完沉了一下,摇摇头,就算刘一溜儿真这么说了,你来我这儿,也是舍近求远。粑粑三儿听了,看看施杏雨,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施杏雨说,水阁大街上有郭瞎子,就在一溜儿堂的旁边,你怎么不去找他?粑粑三儿这才明白了,施杏雨是有往外推的意思。施杏雨好像看出粑粑三儿的心思,又摇了摇头,我不是往外推你,这么说吧,一来,当大夫没这么简单,没有几年的工夫下不来,就算功夫下到了,也不一定真能学成个好大夫,买卖生意半羼子也就半羼子了,当大夫是人命关天的事,真凭着半羼子的功夫干这行兴许就是杀人,再者,街上的这潭水深了,跟你说好话的不一定是为你好,说话扎耳朵的,也不一定就不是好人,此外还有一宗,郭瞎子是气摸儿大夫,气摸儿虽是另一路,但也算岐黄之术,当年跟我这行同出一门,学着也容易些。粑粑三儿一边听着一边寻思,也觉着施杏雨说得有理。刚要张嘴,施杏雨又说,你先去找郭瞎子吧,看他怎么说,他不行,你再回来。粑粑三儿听了,也就只好出来了。所以,他那天下午和崔大梨又去棺材铺时,一听刘一溜儿说,也让他去找郭瞎子,心里就有点儿意外。他没想到,刘一溜儿竟然跟施杏雨说的一样。甭管他两人想的是不是一回事,但至少去找郭瞎子,是对的。
这时,粑粑三儿一听郭瞎子问,就知道瞒也瞒不过去了,只好承认说,是。
郭瞎子问,施杏雨怎么说?
粑粑三儿又犹豫了一下,就把施杏雨的话说了。但前面的话没说,只说了最后一点儿,看一眼郭瞎子,说,他说诊脉开方吃功夫,没个几年下不来,跟你学气摸儿,还容易一些。
郭瞎子听了摇摇头,叹了口气。
粑粑三儿看看郭瞎子,不知他这叹气,是什么意思。
郭瞎子说,我跟这施杏雨只在街上见过两回面,虽不认识,也一直拿他当个知己,这知己倒不是因为同行,说起来都是杏林中人,也觉着他该最懂气摸儿,可现在听他一说,看来这行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懂局,也难怪,隔行如隔山,这山不光在行外,有时也在行里。
粑粑三儿听了想想,脑子一时又转不过弯儿来。
郭瞎子把桌上的银针在粗布里归置了归置,横着一叠,又一叠,再竖着来回一折,拿起来递给粑粑三儿。粑粑三儿看看这粗布包儿,又抬头看看郭瞎子。郭瞎子没戴老花镜,两个眼里像有米汤,他揉了一下说,其实这世上的事,都讲个缘分,这个给你,先拿去吧,人这辈子出一门进一门不是简单的事,回去再想想,想好了,要是有缘,再来找我。
说完,就起身进里面的屋去了。
粑粑三儿既然来找郭瞎子,本来已不用再想。但郭瞎子这么一说,心里就又有些犹豫了。用施杏雨的话说,虽然他和郭瞎子都是杏林中人,吃的是行医这碗饭,可从两人的穿着打扮儿,浑身上下的意思,还是看出不太一样。施杏雨穿一件蟹青长衫,从上到下一尘不染,黑缎子的瓜皮帽方方正正戴在头上,细皮白肉的脸看着也很光洁。济生堂药铺靠墙有一把红木太师椅,是施杏雨的专座,跟前摆着红木茶几,对面放着一个硬木杌子,来求诊的人先在杌子上坐着,把手腕放到红木茶几的脉枕上,施杏雨才不慌不忙地伸手诊脉。郭瞎子的家里却不像诊所,看着倒像个放杂物的堆屋,身上的衣裳也不讲究,一件黑布褂子皱皱巴巴的,前襟儿上还粘着几块棒子面儿粥的嘎巴儿。粑粑三儿回到家里,再细一想,俗话说,人凭衣裳马凭鞍,倘自己真拜了这郭瞎子,干几年气摸儿,是不是也得成了他这模样儿?
想到这儿,粑粑三儿也就不再犹豫了,人往高处走,还是去拜施杏雨。
粑粑三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换了身干净衣裳,就从家里出来。济生堂药铺是在南门里,粑粑三儿走到鼓楼往南一拐,想了想又站住了。人办事,得讲个信用,既然头一天去找过郭瞎子,郭瞎子还送给自己一包银针,让自己回来再想想,现在就算决定了,不入气摸儿这行,也该给人家一个回话儿,总不能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了。
这一想,他就又掉头往回走。
出东门来到水阁大街,快到那家女医院了,粑粑三儿才猛然想起来,医院的斜对面就是一溜儿堂棺材铺。粑粑三儿这时不想见刘一溜儿。刚要拐进旁边的一个胡同,已经晚了,远远看见刘一溜儿站在铺子门口,正朝这边招手。粑粑三儿只好站住了,犹豫了犹豫,就朝这边走过来。刘一溜儿这个上午看着心情挺好,脸上的气色也很好,手里捧着个白铜的水烟袋,在太阳底下锃亮,见粑粑三儿来到跟前,就问,你是来找我,还是去找郭瞎子?
刘一溜儿这一问,粑粑三儿愣了愣,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要说是来找刘一溜儿的,一时想不起找他有什么事,可要说去找郭瞎子,跟郭瞎子的这点事,又不想让刘一溜儿知道,心里寻思了一下,还是如实说,打算去找郭瞎子,跟他说点事儿。
刘一溜儿噗地一乐说,你来晚了。
粑粑三儿没听懂,看看刘一溜儿。
刘一溜儿用手里的水烟袋朝东面一指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粑粑三儿没动,顺他指的方向看了看,又看看刘一溜儿。
刘一溜儿又乐着说,去吧,去看看吧。
粑粑三儿就朝这边走过来。到跟前才发现,郭瞎子的家敞着门,伸头往里看看,屋里有几个人正归置东西,看意思是在腾房。一个秃头的胖子把一个破柜子搬出来,扔在街边的树根底下,拍了拍手上的土,正要进去,粑粑三儿过来问,郭大夫在吗?
胖子看看他,你说郭瞎子?
粑粑三儿说,是。
胖子说,走了。
粑粑三儿没听明白,走了?
胖子说,搬走了。
粑粑三儿忙问,你们是?
胖子说,卖嘎巴菜的。
说完就又进去了。
粑粑三儿站在老槐树的底下,又朝屋里看了看,就转身回来了。刘一溜儿还站在自己铺子的门口,一边咕噜咕噜地抽水烟,冲粑粑三儿乐着说,进来吧,喝口水。
粑粑三儿说,不了,还有事。
粑粑三儿一边朝东门里走着,一边心里再想郭瞎子昨天对自己说的话,就明白了。显然,他当时说,要是有缘,再来找他,意思指的不是现在,而是说以后。这一想,也就有些庆幸,看来自己决定去找施杏雨,还是对了,郭瞎子打算走,应该是早就想好了。
粑粑三儿这个上午从水阁大街出来,进东门走到鼓楼跟前,想了想,又改了主意。本来早晨出门时,心气儿挺高,想着施杏雨前面已经有话,这个上午再去济生堂药铺找他,应该一说也就成了。可现在一见郭瞎子不辞而别,就这么走了,心里又有点儿发空,再去济生堂药铺也就没心思了。这么想着,就转身回家去。到家已是将近中午,随便吃了口饭,一头扎到床上就睡着了。下午起来,正寻思着还去不去济生堂,崔大梨来了。崔大梨显然中午刚喝了酒,脸通红,手里拎着个包袱。这包袱系得不紧,口儿上露出里面的东西,看出是团着的麻袋。一进门还急着要走,问粑粑三儿,头天说的事儿,想得怎么样了。
粑粑三儿刚睡醒,脑子一下没反应过来。
想了想问,头天说的吗事儿?
崔大梨一跺脚,嘴里喝的一声说,我这儿还等着呢,你倒忘啦?
粑粑三儿这才想起来,前一天下午去西门外的杠房,崔大梨曾劝他,跟他们兄弟俩一块儿干。当时自己说,回去寻思寻思。现在郭瞎子已经走了,只剩了施杏雨这一条路,还不一定能行,于是想了一下,试探着问,你们干的,到底是哪路营生?
崔大梨朝他看看说,先说好,你干还是不干?
粑粑三儿说,我得先知道,干的是哪行。
崔大梨摇头,你得先定下干,才能跟你说,要不干,就不能说了。
粑粑三儿低下头,没吭声。
崔大梨又一跺脚说,我那儿还忙着,没工夫儿跟你打八岔。
粑粑三儿还是没吭声。
崔大梨哼一声说,你自个儿接着寻思吧。
说完就急急地走了。
粑粑三儿看着崔大梨走了,又坐着愣了一会儿。粑粑三儿也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快奔二十了,如果去济生堂药铺找施杏雨,就算人家答应了,可跟着学诊脉开方,没个十年八年的工夫也成不了能自己坐诊的正经大夫。而跟着崔大梨兄弟俩干,饭碗就是现成的,说白了一伸手就能有钱挣,挣了钱也就有饭吃。但话又说回来,让粑粑三儿一直犹豫不定的也就是这个挣钱的事。自己跟崔大梨兄弟俩是表兄弟,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跟着他们一块儿干当然比跟外人干强,但表兄弟是表兄弟,一沾钱的事,就难说了。粑粑三儿知道崔大梨的脾气,人倒不是奸,是滑,遇事心眼儿多,平时论着是表兄弟的情分,可真到一块儿赚钱的时候,这情分还能有多少,粑粑三儿的心里没底。过去有爹在,遇到什么事还能跟爹商量,现在只剩自己了,再有事,怎么来怎么去就得自己先想明白了。崔大梨虽然一直不肯说他兄弟俩究竟干的是哪路营生,粑粑三儿也知道,他们干这营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爹活着时,一次和崔大杠子一块儿喝酒,崔大杠子喝大了,一边抹着泪说,儿大不由爷啊,本来想的是,让他兄弟俩也来杠房,怎么说也算一门手艺,可好说歹说就是不听,还整天在外面折腾,现在也想开了,甭管他们混好混歹,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这时,粑粑三儿想,崔大梨现在突然提出来,让自己跟他兄弟俩一块儿干,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看自己刚把爹发送了,只剩一个人了,想给自己找个饭辙;二是他兄弟俩的营生最近忙不过来,需要找个帮手,找外人又不放心,所以才想拉自己去一块儿干。不过,粑粑三儿明白,凭崔大梨的为人,要说心疼自己,想给自己找个饭辙,应该不太可能,他也没这份儿心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他们找自己,只想找个帮手。不过,粑粑三儿刚把爹送走几天,再想事,脑子也学会拐几个弯儿了。眼下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三条路,要么去一溜儿堂棺材铺找刘一溜儿,要么去济生堂药铺找施杏雨,要么就索性跟着崔大梨兄弟俩一块儿干。第一条路去一溜儿堂,肯定不行,爹当初就说过,不想让自己再吃阴阳饭,况且这刘一溜儿也不像能靠得住的。这样一来,也就只剩后面这两条路了。而这两条路比起来,当然还是前者更稳妥一些,实在不行了,总不能瞪眼等着饿死,再答应崔大梨也不迟。
这么一想,粑粑三儿心里也就明白了,于是穿上衣裳,又从家里出来。
粑粑三儿一路走着心想,甭管施杏雨怎么说,这回也就这一锤子买卖了。
济生堂药铺是上午人多,下午人少,来求诊问药的都是一早过来,这时将近傍晚,铺子里已没人抓药,也就挺清静。施杏雨收拾起东西,正准备回去,一抬头,见粑粑三儿进来,就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粑粑三儿来到施杏雨跟前,在对面的杌子上坐下了。
施杏雨说,郭瞎子走了?
粑粑三儿有些意外,没想到施杏雨的耳朵这么灵,郭瞎子刚走就知道了。
于是粑粑三儿点头说,是。
施杏雨嗯一声,他现在走,就对了。
粑粑三儿听了,看看施杏雨。
施杏雨说,要是再晚几天,还能不能这么囫囵着走都得另说了。
粑粑三儿更不明白了,觉着施杏雨这话越说越玄。
施杏雨笑笑问,你知道这毛病在哪儿吗?说着又点了下头,你应该知道。
粑粑三儿隐隐地有些明白了,施杏雨指的,应该是刘一溜儿。粑粑三儿这次来,既然心里已打定主意,成不成也就这一下子了,索性也就不再拐弯儿,看着施杏雨说,我问句不该问的话,听说,当初刘一溜儿做汗门生意,跟你,是师兄弟?
施杏雨说,是,不光是师兄弟,他还是我的师兄。说着又笑了,看一眼粑粑三儿说,有句老话,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听过吗?
粑粑三儿想想,这话确实听爹说过。
施杏雨说,我这一说,你就该明白了。
施杏雨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也不大。但说话声音不大也分两种,一种是已经没底气,声音大不起来,还一种是本来中气十足,只是故意压着声音。施杏雨就是后者。他先端起跟前的茶盏喝了一口,才说,都说汗门生意是卖野药儿的,这话对,也不全对,其实只是鱼龙混杂。施杏雨一说起江湖的事,声音就更低了。卖药的在街上叫皮门生意,也叫汗门生意,但皮门和汗门还不是一回事。皮门虽也是卖药的,但一般做的是正经生意。汗门有正经的,可也有不正经的,不正经的说白了,也就是蹲在街边儿卖野药儿的。街上有句话,叫九金十八汗,金门指的是相面算卦,而汗门说是十八汗,其实还不止十八种,在路边儿光膀子扎板儿带,打把势练武卖大力丸的,叫将汗;点眼药水儿的叫招汗;剔牙虫儿的叫柴汗;在街边摆一溜儿小口袋,里边装着药须梗子的叫根子汗;拿几块猴头熊掌当招幌,弄些猫狗骨头愣说是虎骨让人去泡酒的,叫山汗;还有卖鸡血藤嫩海燕儿海马驹子血三七的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施杏雨当年入汗门,学的是坨汗。坨汗也就是卖膏药的。当时的师父很有些名气,姓李,在街上都叫坨儿汗李,卖的膏药是真膏药,且是好膏药,专治跌打筋损五劳七伤,但每天的膏药只卖50贴,多一贴也不卖。施杏雨入门时,坨儿汗李的跟前只有刘一溜儿一个徒弟。坨儿汗李的膏药是在街上摆摊卖,自从施杏雨来了,他也就不再出来,每天只让刘一溜儿带着施杏雨看摊儿。坨儿汗李毕竟有些名气,50贴膏药不到半天儿也就卖完了。其实一直有人劝他,每天再多做些膏药。但坨儿汗李说,膏油子有限,多做也能做,可做出来的就不是这个膏药了。施杏雨为此很佩服师父,也真想跟着学点本事,每天在街上卖膏药也就尽心尽力。但刘一溜儿的心思却不在这摊儿上,后来干脆说,他还有别的事,就经常让施杏雨一个人看摊儿,自己不知去哪儿了。施杏雨起初也没在意。一天快中午时,师父坨儿汗李突然来了。当时刘一溜儿又没在,坨儿汗李问他去哪儿了。施杏雨说不出来,吭哧了一下说,他说有事。坨儿汗李从摊儿上拿起一贴膏药,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没说话,揣在身上就扭头走了。过了一会儿,刘一溜儿回来了。刘一溜儿一听说师父刚才来过了,脸色立刻变了,问施杏雨,师父说什么了。施杏雨说,没说什么,拿了一贴膏药就走了。刘一溜儿一听更急了,拧起脸说,你怎么让师父把膏药拿走?施杏雨说,师父要拿,我拦得住吗。刘一溜儿说,你要是把膏药都卖了,他还能拿吗?施杏雨一听,觉着刘一溜儿越说越没道理了,在街上看摊儿卖膏药,早卖完晚卖完,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吗?但他心里这么想,嘴上还是没说出来。两人赶紧收了摊儿,就一块儿回去了。
施杏雨这时并不知道,这个上午,已经有人来找过坨儿汗李。这来的人拿着一贴膏药,举着给坨儿汗李看,说他坨儿汗李怎么也做这种烂膏药,跟街上卖的狗皮膏药差不多了,膏油子一烤就化,往身上一贴,能烫出一堆燎泡,这哪是治病,简直是害人。坨儿汗李一听就愣了,他做了这些年膏药,膏油子都是自己亲手熬的,还从没出过这种事。接过来一看,立刻看出了毛病,自己的膏药是白麻布的,而这贴膏药却是旧纺布,灰不溜秋的像一块王八皮。这来的人叫徐二,是在东门外拉水车的,平时难免抻了胳膊扭了脚,也就经常用坨儿汗李的膏药。这时坨儿汗李说,你既然经常用我的膏药,就应该能认出来,还别说膏油子,你先看看这膏药布,我用的是白麻布,可这是烂纺布,怎么能是我的膏药?徐二听了说,是啊,我一开始也不信,可这贴膏药就是在你摊儿上买的,这还能有错?坨儿汗李一听,立刻又是一愣,先把这徐二安抚走,就奔街上的膏药摊儿去。在这个中午,施杏雨和刘一溜儿回来时,坨儿汗李正黑着脸等在家里。一见他二人回来了,啪地把手里的膏药扔在桌上,问他二人,这是怎么回事。刘一溜儿先伸过头来看看,眨了眨眼,也回头问施杏雨,这是怎么回事?施杏雨本来让师父一问,已经给问蒙了,这时刘一溜儿再问,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坨儿汗李的脸气得铁青,指着桌上的这贴膏药说,我自己的摊儿上卖的不是我的膏药,你俩的本事太大了,比我本事还大,以后我得叫你俩师父了!刘一溜儿先看一眼施杏雨,就对坨儿汗李说,师父您先别急,我这几天家里有事,住南市的一个表大爷病了,家里没人,得经常过去看看,摊儿上的事就没顾上。坨儿汗李打断他说,我现在就想知道,这膏药到底是哪儿来的?刘一溜儿一听就回头问施杏雨,这膏药到底是哪儿来的?施杏雨这时已经彻底蒙了,刘一溜儿是大师兄,摊儿上的事一直是他说了算,自己只管盯摊儿,这每天的50贴膏药都是刘一溜儿一早拿来的,中午卖完了,钱也是他交给师父,两头儿的事自己都不经手。坨儿汗李这时反倒心平气和了,点头说,我今天已经看了,摊儿上膏药都是假的,我就想知道,我的那些膏药哪儿去了?说完看看刘一溜儿,又看看施杏雨,见他俩都不开口,就叹了口气说,看来你们师兄弟的心真齐啊,没想到,合起伙儿来一块儿糊弄我。刘一溜儿想了一下,赶紧说,师父您甭生气,我先好好儿问问老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完就要拉施杏雨出来。坨儿汗李说,你也不用问了,我坨儿汗李卖了半辈子膏药,在街上还没栽过这样的跟头,看来我没这德行,根本就不配有徒弟,你们都走吧,从今以后,咱在街上再碰见,就当谁也不认识谁。
他说完挥挥手,就起身进里屋去了。
其实这时,施杏雨的心里已经明白了。每天在街上看膏药摊儿的只有自己和刘一溜儿两个人,如果捣鬼的不是自己,也就只能是刘一溜儿。况且他在师父面前说的话也明显藏着奸,他说让师父先别生气,他再好好儿问问老二。这一说,也就先把他自己洗出来了,等于明着告诉师父,这事儿他不知道,所以与他无关,自然就是老二干的。施杏雨虽比刘一溜儿小几岁,街上的事也明白一些。这天从坨儿汗李的家里一出来,刘一溜儿就跺着脚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弄成了这样?施杏雨看看他,本想对他说,既然已让师父清了门户,以后咱在街上再碰见,也就只当谁也不认识谁吧。但想了想,觉着说这种绝话已没意思,就扭头走了。
后来过了些日子,刘一溜儿又来找施杏雨,想拉他一块儿去见坨儿汗李,说,过去这些日子了,也许师父的气已经消了。但这时施杏雨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施杏雨也是无意中听街上人说的。原来刘一溜儿认识一个在南市卖膏药的,这人虽也是做正经生意的,但自己不会熬膏药。刘一溜儿就跟他说,可以把坨儿汗李的膏药转手给他。坨儿汗李在老城里的名气很大,这人一听当然高兴。但刘一溜儿也明白,这种事当然不能天天干,也就只是隔三岔五,先从坨儿汗李那里拿了膏药,再换成在街上卖野药儿的手里买的假膏药,把这假膏药拿到膏药摊儿上,让施杏雨当真的卖,他再把那些真膏药倒卖给南市那个卖膏药的人。
施杏雨沉了一下,又看看粑粑三儿说,还有个事,恐怕你也不知道。
粑粑三儿盯着施杏雨,没说话。
施杏雨问,你爹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粑粑三儿说,摔寿材时,斧子砸破了手腕子。
施杏雨说,你爹摔了这些年寿材,手没少破,怎么单这回死了呢?
粑粑三儿说不上来了。其实这事,粑粑三儿也想过,总觉着爹这回死得蹊跷。
施杏雨说,要说你爹,这回太冤了,自己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就这么死了。说着又叹口气,这事儿,我也是这两天刚听说的。说完看一眼粑粑三儿,先说下,这话我一说,你一听,咱是哪儿说哪儿了,你当真也行,可不许去找刘一溜儿,更不能说是听我说的。
粑粑三儿点头嗯了一声。
施杏雨这才告诉粑粑三儿,刘一溜儿认识西门外北小道子一个叫二疤瘌眼儿的人。这二疤瘌眼儿是个专干偷坟掘墓营生的。刘一溜儿对二疤瘌眼儿从坟里偷出的东西不懂局,但是对他挖出的椁板却懂。有钱的大户人家,下葬不光用棺材,棺材的外面还有一层,叫椁,这椁的木料有的比棺材还讲究,刘一溜儿就跟二疤瘌眼儿说好,挖出的椁板赶上有好的,还没糟朽,就卖给他的棺材铺。施杏雨对粑粑三儿说,你爹这次摔寿材,刘一溜儿让他用的就是这种椁板。粑粑三儿立刻想起来,当时他帮爹摔寿材,爹曾说过,这木料都是旧的,闻着还有一股怪味儿。施杏雨说,这椁板虽在棺材外面,不挨着死人,可年头一多,死人的东西流出来,也能渗进这椁板,这是尸毒,人沾上了很难治,你爹这次碰破手腕子,也就是沾了这种尸毒。说着又摇摇头,他要是早来找我,也许还死不了。
粑粑三儿一听,这才明白了。
施杏雨看一眼粑粑三儿,又问,这郭瞎子,你知道是为吗走的吗?
粑粑三儿说,听说头些天,他扎死了人,让人家打了,把家也给砸了。
施杏雨问,这是刘一溜儿告诉你的?
粑粑三儿说,我表兄听街上人说的。
施杏雨又沉了沉,说,跟你说吧,这事儿,也是刘一溜儿让人干的。
粑粑三儿听了立刻瞪起眼,刘一溜儿竟然还干出这种事,这他真没想到。
想了想,粑粑三儿还是不太相信,又问,他为吗这么干?
施杏雨笑笑说,天底下开棺材铺的,跟大夫都是对头,这你还不明白吗?说着又一摇头,他这几年是没逮着机会,要逮着机会了,早就想法儿把我也整死了。
施杏雨一边说着就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了,看一眼粑粑三儿,又说,有句老话,叫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跟你说句透底的话吧,你这辈子干别的行,可干不了这行,还是想个别的饭辙吧。说完,又招呼了一声铺子的伙计,把门板上了,就挟着自己的诊包儿走了。
粑粑三儿在往回走的路上再想,也就明白了,施杏雨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收自己。他让自己来,只是想把这些事告诉自己,目的是让自己知道刘一溜儿是什么人,别去他的棺材铺。
粑粑三儿想,施杏雨还是想错了,其实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想去刘一溜儿的棺材铺。
粑粑三儿终于决定了,还是跟着崔大梨兄弟俩一块儿干。人总得吃饭,甭管他兄弟俩干的是哪路营生,先说有饭吃,能长干就长干,倘不能长干,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天一大早,粑粑三儿就奔西门外的邢家胡同来。粑粑三儿知道,崔大梨兄弟俩平时虽跟他们的爹崔大杠子一块儿住,但在邢家胡同还单有一间小房儿。这小房儿是租的,他兄弟俩在这小房儿里有自己的事。粑粑三儿曾跟着崔大梨来过这边,所以认识。
邢家胡同是南北向,北边顶着西关大街。粑粑三儿出西门,沿西关大街走了一段就拐进胡同。崔大梨兄弟俩的这间小房儿说是房,其实就是个没挂瓦的灰棚儿,窝在一堵大墙的后面,很不起眼,即使来到跟前也看不见里面。粑粑三儿绕过大墙看看,门没锁,但屋里没人。心里正犹豫,是在这儿等一会儿,还是去杠房那边找,就见崔大梨兄弟俩回来了。崔大梨的身上背着个大麻袋,崔二梨跟在后面。崔大梨和崔二梨虽是亲兄弟,但看着不像哥儿俩。崔大梨是个胖子,大高个儿,浑身上下五大三粗。崔二梨却瘦小枯干,长得也尖嘴猴腮。崔大梨一见粑粑三儿等在门口儿,做了个手势。崔二梨开了门,粑粑三儿就跟进来。崔大梨先把身上的麻袋扔到地上,长出一口气,让崔二梨把门关上,才回头问粑粑三儿,想好了?
粑粑三儿说,想好了。
崔大梨说,就是啊,咱是自己人,能让你吃亏吗?
粑粑三儿说,现在你能说了,到底干的是吗买卖?
崔大梨没说话,把地上的麻袋解开,抓住底下的两个角儿使劲一掀,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粑粑三儿立刻闻到一股噎人的怪味儿,伸头一看,竟是一堆黄军服。再细看,只觉头发根儿一下都立起来,跟着嗓子眼儿一顶,差点吐出来。这黄军服上有一片一片黑紫色的血污,有的已经干硬,还有的仍然湿漉漉的。这才明白,这股奇怪的味道是血腥味儿和死人的恶臭。
崔大梨回头冲粑粑三儿说,明白了?干的就是这个买卖。
粑粑三儿的脑子一下还没转过弯儿来。
崔大梨说,从去年秋上,天南地北的军队都开过来,整天你来我走,不是在津南打仗就是在津北交火儿,当然打仗是他们的事,连直隶总督都管不了,跟咱平头百姓就更没关系,可他们打死的人,就跟咱有关系了。崔大梨见粑粑三儿没听懂,就又说,人死了,可身上的衣裳还能用,又是军服,明白了吗?旁边的崔二梨见粑粑三儿还不明白,就乐了,过来说,甭管哪儿的队伍,死了人就得补充兵员,新兵总不能光屁股,可军需又跟不上,他这空缺也就正好是咱的买卖。崔大梨噗地乐了,说,把死人的衣裳卖给活人,这买卖多合适,无本求利,只赚不赔。说着又拍拍粑粑三儿的肩膀,就一样,得有胆儿,没胆儿干不了这个买卖。
崔二梨说,不光有胆儿,还得禁得住事儿。
粑粑三儿这才明白了,跟着浑身的汗毛就都竖起来,敢情崔大梨兄弟俩一直干的营生,是从死人身上扒衣裳。但想了想,还是不明白,这扒来的衣裳怎么出手,卖给谁?崔大梨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说完就开始和崔二梨忙起来,先把这堆军服一件一件整理好,上衣跟上衣放一堆,裤子跟裤子放一堆,然后又翻衣兜里的东西。崔二梨一边翻着嘟囔说,这些穷当兵的,兜里没吗值钱的东西,可有时也能翻出点儿有用的。翻了一会儿,崔大梨就让粑粑三儿帮着把这些军服抱到院里。粑粑三儿这才发现,在院子角落有一口大水缸。军服泡进缸里,又倒了些火碱,崔大梨就用一根棍子在缸里来回搅。搅了一会儿,缸里的水就红了。捞出来,又换了清水,再涮了一下这些军服就干净了。粑粑三儿这时才明白,崔大梨兄弟俩为什么选择这间小房儿。这小房儿的前面有大墙,外面也就看不见里边的小院。这时崔二梨已在小院里拴了几根绳子。把这些军服捞出来拧干,就都在绳子上晾起来。
崔大梨看看已是中午,擦了擦手说,走,喝酒去。
从邢家胡同出来,把着街边有一个卖烩饼的小铺儿。崔大梨和崔二梨各要了一碗素烩饼。粑粑三儿这时已经吃不下东西,一想刚才的恶臭腥味儿就想吐。看着他兄弟俩又各要了二两老白干儿,就着素烩饼一边吃一边喝,跟他俩打个招呼,就从这小铺儿出来了。
粑粑三儿回到家也没吃午饭,一想刚才的那堆烂军服心里就一翻一翻的,直想吐。崔大梨兄弟俩敢情干的是这种营生,如果这样,这事儿就得再寻思寻思了。当初爹说过,阴阳饭不好吃,本来不想让自己再进这一行,后来跟着学木匠,摔寿材,也是出于无奈。可现在这阴阳饭算是吃到家了,竟然从死人身上扒衣裳。粑粑三儿一想,身上就直起鸡皮疙瘩。但转念再想,现在如果不干这个,也已无路可走了。施杏雨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粑粑三儿不适合干行医这行,说白了,也就是不想收自己。而如果按施杏雨所说,刘一溜儿竟然是那种人,也不可能再去他的一溜儿堂棺材铺。退一步说,就是真想去,看刘一溜儿的意思,也没打算要自己。粑粑三儿这一想,也就明白,眼前只有这一条路了。崔大梨眼毒,中午已经看出来,这事儿把粑粑三儿吓着了,所以在粑粑三儿临走时就对他说了一句,晚上老二去西门外的杠房有事,这边缺人手儿,粑粑三儿要是想过来,天黑就过来。当时粑粑三儿没说话,但已听明白了,崔大梨的意思是让他回来再想想,如果想好了,还跟着干,晚上就去找他。这时,粑粑三儿终于想好了,既然已经没有别的路,这条路是泥是水,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天大黑时,粑粑三儿又来到邢家胡同。崔大梨已经把院里晾的军服都收进来,一件一件叠得很平整。这些军服用火碱烧过,颜色浅了一些,但浅得很自然,像是经过风吹日晒已洗得发旧,也看不出一点有血渍的痕迹。崔大梨把这些军服分成两个大包袱,系好,自己拎起一个背在身上,冲粑粑三儿指了指另一个,就头前出门去了。粑粑三儿赶紧背起这个包袱,跟在崔大梨的身后出来。天一黑,街上就清静了。粑粑三儿跟着崔大梨沿西关大街从西门进来,一直往东走,过了鼓楼,还往东。粑粑三儿越走越含糊,不知崔大梨这是要把这些军服往哪儿送,有心想问,可是看崔大梨在前面走得挺急,就又忍住了。
出了东门,穿过东马路,眼看着上了水阁大街,粑粑三儿实在忍不住了,紧走几步追上来,问崔大梨,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崔大梨已经走出一头汗,回头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这时,粑粑三儿突然有了一种预感。
果然,一过观音阁旁边的女医院,崔大梨在一溜儿堂棺材铺的门口站住了。粑粑三儿犹豫了一下,只好跟过来。崔大梨敲了敲棺材铺的门。里面的灯亮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粑粑三儿跟在崔大梨的身后进来。刘一溜儿显然正等着,一见粑粑三儿,愣了一下,跟着就噗地笑了,点头说,好啊,好,你这条道儿算是走对了。粑粑三儿没说话。崔大梨没理会刘一溜儿的话,放下包袱说,一共30套,一个包袱15套,你过过数儿。刘一溜儿朝这两个包袱瞥一眼说,不用了,回回这样,还信不过你?接着又说,下午那边刚传过话来,再要100套,这回可要得急,给三天限,行不行?崔大梨想想说,行倒是行,八里台子那边还有,可那一块儿的人已经烂了,就不知能用的衣裳还有多少。刘一溜儿说,就算人烂了,衣裳也烂不了,不过这回可别像上回,衣裳不能有味儿,那边最忌讳这个,真退回来,可就白忙活了。
崔大梨说,这好办,用火碱多烧一会儿就行了。
刘一溜儿点头,这就是你的事了。
又说,还是老规矩,钱下回一块儿算。
崔大梨嗯了一声,就和粑粑儿出来了。
粑粑三儿没想到,刘一溜儿表面开着棺材铺,暗地里还干这种买卖。往东门这边走了一段,问崔大梨,刘一溜儿收了这些军服,再去卖给军队?崔大梨这时交了军服,已经轻松下来,脚步也放慢了,回头说,他够不着军队的人,这中间还隔着好几道手呢。
崔大梨见粑粑三儿没明白,就告诉他,一开始,刘一溜儿找他干这事儿,他也以为很简单,他去城外扒来死人的衣裳,卖给刘一溜儿,然后刘一溜儿再转卖给军队的人。可后来才知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水也挺深,这些军服最后卖到哪儿去,卖给谁,连刘一溜儿也不清楚。刘一溜儿认识一个叫马大瓢的人,这马大瓢是在估衣街上卖估衣的。估衣街上卖估衣的也分两种,一种有店铺,做的是正经买卖。还一种是打地摊儿,用街上的话说,做的是野买卖儿。这种做野买卖儿的,卖的估衣就不能问来路了。这马大瓢在估衣街上就是打地摊儿做野买卖儿的。有一回他的摊儿上来了个人,听着是外乡口音。这人在他的摊儿上扒拉了两下,抻出一件军服来,拎起来问,这是哪儿来的?马大瓢一看脸色就变了,这军服上还带着两个很明显的枪眼儿。马大瓢卖的这堆烂估衣哪儿来的都有,这时一问,他自己也说不清了。再看这外乡人,长得方头方脸,留着一寸来长的茬子头,短脖子宽肩,也摸不清是干哪一行的,不过看着倒没恶意。外乡人用一根指头挑着这军服问,这种衣裳还有没有?马大瓢这才回过神来,说,眼下就这一件,不过如果真想要,还能想办法。这人说,再要10套,连上衣带裤子,5天以后,我来拿。说完扔下这军服就起身走了。走了几步又站住,回头说,再有带枪眼儿的,给我补好。马大瓢看着这人走了,就赶紧收起地摊儿,奔水阁大街的棺材铺来。刘一溜儿跟马大瓢已认识几年了,也是生意上的交情,赶上这边有死人剩下的衣裳,就转手倒给马大瓢,让他拿去当估衣卖。马大瓢来到棺材铺,把这事儿跟刘一溜儿说了,又说,这种事想来想去,只能找你,这一阵城外整天响枪响炮,听外面来的人说,打死的人一堆一堆的,扔在野地没人管,让野狗拉得到处都是,弄几件军服,应该不是难事。刘一溜儿听了说,行倒是行。后面的话就没说出来。马大瓢知道刘一溜儿的意思,这人没给定金,就是拿嘴这么一说,怕这事儿不保险。于是说,这种事儿也如同做买卖,买卖没有手拿把攥的,有赚就有赔,真打算干就甭犹豫,大不了弄来他又不要了,我当估衣卖也不会砸在手里。刘一溜儿一听,也是这个道理,就又去找二疤瘌眼儿。但二疤瘌眼儿只干偷坟掘墓的事,扒几件死人衣裳赚不了几个钱,这种事也就看不上眼,于是给刘一溜儿出主意,可以去西门外的杠房,找崔大杠子。刘一溜儿当然知道崔大杠子,但这时一听,觉着这二疤瘌眼儿说的不挨着,崔大杠子是杠房抬杠的,怎么会去干这种事?二疤瘌眼儿说,他不干,可他的两个儿子能干啊。
刘一溜儿一听也对,这才来找到崔大梨。
这时,崔大梨对粑粑三儿说,干这事儿已经快一年了,现在也越干越熟,每回他和老二去城外弄了衣裳回来,先洗了,给刘一溜儿送来。刘一溜儿再转手交给估衣街那个叫马大瓢的。马大瓢再仔细洗一遍,找人把枪眼儿和破的地方都补上,然后卖给那个外乡人。这一阵,听刘一溜儿说,马大瓢要的量越来越大,他兄弟俩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才想找个帮手。
说完,崔大梨又看一眼粑粑三儿,干这行没别的,一是嘴严,二是胆儿大。
粑粑三儿闷着头,嗯了一声。
粑粑三儿这一宿没睡踏实,天快亮时才睡着。再醒来,就已将近中午。起来吃了口东西,就又来邢家胡同找崔大梨兄弟俩。崔大梨和崔二梨已经准备好麻袋,一见粑粑三儿来了,用个包袱皮儿把几条麻袋包起来。崔大梨拎在手里,回头说,走吧。
粑粑三儿就跟着他兄弟俩出来了。
从邢家胡同南口儿出来,奔海光寺,再一路往南,就朝八里台子这边走来。一过八里台子越走越荒,再往前就已经没有人烟了。这时天也渐渐黑下来。粑粑三儿跟在崔大梨兄弟俩的身后,又往前走了一段,就闻到一股一股的咸臭味儿,噎得人直想吐。他知道,这应该是死人的味道。下了大道又往里走了一阵,崔大梨兄弟俩就在前面站住了。粑粑三儿朝四周仔细看了看,登时头皮一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借着月色,只见前面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人。显然都是打仗打死的,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一条腿。粑粑三儿朝前迈了一步,脚下突然一绊,低头看看,才发现竟是个人脑袋,正龇牙咧嘴地朝自己瞪眼看着。这个脑袋显然是被大刀斜着砍下来的,而且刀很锋利,刀口齐刷刷的。粑粑三儿只觉嗡的一下,连忙又朝前紧走了几步。崔大梨兄弟俩已在前面弯着腰翻弄尸体。崔大梨回头说,你不用动手,跟着就行。
说着,就朝这边扔过一件军服上衣,让粑粑三儿装进麻袋。
这时,远处有个人影,朝这边走过来。
这人影喊了一声,来了?
崔大梨说,来了。
人影说,这回你们费点儿劲。
崔二梨问,怎么?
这人影说,衣裳不整齐,人都打烂了。
这人影说完,就朝旁边去了。
崔大梨兄弟俩不时把衣裳扔过来。这些衣裳有的很湿,也黏,抓在手里滑溜溜的。粑粑三儿觉着自己马上就要吐出来了,但还是使劲忍着,一边在心里数着,连上衣带裤子已有三十几套,第二条麻袋也装满了,已经在装第三条麻袋。刚才的人影在不远处朝这边喊,这边的尸首好,比那边的囫囵。崔大梨应了一声就朝那边走过去,一边回头问粑粑三儿,麻袋还能装下吗?粑粑三儿说,快满了。崔二梨在这边说,已经三十几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崔大梨嗯了一声,就回来了。
这时,粑粑三儿已经把满满的三麻袋衣裳拎到旁边的小路上。崔大梨兄弟俩过来,三个人各拎起一个麻袋,背在身上,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大道这边走来。
回到邢家胡同时,天已大亮了。粑粑三儿一进小院扔下麻袋,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光是累,这一路让麻袋里的军服熏的,已经吐了几次,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崔大梨也扔下麻袋,从屋里拿出一个酒瓶,自己先喝了一口漱漱嘴,吐了,又喝了几口,递给粑粑三儿说,把嘴涮涮,喝几口,这东西能解毒。粑粑三儿从没喝过酒,这时也已顾不得了,抓过酒瓶子就喝了一大口,连辣带呛,一下憋得脸通红,差点儿背过气去。赶紧吐了,又喝了两口,才渐渐喘过气来。崔二梨虽然瘦,倒有些干巴劲儿,这一路没看出累。这时已经把麻袋里的军服倒出来,翻了每个上衣的衣兜,然后抱着塞进院子角落的水缸。崔大梨说,今晚还得去。
粑粑三儿已经走到小院门口,回头说,还去?
崔大梨说,要的是100套,这才三十几套。
崔二梨说,是啊,至少还得跑两趟。
粑粑三儿没再说话,扶着墙慢慢走了。
这个下午,粑粑三儿再来时,一进小院,听见崔大梨兄弟俩正在小屋里矫情。粑粑三儿犹豫了一下。人家兄弟俩不知为吗事儿矫情,就一时吃不准,进去还是不进去。这时屋里的崔大梨已经看见了粑粑三儿,就朝外说,进来吧。
粑粑三儿只好进去了。
他兄弟俩还接着刚才的话,继续矫情。
粑粑三儿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崔大梨有个习惯,每次出门前,总要先在院里扔一只鞋,倘鞋尖冲东或冲南,就是吉,这事也就能干,而如果冲西或冲北,就是凶,这事就得寻思一下。这个中午他兄弟俩吃完了饭,又收拾好麻袋,崔大梨趁等粑粑三儿的工夫又去院里扔鞋。头一下扔得劲儿大,把鞋扔到房上去了。崔大梨就觉着不好。上房把鞋拿下来再扔,果然,鞋尖冲西。这一下崔大梨就犹豫了,有心想不去了,可棺材铺的刘一溜儿给的是三天限,今天已是第二天,倘不去,这100套军服就来不及了,可是去,心里又没底,眼看着是个凶卦,不知真去了会不会出事。崔二梨却不信这一套,觉着大哥是自己吓唬自己,就坚持说,该去还去。于是兄弟俩就为这事儿一直矫情来矫情去。这时,他俩又一块儿转过脸来让粑粑三儿说,去还是不去。粑粑三儿倒不相信扔鞋,但相信算卦,爹这回死,事先就曾算过一卦,算卦的说爹流年大凶,会有金器之灾。结果爹让斧子砸了手腕,人就这么走了。这时一听他兄弟俩问自己,就有些为难,有心想说不去,怕崔二梨不高兴,可如果说去,又怕崔大梨不高兴,况且既然已算出是凶卦,倘真去了,再出点事,自己也担不起这责任。最后还是崔大梨一咬牙站起来,说,去就去吧,刘一溜儿那边催得紧,就算今晚去了,这100套都不一定凑得上,咱小心就是了。崔二梨一听,立刻也说对。
于是几个人拿上麻袋就出来了。
也就在这天晚上,果然出事了。
这一晚来到昨天来过的地方时,天还没黑透,四周也就看得很清。粑粑三儿这一看,浑身的汗毛又竖起来。敢情这是一片乱葬岗子,四周黑乎乎的一片,扔的全是尸首。这些尸首都穿着军服,显然是在哪儿打完了仗,又被拉过来的,因为尸首太多,埋不过来,也就干脆横七竖八地都扔在这里。崔大梨又让粑粑三儿等在旁边,就开始和崔二梨忙着翻弄尸体,找身上囫囵的,往下扒军服。粑粑三儿在尸堆外面,把崔大梨兄弟俩扔过来的军服一件一件装进麻袋。这时天已黑下来。昨天的那个人影又朝这边走过来,喊了一声,还天天来啊?
崔大梨没抬头说,买卖的事,身不由己啊!
粑粑三儿朝那边看看。崔大梨已告诉他,这个人影就住在附近的李七庄,叫麻和儿,是个专在尸首堆里捡洋落儿的。所谓捡洋落儿,也就是在死人身上翻找值钱的东西。
这时,这麻和儿又朝这边喊了一声,这两天野狗多,小心啊。
说完,麻和儿就朝远处去了。
这天来得早,天还没黑透,崔大梨兄弟俩已经又扒了三十几套军服。粑粑三儿数着差不多了,就朝崔大梨那边喊了一声。崔大梨显然心里也有数,叫了一声崔二梨,就朝这边走过来。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吵嚷声,再细听,是叫骂,跟着又是一阵哭号的声音。粑粑三儿听出来,这哭号的是麻和儿。崔大梨知道出事了,喊了一声快跑!三个人背起麻袋就朝大道那边跑去。粑粑三儿一边跑着,又扭头朝麻和儿那边看,这时就见几个人已朝这边追过来。粑粑三儿紧跟在崔大梨的身后。但崔二梨身材瘦小,腿也短,背着麻袋越跑越慢,渐渐就落在了后面。崔大梨回头喊,把麻袋扔了吧!崔二梨舍不得,还把麻袋背在身上。前面有个土坡,土坡的下面是一个水坑。崔大梨急中生智,跑到土坡跟前一扭身就跳下去。粑粑三儿明白了,跟着也跳下去。这时崔二梨也从后面跑过来。但跑到还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后面突然传来枪响,砰的一声,就见崔二梨的脑袋像一只猪尿泡,忽然一下爆了,转眼间似乎变成无数碎片飞得无影无踪,只剩了一个光秃秃的脖子。他背着麻袋又往前跑了几步,似乎犹豫了一下,才一头栽到地上。后面的人追上来。粑粑三儿躲在黑暗中,借着月色看清了,这几个人都穿着军服,手里提着枪。他们过来,把崔二梨的尸首踢到一边,抓过麻袋把里面的军服倒出来,开始一件一件地翻找。翻了一阵,一个关外口音的人说,妈个巴子的,还是没有。
那人说完啐了口唾沫,就起身带着几个人走了。
崔大梨和粑粑三儿见这几个人走远了,才从土坡底下爬上来。过来看看崔二梨,只见他像只蛤蟆似的趴在地上,脖腔里流出一大摊血。崔大梨哽咽着说,知道今晚就得出事,还非要来,这才叫倒霉看反面儿。又朝四周看看说,先埋这儿吧,以后再想办法。
说完,让粑粑三儿帮着把尸首抬到土坡下面,就草草地埋了。
粑粑三儿这时已有预感,这件事还没完。
果然,第二天就又出事了。
粑粑三儿和崔大梨第二天回来,把这次弄来的军服整理出来,都洗净晾干。到了晚上,连同头一天弄来的军服一起包好,就给刘一溜儿送来。刘一溜儿一看挺高兴。崔大梨没提兄弟崔二梨出事的事,只告诉他,这是78套军服,再多没有了,也弄不来了。刘一溜儿听了点头说,弄不来就弄不来吧,有多少算多少,两天以后,你来拿钱。
粑粑三儿和崔大梨就从棺材铺出来了。
快到东门时,崔大梨说,你今晚别回去了。
粑粑三儿明白崔大梨的意思。兄弟崔二梨刚死,现在尸首还扔在八里台子那边的坟地,崔大梨又不敢告诉他爹崔大杠子,心里肯定烦乱。于是粑粑三儿就跟着崔大梨一块儿回邢家胡同这边来。两人刚进门,就听院里有动静。崔大梨正要出去看看,屋门咣的一下被踹开了,李七庄的麻和儿一步跌进来,后面跟着进来几个穿军服提着枪的人。粑粑三儿借着灯光,见麻和儿的脸上都是伤,身上的衣裳也撕成一条一条的了。接着就认出来,这跟进来的就是在坟地追着打死崔二梨的那几个人。显然,是麻和儿把他们带来的。麻和儿拖着哭腔说,崔大哥,你别怨我,是这几位老总让我带他们来的,其实也没吗大不了的,只要跟他们说清楚,就没咱的事了。
崔大梨这时已说不出话来,看看麻和儿,又看看他身后的这几个人。
还是那个说话有关外口音的人,走过来问,你们弄回的军服呢?
崔大梨犹豫了一下说,卖了。
这人问,卖谁了?
崔大梨不敢说了。
这人用手里的枪朝崔大梨指了指,说,再问你一遍,卖谁了?
崔大梨朝后退了一步,还不敢吭声。这时旁边的麻和儿已经哭出声儿了,对崔大梨说,崔大哥啊,你把这些军服到底卖谁了,赶紧说出来吧,再不说咱几个也没命了!
崔大梨还不吭声。
这时,粑粑三儿忽然在旁边说,卖给一溜儿堂棺材铺的刘掌柜了。
关外口音的人扭头看看粑粑三儿,问,这一溜儿堂棺材铺在哪儿?
粑粑三儿说,东门外,水阁大街。
麻和儿立刻哦一声说,我知道。
说完,麻和儿就带着这几个人走了。
崔大梨见这几个人出去了,才回头埋怨地看看粑粑三儿。
粑粑三儿看一眼崔大梨,没说话。
粑粑三儿回家一连睡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崔大梨来了。崔大梨平时很少来这边,这时一见他来,就知道,应该又出事了。崔大梨说,是又出事了,不过这回不是咱的事。
粑粑三儿问,谁的事?
崔大梨说,是刘一溜儿的事。
崔大梨告诉粑粑三儿,这天该是去找刘一溜儿拿钱的日子,他一大早就去了水阁大街的棺材铺。可到那儿一看,铺子里没人。一会儿铺子的伙计来了,问伙计,伙计也说不知道。再使劲问,伙计才说,两天前的晚上来了几个人,都穿着军服,提着枪,看样子挺吓人,一来就找刘一溜儿。伙计说不在。这几个人问去哪儿了。其实这时刘一溜儿就在铺子后面,但伙计不敢说,只说不知道。这几个人就走了。没一会儿又回来了,这回径直去后面,就把刘一溜儿揪出来。刘一溜儿在铺子后面住的是一个暗室,就是怕有人找他。不知这几个人是怎么知道的。这几个人把他揪出来问,最近是不是收了一批军服。刘一溜儿起初不承认,说他是卖棺材的,不卖军服。这几个人一见问不出来,就开始打他,还不是用手,是用手枪的枪托子,几下就把他的脑袋砸破了,血流得浑身都是。刘一溜儿这才说,是收了一些军服,不过都卖给估衣街的马大瓢了。这几个人立刻让他带着去估衣街找马大瓢。
崔大梨说,刘一溜儿让这几个人带走,就再也没回来。
粑粑三儿问,他出事了?
崔大梨说,是,出事了。
当时崔大梨一听棺材铺的伙计说,刘一溜儿是让那几个人带着去估衣街找马大瓢了,就赶紧又去估衣街,想问问这个马大瓢。崔大梨倒不是担心刘一溜儿出事。刘一溜儿还欠着这几次军服的钱,这些钱是用崔二梨的命换来的,崔大梨想,不能让这钱就这么烂了。等去到估衣街,也找到了马大瓢,才发现这马大瓢这时躺在床上,两眼睁得挺大,已经不省人事了。听他家里的人说,他是让那几个来人连打带吓,成了这样的。崔大梨再问马大瓢的家里人,那几个人后来带着刘一溜儿又去哪儿了。马大瓢家里的人也说不上来。
粑粑三儿一听就明白了,看来刘一溜儿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崔大梨说,是啊,后来的事,还是听二疤瘌眼儿说的。
这个下午,二疤瘌眼儿来西门外的杠房找崔大梨。崔大梨一见他挺神秘,像是有话,又不想当着别人说,就跟他一块儿出来。等来到个没人的地方,二疤瘌眼儿才说,水阁大街棺材铺的刘一溜儿出事了,问崔大梨,听没听说。崔大梨正急着要找刘一溜儿,一听就说,只听说他让人带着去估衣街找马大瓢,后来到底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二疤瘌眼儿嗨的一声说,他也是刚听说的。他这几天刚又挖出一副好椁板,本想卖给刘一溜儿,可去棺材铺找了他两回,都没找见。这个下午,无意中听济生堂药铺的施杏雨说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头些日子不知哪儿开来一伙军队,跟总督府的队伍在炮台庄打起来。这一仗打得挺惨,这伙队伍的一个营长也给打死了。按说这营长死了也就死了,可他身上还有东西。这营长太迷财,这几年搜罗了不少钱,后来他把这些钱都兑成了金子,又化成金饼。金饼在身上不好带,就都缝在军服上衣的领子里,平时穿在身上也看不出来。这事儿本来没人知道,可有一次他的马弁喝醉了,把这事儿吐噜出来。这一下,他手底下的人也就都记住了。这回这营长给打死了,他手下的人就都想找到他的尸首,找尸首,当然是冲着他缝在军服领子里的这几块金饼。这几个人一路捯着找到刘一溜儿,刘一溜儿先还不承认,说没收过军服。后来一见脱不开了,又说收是收了,可没见有什么金饼。再后来又说出马大瓢,这几个人就让他带着去找马大瓢。马大瓢也说没看见,而且说,刘一溜儿送来的这批军服还没打包。这几个人把包打开,果然找到了那个营长的军服,再一看,这军服的领子已经被人拆开,里面的东西都已拆走了。马大瓢这人本来胆儿就小,这时让这几个人连打带吓,一下就吐着白沫不省人事了。这时,这几个人也明白了,这事儿应该就是刘一溜儿干的,于是就把他带走了。
崔大梨说到这儿,就乐了。粑粑三儿看看他。
崔大梨说,有个事儿,很奇怪。
粑粑三儿问,吗事儿?
崔大梨问,刘一溜儿在棺材铺后面的那个暗室,你知道吗?
粑粑三儿想想说,不知道。
崔大梨说,是啊,连你都不知道,外人就更不会知道了,可这几个人是怎么知道的呢?粑粑三儿一听就明白了。崔大梨又摇头咂了一下嘴说,只是他欠的钱,这回算是真烂了。
粑粑三儿问,他死了?
崔大梨说,是啊,今天一早,在海河里漂上来了。
这天上午,粑粑三儿到东门里的吴家胡同去了一趟。吴家胡同的把角儿有个“鸣记棺材铺”,掌柜的姓洪。粑粑三儿听爹说过,这洪掌柜还欠着两口寿材的工钱。粑粑三儿来到“鸣记棺材铺”,洪掌柜一见就赶紧说,等了你这些日子,总算来了,钱早准备了,就等着你来拿。然后又凑近粑粑三儿,把声音压低了问,这几天,去水阁大街了吗?
粑粑三儿见洪掌柜的眉毛一跳一跳的,看出挺高兴,就摇摇头。
洪掌柜嗯一声说,你去看看吧。
粑粑三儿问,看谁?
洪掌柜说,一溜儿堂啊。
粑粑三儿没说话,拿上钱就出来。
粑粑三儿径直奔水阁大街这边来。来到一溜儿堂棺材铺的门口,一下愣住了。只见郭瞎子正微笑着站在铺子的门口。他身后的棺材铺,已改成了针灸馆……

王松,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王松作品集》(四卷)。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发表作品700余万字。小说和散文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各种文学奖项。
来源:《芙蓉》
编辑:施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